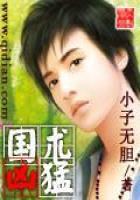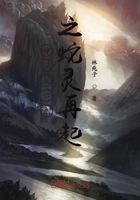中午三人只是胡乱吃了些,张北翎甚至吃完了都记不清吃的是什么。自从青渊吞噬了那四剑的剑鞘,就一直烫的要命,以至于必须要魂气压抑才可以勉强挂在腰间。回到准备间第一件事就是把青渊晾到了两步之外。张北翎看着还有不少时间,感觉眼前也有点模糊了,不知不觉睡了过去。
无梦。
下午的剩余两场,竟然是以令张北翎哑然的方式结束的——对方都是挂着彩上来的,或许就是被那一人的队伍虐了,一开始就认输,倒是轻轻松松。
晚饭时候,张北翎又莫名其妙地睡着了,也不知是中了什么邪,那劲头就好像要把前些日子缺的觉都补回来一样。自然就谁都没吃饭,倒也都睡得着。醒来后,却注意到那个先前被青渊鞘搞出来的方坑恢复了原来地面的样子,整个屋子都暖洋洋的。
三人相继睁开眼睛。
“你说咱们会不会进决赛?”罗桀问道。
“七胜一负,有点悬,但把那个变态看成全胜水准,那其他队伍最多也是七胜一负吧。”
张北翎不打算说话,再次眯上眼睛装睡着。
吴冬至的声音压得很低,但张北翎还是听得清楚:
“你知道上午影二那四把剑是什么吗?”
“没记错,应该是月瑕?”罗桀已经尽力压低声音,但大粗嗓门让他不成功,反而听起来引人发笑。
“《器》字卷第八。”
“嗯,怎么了?”
“以北翎的实力,是绝对无法让青渊吞噬掉那四剑,但那四剑的剑鞘从开始时就一直陈列在角落,如果把握住机会还是有可能得手的。青渊这个状况应该也是逼近吞噬的极限,一时半会怕是复原不了,而张北翎也会因为魂器的疲惫而疲惫,这就解释通了。”
“嗯,冬瓜,你确实是脑子快。”张北翎吐出一句,睁开了眼,“但为什么要这么小声,这是什么坏事吗?”
“你不知道的吗?月瑕!”
“哦,我在小时候看书看到过,不就是四把名字很唬人的逸剑?听你说好像还挺有名。”
张北翎渐渐回想起那几十页黄草纸上关于名兵器密密麻麻的记载,忽然脸色沉了一些,但还带着疑惑。
“十多年前,风魁无极先生一家被无由灭门,无极先生本人都惨死园中,分别在百汇、龙窍、岳口、浃门四穴有四处致命伤,被辨认出是这四剑所造成的。要知道,当时无极先生是天下第二,而第一是皇宫禁军统领纵阑先生,当时正在伏羲阁门口亲自巡逻,包括陛下的许多人都看见了,无暇杀之而且作为当时的影魁也于无极先生交好,没有理由,所以究竟谁下的手一直是个迷。四个月后,征南将军岑苏于沉琥国界意外捡到四剑,陛下命人在此剑上贯了决绝之意,从那时起,任何一个用那四剑的人都不可避免心困决绝,经年必然焚心而亡。上午那人一人成队,应该就是当代影魁亲传,应该是有什么拖延的办法,但绝不会解除,因为当年贯意人在转年初被人刺杀,死相极惨,释意必须贯意人,所以这意就相当于永远不毁了。虽然你只是带着剑鞘,或许会轻很多,看起来你和影魁也熟络,我还是很担心你会因此背负心魔。”
“先别说我,我命大不着急。我有几个问题......”
“一个一个问,我容易忘。”
“第一个,为什么不怀疑征南将军是凶手?”
“岑苏是个普通人,没有魂域,无法使用逸剑。”
“第二个,为什么名人都叫什么先生,而宁箴不这样?”
吴冬至已经对张北翎直呼影魁名讳一点都不惊讶惶恐了。
“影魁本来是有的,但不好听,所以让世人都知道自己的真名。”
“不好听?”
“失慕先生。”
“哪里不好听,挺好的呀。”
“影魁就觉得不好听,就不想要,你也管不了人家。”
“那无极先生的真名是什么?”
“长老和门魁的真名,一般是不允许被普通世人记住的。”
张北翎懒得问为什么,都是些不感兴趣的繁琐的故事,那种故事他不喜欢听。又要睡着的时候,马老师却走进了准备间,张北翎又一下子睁开眼。
“怎么样,状态都还可以吧?”马老师扫视众人
“马老师,我们进没有进决战?”罗桀最心急。
“啊,因为有和你们胜负比相同的,裁决正在评估你们的水平,明天一早就会有答案。在这之前,你们可以讨论一下战术。因为若你们真的进入决战,这两天的战斗中可能成为你们对手的人已经见识过你们先前的战术战法,为了做好准备,尽管不确定是否用得上,你们必须要在这个晚上有所突破。”
“马老师有何指点?”
“我当年的经验就是,一直睡觉。我想你们现在的情况这么做再简单不过。没铺盖也没事,坐着就行,术师大多都这样。我今晚回山上,明天也不来了,你们事都办完就自己回去吧。”
未等三人问关于决绝意的事,甚至没来得及客气几句,马后炮已经离开了。
“看,马老师都说了要睡觉,你们两个就好好听话吧,一直窃窃私语的我睡不着。”
“好吧。”吴冬至闭上了眼,坐在了专座,墙角。
张北翎睁眼时,却发现自己正站在残云山上遍地秧苗的结界中,周围空无一人。走到马老师和各长老的屋子里,也是同样。张北翎自言自语了一句,说完却不记得说了什么。
作为一个经历了许多难以理解的事的人,张北翎在最快的时间内恢复了冷静。青渊挂在腰上,却不知为何挂在了右边,和平时不一样。张北翎发现自己无法回忆任何事情,他的精神世界好像被什么东西填满了,时不时还有阵痛传来。
张北翎向着出口的方向跑了很久,却一直没有出去。回头已看不到身后茅屋、小湖和农田。
猛一转头,右边远处有一点黑色。有一股力量驱使自己向那黑色跑去,不觉疲惫。越来越近时,渐渐看清了,那黑是一条通向地下的隧道口,一串整体的台阶笔直通向更黑的地方。张北翎走了下去。
黑漆漆的一片,张北翎靠着右边摸着墙壁走。脚下有时碰到各种触感的东西,张北翎只好走得越来越快,或许是人的本能,什么都看不到时,总是会感觉面前有什么挡着自己,但张北翎只在这里感受到自己的气息,回头再也看不到光明,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
只听见“噗通”一声,张北翎感觉到向下掉了一截,从脚踝一直到膝盖传来湿润和冰凉的感觉,但是又有些粘稠,张北翎不认为这是水,但还是义无返顾地继续走着。
越来越深,直到不明液体没到腰间,胸前,下巴......张北翎全身都浸了进去。意外发现在其中不需要闭气。
张北翎突然感觉脚下一空,想退回来却觉得有股吸力将他吸向那个空洞。
张北翎想挣扎,但突然周身失去知觉。
张北翎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树荫之下,身下是厚厚的落叶,还挺软。周围是看不到尽头的森林,再次看见光,觉得无比刺眼。
环视周身,花草树木都比平常大上一号,落叶都有八九掌大小,不远处一些小爬虫看起来也有手腕粗细,似乎注意到他,抬了抬头,不知钻到哪里去了。
张北翎站起来,地面上略过几只硕大的鸟影,抬头却没看见什么。
往前走,张北翎发现这里的一切越来越大了,到最后树上的爬虫变得和他一样大,在遥远却清晰的地方蠢蠢欲动。
“小”爬虫们向自己爬过来,张北翎开始跑起来,但速度显得要慢许多。附魂之时,青渊却突然有了重量,而且渐渐变得越来越沉,张北翎感到有些累了,心跳声清晰地响着,越来越快。附魂只是暂时甩开了一小段距离,越附自己就越小了,也就越慢了。
张北翎回头看时,一张腥黄的大口已经近在咫尺。张北翎可以清晰地看到几排不齐整的小牙上还有一些极小的样子各异的虫在蠕动。一股腥臭要包围他。
张北翎一咬牙一闭眼,身形一转,向后附魂冲去。剑气在瞬间迸发,张北翎到了单次攻击的极限——十七道剑气,全部直接放射出去。
感觉到出来了,张北翎看着自己一身粘稠的腥黄液体,胃里一阵翻江倒海。还没来得及出汗,回头见身后已经血肉模糊的大虫子,扑腾了几下彻底失去了生机。
周围的其他虫子停滞了一下,以更快的速度向张北翎涌来。
张北翎一步步往后退,虫子们小了一点。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吗?”
张北翎开始附魂后退,感受到身后近处有气息就偏开,在包围圈之中转着圈附魂后退。包围圈越来越小,张北翎在差不多大小时跳出了圈子。青渊渐渐恢复了平常的轻若无物,张北翎感觉自己甚至比之前还大了许多。张北翎懒得再理那些小虫子,却发现自己已经不在最初进来的地方。张北翎也管不了那么多。头昏脑涨的感觉又来了,压迫着他向一个方向走去。
倒着走,张北翎一直变大,周围的树一直变得越来越细,却好像一点都没矮。青渊闪出一道剑气竖直向上,一秒后就有“噗”的一声,伴随几片残叶落下来。应该是不远了呀,但就是怎么都到不了顶。张北翎想到魂殿门口那棵巨树,却没有当时不到终时不停息的想法,都理解不了那囫囵便过,正着跑几步,恢复正常。
为了保持正常大小左右,张北翎只好向前走一段路,看好了之后再转身,向后走一段路,如此往复。但张北翎是种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对,总是摔倒。
可能是记不清楚吧。张北翎这次要开始倒着走的时候,便格外仔细地看过一遍,挑好一个方向,确认了路上是绝对的平坦,倒着走了去。
四步半,张北翎感到后背一小阵痛麻,回头才知自己撞倒了树上。
地上的脚印笔直地延伸过来,才四步也不可能差这么多。由于这两天见识过了关于一些曲折空间的魂术,张北翎对此较为敏感。略偏一些,拔出青渊来,把剑刃当做镜子,继续倒着走。
诡异。张北翎盯着剑刃中的画面,自己每动一下,身后便有无数事物移位,而身前却什么也没发生。张北翎再往前走,身后的事物也会变换。正好五步,一切又是先前的样子,看上去毫无阻碍的一条路。
突然脚下咯吱一声,大概是自己踩断了一根树枝。低头看去,最令他不解的一幕展现在眼前。
又一圈小爬虫,在地上极其缓慢地蠕动。张北翎知道自己为了防止意外,可以把自己变得大很多再保持。只是这一圈爬虫实在熟悉不过——是那一圈曾经要吃了我的恶心虫子?
张北翎其实并不在乎这些爬虫,只是对这丛林,有种畏惧。自己身上那些腥黄粘稠的虫血不知何时消失的。
张北翎继续走着,碰树的情况由于青渊这面镜子已经几乎避免了。数着步子,却听又是咯吱一声,张北翎诧然低下头,自己又把断掉的半截踩断了。那一圈小虫还是一样的,仔细看还能发现圈子其实大了一点。七十七步。
这次,刻意歪歪曲曲地走,还一步长一步短,七十七步,张北翎死盯着地面,发现自己的脚正好落在上次踩断树枝的地方。
张北翎原地踏步了七十六步,再后退一步,这次却没有踩上。推想的,难道是位置的改变才可以?
伴随着一些惊慌,张北翎却急中生智,如若是横着走,它会不会前后同时变化?
向左迈一步,什么都没有发生,前后的世界依旧。张北翎有点失落,但是又有些安全感。
张北翎没见右边赫然是一个不见底的深坑。一步踏出,左脚也跟着一滑,半个身子已经下去了。
张北翎试图抓住什么,但地面上只有又滑又脆的叶片。张北翎在坠落中大喊出声。
拼命地要附魂往上,但四周黑得不知是否有效。只看到上方有一点光明越来越小。
张北翎望向底下,白白浪费魂气是不明智的。张北翎双臂缓缓弹出,用青渊极力向前伸,想要够到那边缘去。终于,重复了几次之后,铿锵响起,张北翎虎口一麻,但还是竭力控制住了。青渊插进洞壁,溅出无数火星,还有一些极其尖锐刺耳的摩擦声音,让张北翎头疼。
不对,身下也有光明。
终于停止了下坠,张北翎却看到不远处,有一小点烛焰一般的火焰,爬近点,这分明就是烛焰。
这地方还有人?张北翎想在最想见到的就是人了,活的最好,死的也凑和,甚至不论生死要跟他一话不说打上一架也可以,他已经在精神的极限徘徊了。他感觉得到自己,对这寄予了的些许希望,如果落空,自己怕是会有一些心境上的损失了。
那是一个垂直于大洞的另一个洞,大约九尺高,过人正合适。
入洞也不敢打招呼,洞壁较光滑的,阴森森却不狰狞。转个弯,张北翎看到一个身穿破旧的粗麻袍的人形事物,好像正坐在那里。
张北翎在经历了这些事情后,已经不太相信自己的眼了。
“嗯?还有人会来这里?”一个沙哑含糊的声音响起来,张北翎有些熟悉的感觉,但感觉很遥远,怎么都记不起来。
那身影回转过来,那竟是一个没有五官的“人”,只有两条浅眉和一大把黑白相间的胡子。张北翎不知是否应该称其为人。总之是被吓了一大跳,还没归鞘的青渊剑青光骤现。
而那“人”似乎非常惊讶,腾地一下做起来。张北翎本能地驰出去一道剑气,却令他不解地迅速消失于无形之中。
“别害怕,我原来也是个正常人的,我不会伤害你的。”只听到那声音不怎么含糊了。
“你坐那别动。”张北翎的声音倒含糊起来。
“老者”慢慢地坐下,好像背着沉重的东西一般。
“我刚进来不到一年,有人就来一趟。说吧,你什么事?”
“我先问。你为什么在这?为什么成这样?为什么我来就要有事?”
“老者”想着,是个心急的孩子?
“你要是想知道,那可得要不少时间了。也罢,看在你是第一个来的,我就跟你讲一讲这个故事。”
张北翎莫名其妙要听故事,有些突然,从绷紧的状态放松一些,但还没从刚刚的许多诡异经历中缓过来,只是想到这里应该也算是魂殿的结界中了,应该不会有什么穷凶极恶的人物......要是有也打不过,自己就连剑气是何时被化解的都感受不到。对方动都没动,必然高深莫测,但“他”的气息意外很明显就可以感受到,没有一丝杀气,似乎没什么危险。
“因家中远亲重罪受牵连,我虽未被斩决,但数十年努力都没能进入魂殿,名正言顺地成为一个术师。我很不甘心,我知道自己的天赋,我就辗转天下各处,从市集到荒野,偷偷修习,但最终还是被发现了。我逃到了很远的地方,但我的家人却被牵连受燃魂之刑,他们本来就过着非人的生活,却还要如此惨死。我在阴影中沉吟了很久,怪那禁止被提起名字的先人也没有用,我只能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想让看不下我的人都惧怕我。”
张北翎突然想起来“他”没有嘴,不知道是如何说话的。
“但我发现,惧怕是不够的。因为天下通缉,当时连我尸首的悬赏都达到了三万六千两黄金。我当时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想进魂殿就是不能进的天赋异禀的人为什么不得不屈膝隐忍去过低落的一生,不知为什么他们如此恨我。想来或许是因为太惧怕了。”
“打断一下,你就如此确定你的家人全都死了?”
“他”没有理会,只是继续讲着。
“我只好杀掉他们,但总会有更强的人来。我心中是有执念的,魔人曾经几次招揽过我,但我一直没有答应。导致魔人也开始看我不顺眼。”
他的声音又有些含糊,但不多时又恢复清脆。
“天下都容不得我了,我被迫与天下为敌。我曾经去过大陆的尽头,去过每一座城,一次次死里逃生,让我越来越沉浸于此。我甚至开始享受那些人们口中的天之骄子们绝望痛苦的表情,尽管我自己也重伤逼近极限,我感觉得到自己的心境不正常了,但我没有办法。最后,光魁先来了,我用全力杀了;然后是雷魁加上言魁,但我逃了,也伤了他们。影魁守着皇宫,只剩一个风魁。无极先生,一直没有来。但我听闻,就是无极先生处死的我的家人。我无法抑制,亲自去找了风魁,带着四把我自己打造的剑。我以半道神魂为代价杀了他和他所爱的一切,但我却不知为何更加痛苦了。这和我想要的完全不一样,我甚至后悔自己没有忍住要强的心去做个低微的凡人。我当时境界亏损许多,料到已经惊动的一些势力自己无法应对,我便干脆掩埋了我的所有魂域,把剑弃了,易了身体面容,随便到一座城中当了个小人物。我突然觉得这样的生活也不错。”
“然而没料到多年之后,我的那可怕的真相再次被人拾起,我却无心无力再去流浪四方,于是便趁魔人祸乱和风殿倾山之力诛杀我的时候,得老友助力,到了这结界中的隐秘处,让结界的灭意渐渐蚕食我,消去我的五官肌肉,我只是在这等死,也是享受这世上我能拥有的最后的清静。你是风殿弟子吧,我看你似乎不知道关于我的故事,看来那帮老头口风挺紧呢。你现在没有能力替你们当年的风魁报仇雪恨,应该是无意间来的?”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或怎么来的。”
“你的体内有决绝意,看来逼死我还不够,竟然还要逼死剑......还算浅,我劝你......不对,他必须得死了吧,你好像没救了。”
“我自有解决办法。”张北翎其实很害怕,但是他拼命地没有表现出。
“你出去的时候,还是别说了,长老们会为了风殿的名誉,先把你扫地出门,最终你也得落得跟我一样下场......唉,这是我的错吗?还是这个世界的错?”
张北翎有种莫名的悲哀,但突然想到面前是自己作为风殿弟子不得不面对的仇人,却不知说什么好。就死死地盯着。
“谁说说出来,就舒服多了?”“他”似乎有着无声无形的笑。
“你能停住在这,自然是你有缘听我唠叨几句,接着下去,便是出路。也由不得你不信了。”“他”说完,身子又转过去,继续安然地坐着,好像淌着无声无形的泪。
张北翎感觉身体有点沉重,头有点晕。
“若你想真正地活到有意义,本要让惧怕你的人变得尊敬你,这才是最后的真相。真的是命运让你不得不放弃了这条路吗?”张北翎发现青渊替他说了句话,突然也觉得有理,但又理解不了。
“他”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成了一块石头。
张北翎趔趄几步走到了洞口,感受到有几股凉而不阴的风地从下面吹上来,但是不知为何脸颊有如刀割,竟是凌厉如此。本来还要犹豫一会,但脚一滑直接摔了下去。
用火候不够的风墙勉强撑着,张北翎感觉四周有股深邃的幽怨,拼了命地想钻进自己心境之中。张北翎也吝惜不得魂气,焦急之间突然想到那不人不鬼的会不会坑了他?
“忍住。”张北翎不知不觉间咬牙,自言自语自己都听不清。
满身大汗地,张北翎腾地一下站了起来,熟悉的准备间里还有两人睡得正香。
走出去,明月依旧是整个天最亮的那片,它也早已对天下的一切见怪不怪了吧。看着遥远而不清晰的风云,渐渐纠结成不知名的形状。张北翎回想这个梦,真是锻炼人的心理素质啊,喃喃几句,真不知道在梦里施展魂术竟然能那么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