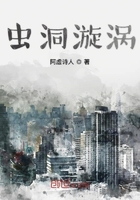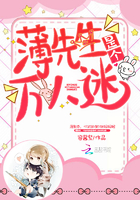说来离开自己的母校也有七年了,自从上了高中也就只回去了一次。说不出好坏,但逝去的事物总夹杂些对岁月匆匆的无奈。
依稀记得自己入学是在六岁的年纪,告别了屋后林子里的泥巴,由母亲牵着去了学校。仔细想来,我上七年小学母亲也就只去了那一次,去年夏天在家吃饭的时候,我不无埋怨的说:“别的同学下雨都有人来接,就我自己淋雨跑着回来,你就不担心吗?”
母亲窘迫的放下筷子“哪能不担心呢?”
小学是村子里的,离我家并不是太远,现在习惯了千百里地的来来往往,母亲的担心想必又要多很多了。
入了学就不能再蹲在母亲身边摆弄她扎的穗子,不过新熟识的同学总能很快转移孩童的视线,可能是天生的玩性吧。
去学校的路上会经过一条河,因为在里庄的北面,所以被人唤作北河。每次出门母亲都会叮嘱一句:“离河沿远点,水里有脏东西,掉下去就上不来了。”我一边应着一边跑着,她的话大多被丢在了后面。
北河的水很清,洒在水面上的光像邻家丢的碎镜子一样。河畔的野草丛里常常能捡到不知人家的鸭蛋,这时孩童会兴奋的大叫起来,把鸭蛋托的很高,向捡了一手羽毛的同伴炫耀。因为自家里都有养鸭子也就无所谓是谁家的了。
母亲大抵知道我不会听她的话,等我跑远,她一定会跟出胡同口来向北河看一眼。有时还会拜托堂哥带我一起去学校,其实走到北河倒是堂哥在看河里有没有鱼。现在北河被填平了,堂哥的孩子也快到当年我们的年纪了。
过了北河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地上满是苔藓,赶上下雨天,少不了栽上几个跟头,有不少次都是一身泥污的赶到学校。
出了树林就能看到学校的大门了,不过还要过三道“岗”。所谓的“岗”就是建房起基时挖出的深沟,为了雨季蓄水也就没再填平。孩童时喜欢跑到最高处再冲下去,常常把布袋里的书洒的哪都是。
校门口有一棵很高的柿树,听人说种了有几十年了。秋天,柿子挂满枝头,好不可人。
种柿树的是一个喜欢穿着军大衣的老人,同村的人说他以前当过连长,七十岁了腰杆也挺的紧直。因为挨着学堂,他便在自家院外搭了间木板房,卖些学生喜欢的零食和文具。大家都称他作“老公人”。在那些没有学校保安的日子里,他确实在为“公”守校。后来学校改建,将原先的大门封了起来,他就少有生意做了。不过他还是会闲坐在碎石上,给同学讲当年的历史:“小日本从永城走关路过来…………”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在六年级,他在学校曾经的操场上种了些蚕豆。是年,这个可敬的老人就过世了。
进了校门,迎面是一座**的雕像,底座上镌刻着“向**同志学习”几个大字。当然,这些都是后来知道的,刚入学的时候,我尚且不知道人像是谁,胡妄乎龙飞凤舞的草书。那雕像也在学校改建的时候拆了,扔到了学校西边的沟里。
当年,学校还都是低矮的房屋,教室前面毫无例外的种着剑麻,只有办公室那里长着几棵紫荆。当时学校最多的就是松树了,处处都有松脂的香气。学校改建之后,独留了一棵,孤零零的立着。
第一排教室的墙上贴着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祖国是什么样子。几个孩童常常盯着它们看,然后一个人随便说一个国家,看谁能率先找到。我很庆幸的是知道了朝鲜这个国家,准确的说是知道了“鲜”这个字。因为学前班的期末考试有一题就是用“鱼”和“羊”组成一个字。比之同学将“鱼”放到“羊”的上面,我是很幸运的。
第二排教室后面有一块空地,大多时间荒废着,后来老师们种满了蔬菜。春天时满园的油菜花,还有飞舞的蜜蜂和蝴蝶。学校改建之后,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那天我和小学同学王君一起回了学校,没有感伤,只是感觉我还是更喜欢记忆里的那个地方。比之树木,变化最大的是青春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