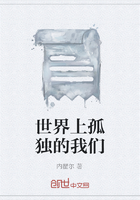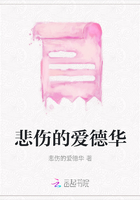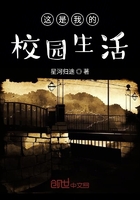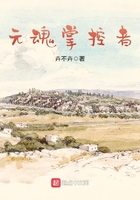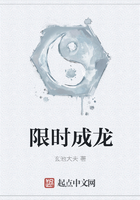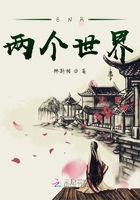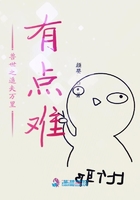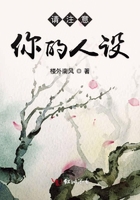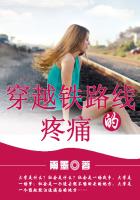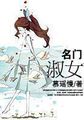最近读《列子》,其中有一篇公孙龙的论题。
原文如下“乐正子與曰:“子,龙之徒,焉得不饰其阙?吾又言其尤者。龙诳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尽。有影不移。发引千钧。白马非马。孤犊未常有母。’其负类反伦,不可胜言也。””
“白马非马”的解释大抵为,“白”是命“色”的,而“马”是状“形”的。形,色各不相干,因此“白马”就是“白马”不能说“白马”是“马”。“马”是各种形色马的统称,而“白马”只是诸多形色马中的一种,这里是一般与个别的差异。
公孙龙是战国时期名家的代表人物,他有名的辩题有“离坚白”和“白马非马”,他着重分析概念的规定性和差别性。
先前读过《南华经》,以庄子和列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对其论断有诸多批评,认为他“负类反伦”即背弃事物类别,违反世人的常识。我未曾读过名家代表的著作,不过可以猜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名家也会批评道家的不可知论。
“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
诚然受时代的制约,两者都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不过深究一点,万事万物寄寓的文化信息都是人类本着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界定的,即“概念”本身就是人类所创造的。换言之,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题终没跳脱“概念”的区间,只是用“概念”本身去说明“概念”以此混淆人的认知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