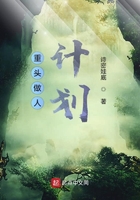望着那昏暗而来的灯火,孟洪奎扶着枪托甚为吃力的从地上爬将起来。他是一个大烟鬼,那原本精壮的体魄早已在醉生梦死的烟火中被吞噬殆尽。这不得不说是命运导演出的玩笑,一个靠种植罂粟来谋取暴利的地主老财,竟然被自己的罂粟狠狠扣上了一耙。想到此处,他不禁摇头懊悔。早在从军之时,孟洪奎就在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讨厌鸦片,也诅咒鸦片,更视那喷云吐雾的烟鬼为肮脏在人间的粪土,一文不名的渣子。不想如今的自己却又重蹈覆辙,不仅披上了魔鬼的外衣,更沦为了烟毒的奴才。这恰若那吃人的“藏金明王”,若不是昨日自己的一时之贪,哪会惹来今日这般的祸难。或许命运本该如此,一旦让你栽进了坑里,即便是喊破嗓子,哭瞎了眼睛,也找不到一个说理的地方。和谁说理?老天爷吗?所谓命运,看似简单二字,却犹如天书般的包罗万象,又似大海般的不可斗量。斗得过它就是运,斗不过它则是命。孟洪奎颤抖着虚弱的身体,在夜风萧瑟的坟地间狼狈的前行着。此时,他终于认清了自己,也似乎看透了生活。内心的贪欲让人变得疯狂,而贪欲的本身不过是高高在上的,也永无止境的空中楼阁,它不断的驱使着你去踏破底线,去抛弃尊严,只为用这人间的血泪铺就出攀爬的阶梯,让你无休止的禁锢在这不胜寒的边缘之间。稍有不慎,便是粉身碎骨的梦魇。
孟洪奎就这样一路跌跌撞撞的浑噩而来,寒风吹透着他单薄而又华丽的衣衫,清晰出瘦削残破的躯体。几片凋零的树叶像是爬行在地狱中的游魂,被萧索枯寂的灯火映衬着。这是街市中的一处胡巷,孟洪奎站在被阴暗所笼罩的墙壁旁,仔细的察看着街上的动静。作为本地知名的财神爷,他向来是要脸面的。虽然最近常蛰居深府大院,但平日里也常有走动。每次出行之时,孟老爷总会坐上八人抬着的红顶大轿,甚是风光的排场而出。可谓前呼后拥狗百条,人海一片呐喊声。回想昨日之奢雅,再看今时之窝相,孟洪奎不禁唏嘘万声感叹,心生千层落差。这万一被路人识出,岂不丢了身份,辱了家门。随着一阵冷风袭来,那孟洪奎蜷缩着脑袋,直将自己朝脖颈间压了过来。再看这眼前的街市,已无昨日的繁华。冷清的街道顺着月色的凝重铺将而开,昏暗的灯火眯睡着疲惫的亮尖,不时的跳动着。那原本热闹的门面商阜竟也变得空落起来,不再有人头的往来窜动,不再有鼎沸熟悉的吆喝声。除了一抹萧瑟的凄凉,更多的是繁华落尽的沧桑。再看那街道中央的“无量须弥座”,此时早已破败不堪,再无曾经的色亮与鲜灼。这是孟洪奎特意用汉白玉为“藏金明王”雕磨而成的,其高三丈,宽五尺,一片金色的睡莲犹如冰砌而成的美玉,冠顶在大坐的中央。每逢春秋法会之时,那被奉若神明的“藏金明王”总会身披红色圣云袍,头戴黄色尊者帽。在无数善男信女的虔诚跪拜中高坐在睡莲之上,以示自己的尊魅和威严。然而,出乎孟洪奎预料的是,再历经半年不到的时间里,这原本繁华的“天途圣藏”不仅破财凋零迅速衰落,连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险些随它而去,成为欲望吞噬下的陪葬品。唏嘘哀叹之余,却听一阵嘈乱直入耳间。孟洪奎闻声望去,但见那“金王庙”附近的烟馆里突然跑出一个人来。这人跑的甚是狼狈,此时正赤脚裸踝的朝“无量须弥座”下狂奔而来。其身后紧跟着七八个彪形大汉,他们手拿棍棒一路追赶,面色俱戾间像极了发疯的狼狗。不多时的功夫,这人便躲进了座下熟睡的人群里。那是虔诚的一群信徒,再听说“藏金明王”闭关修行之后,他们便在此搭建起简易的窝棚,只盼活佛早日出关。其多是一些破产的商贩和佃户,今日之遭遇也多是吸食福寿膏所致。这突如其来的一阵杂乱,顿时将座下熟睡的信徒们炸将开来。但听骂声连绵,哭声震天,更有甚者直接拎起了手中的家伙,开始同那些大汉们厮打起来。“你们这群吃人不吐骨头的夜叉鬼,迟早要遭报应。朗朗乾坤,佛爷座下,岂容你们这些小怪倒弄烟土,祸害乡邻。”人群中突然有人大骂道。“乡亲们,我们今天就杀了这些夜叉鬼,再烧了那孟家的烟馆,也好为光了这佛爷的门面。”又人跟声附和道。话音刚落,但看一众人等黑压压的围将过来。随着一阵激烈的打斗,那原本气势汹汹的彪形大汉们已被撂倒了五六个。剩余之人见此情形,纷纷扔了家伙,连滚带爬的逃入烟馆里去了。“走,烧了这孟家的烟馆!毁了这吃人的魔窟!”人群之中又爆发出一阵呐喊来,却是民愤犹若干柴积,只等危处一把火。但看这些虔诚的信徒们好似吃了烈酒的羊,正齐刷刷的朝烟馆前涌将而来。就在这一片混乱之际,突听一声枪响从街心传出。众人惊愕寻看之时,又见一薄衣着装之人正手举长枪,于远处迎风而行。其面色肃然,步调凝重,瘦削的身体犹如从坟中爬出的骷髅,被昏暗的灯光肆恣的啃嗜着。来者不是别人,正是那烟馆的始作俑者孟洪奎。孟洪奎之所以弃了脸面挺身而出,倒不是为了是顾全大局平息冲突。反倒是他害怕这群无家可归的泥腿子们真的把那烟馆付之一炬,到时候别说这辛苦积累的不义之财将蒙受损失,即便是那库存的福寿膏一旦出了闪失,也够他喝上好几壶。想到此处,孟洪奎再也站立不住,他只得豁出廉价的尊严和面子,准备同这群乌合之众拼上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