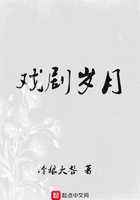蛤蟆神情紧张的坐在沟前的土坡上,不停的朝四下寻望而来。这种感觉简直就是脱了裤子在街上蹲大号,等翔飞出了一半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正在被直播。想跑跑不掉,想拉又出不来。痛苦犹豫之时,却看到沟下的乱草丛中突然跃出一道细微的亮光来。说来也怪,但见这光有小而大,似是那聚集的萤火融作一团,正滚着圈儿,打着转儿化作一个身形佝偻,面目狰狞的和尚来。蛤蟆被它晃的眼睛疼,忙大声祈求道:“鬼老爷,你就放过我吧,我只是一个卖草帽儿的。你说咱俩素昧平生,即无冤仇大恨,更无小节纠葛,为啥抓着我不放呢?”那和尚一听,突然发出咯咯咯的怪笑来。这声音就像是被捅进了刀子的猪,直钻的人头皮发麻,后背汗出。蛤蟆只觉得一道道刺骨的冰凉从后颈斜插入脊骨,犹如蠕动的巨大的虫子般的不停的在身上窜来窜去。“刚刚听到你在这里吹牛逼,以致于扰了我的好梦,便爬上来看看你的手艺。”那和尚终于开口说话了,他迈着轻盈而又细碎的步子,不断的朝蛤蟆走来,那一身破烂的地主袄像是被撕破的棉花套儿,被皱巴巴的印满了“福字”的铅红色外皮寒酸的包裹着。“我哪敢在您老的地方……吹……吹牛逼……爷爷一定是听错了。”蛤蟆结结巴巴的回应着。就在他话音刚落的一瞬间,但看一张枯树皮般的白色大脸正依偎在自己的额头前。蛤蟆直觉得脑子一沉,屁股一紧,几乎将那天灵盖给抖了下来。“牛逼谁都会吹,可吹破的牛逼不一定谁都能缝。”那和尚沙哑着喉咙,一字一钝的望着蛤蟆接着道。“我看你这帽子弄得不错,想必也有两把刷子来。今天你我在此相遇,也是不可多得的缘分,借着这个机缘,老朽正好托你操办点家务小事,不知能否允应与我呢?”蛤蟆自觉已是踏入鬼窝,却又不知这老鬼葫芦里卖的啥药,便醒着头皮,战战兢兢的接话道:“鬼爷有事尽管吩咐,我虽手拙技劣,却在干活这事上从不含糊,只要是我能办到的,必定竭尽全力,不然我就是吃屎长大的。”“那你看我这头发可还能补补缝缝?”和尚歪斜着嘴巴,拍了拍光悠悠的脑袋道。蛤蟆一听,不仅觉得好笑起来。他心里暗度道:“这老鬼定是没事找事,拿我消遣来着。我一个缝草帽的,哪有本事给他植头发呢?这和为火车补胎,给蚂蚁上环有啥区别?可是……一旦说了实话,定没得活路。与其坐以待毙恪守人伦,倒不如说句鬼话耍它一耍”。“爷,这事好办,只是今天来的急,没带那吃饭的家伙,要不你随我进村一趟,我给媳妇说说,剪点她的头发给你些。然后再用针线加以缝合,只需片刻功夫便能起活儿。”“嘿嘿……后生,你莫不是想趁机把我骗了去,待前脚踏进了你家的狗衙门,再来个瓮中捉鳖不成?”和尚一脸诡笑的望着蛤蟆,然后竟慢慢的将头皮一点点的扯了下来。但见那鲜血淋淋的脑瓜子上,一道道红色的经络正如炸开的西瓜皮,不断的渗出白色的汁水来。见此情景,蛤蟆哪敢再看,他只觉得腹中一阵抽搐,嘴里一股腥咸,接着便是吼吼吼的一番猛吐。那和尚见状,又发出厉声的尖笑道:“头发可以晚点补,但这脑袋今天必须帮我修修,你看看它拉的我的脖颈都快断了。”话语间,忽听砰的一声闷响,接着便是如死水般的归于寂静。蛤蟆不再听到那和尚杀猪般的戾笑,他只觉得脚下有个东西硬挺挺的直朝脚面砸来,待其定睛细瞧,便鼻孔哼的一声进气儿,两眼唰的一阵黑儿,整个人犹如泄了底的锅,正噗噗噗的吐着白沫,被那漏下的浆糊瞬间包裹着。蛤蟆就这样在一个触电般的蹬腿,一泡火辣辣的热尿,一声无助的尖叫中……迎来了他解脱性的晕倒。
等蛤蟆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家中的床铺上。此时,他的老婆正掩面而泣,一旁的龟毛也和众族也人站于屋中焦急的等待着。“哎呦,我的哥耶,你终于醒了,可把大家给吓死了。”龟毛半蹲着来到床前,差点没把蛤蟆吓的跳起来。他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再加上皮肉的肿胀,简直就是一个大猪头。“你……小子……这是被尿憋到头上了嘛,咋这么吓人呢!”蛤蟆没好气的翻着白眼道。“你就别怪他了,这不都是为了你吗?”蛤蟆的老婆拿着手帕,继续哭哭啼啼的接着又道:“龟毛昨天晚上回来报信,刚刚到家门口便吓的一头昏死过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最近咱家的老母猪正处于发情期,它看到晕倒的龟毛,便使着劲的将他往窝里拖。隔壁六叔以为是有贼偷猪,又喊来兄弟们过来抓贼。哎……大家不分青红皂白,只将他是贼了,憋足了劲儿往死里打。打了半天,才发现是自己人。”那龟毛听闻嫂子这么一说,也跟着挤出泪儿来。“是呀,哥……我本来都被他们打醒了,方要喊话解释,不知哪个不长眼的又出了损招儿,硬是将一大口猪粪塞到了我的嘴巴里。呜呜呜……这才耗磨了大半天的功夫,以致于让你在那里受了那么久的罪。”看着哭泣的老婆与堂弟,蛤蟆只摆了摆手不再说话。想必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他已不想再有任何的回味。很快,蛤蟆的这段诡异经历便在村里传开了。有人说:那天晚上等大家赶去救援的时候,发现蛤蟆被吊在沟前的一棵歪脖子树上,险些断了气。还有人说:那是沟里的“卧财鬼”耐不住寂寞,就是抓人取个乐。而这样的鬼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但凡被其捉住的人,只要能经得住它的“折磨”,日后必定富贵。还有人说:蛤蟆压根就没遇到鬼,一切都是他和龟毛吹牛吹出来的。然而,无论大家怎么说,有两件事是不争的事实。第一:在解放初期,确实有一位黄姓的地主在那里被砍了头。据知情的老人们回忆,黄姓地主临死前,确实被平日里压榨过的佃农给吊在了房梁上。他们用绳子拴住他的头发,几乎将整个头皮都给揭了下来。第二:自此以后,蛤蟆放弃了做草帽的营生。他带着龟毛投身于刚刚兴起的建筑行业,没过几年便成了村里的首富。又过了几年,村里发大水,支书孟凡天带领村民挖沟引洪,将水统统灌进了“泣魂沟”中。经过岁月的洗礼与时光的变迁之后,这里也早就变换了原来模样,除了最北段的一处洼地外,它几乎被风沙填平了。和当年相比,少了地势的凶险与怪戾,多了现在的平常与无奇。再后来,村里的五保户“刺猬爷”在这里种起了甘蔗。支书看他孤苦,还为他在这里修建了房子。不管怎么说,总算多了一点“人气儿”。只是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他常看到蛤蟆兄弟在这里偷偷的斟酒祭奠。或许,正应了那句传言:那黄姓的地主就是所谓的“卧财鬼”,后来蛤蟆为他缝好了脑袋,料理了遗骸。而作为报答,他将生前所埋的几个大金锭赐予了这对有缘的兄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