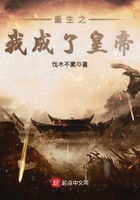当晚,朱伟迪自然是去了田妃那里。
皇帝突然的示好让她有些吃惊,不过让朱伟迪稍微有些不满的是,这女人还是老样子,一路上都摆着张冷冰冰的脸。
屏退了左右后,朱伟迪决定和他好好谈谈。
“爱妃可是恼了朕?”
田妃一听不由大骇,急忙下跪,“妾不敢,不知妾犯了什么错……”
朱伟迪一把扶住她,“爱妃没有错,朕冷落了你,是朕的不是。”
田妃闻言又要下跪,不过朱伟迪却是一把从正面抱住了她。
田妃不敢挣扎,只是低下头,小声说道:“妾不为圣上所喜,是妾的不是,万万不敢恼了陛下。”
朱伟迪轻轻抚摸着田妃的后背,轻声道:“朕有那么可怕么?伴君如伴虎。那是说的寻常君王,不是朕。朕虽说冷落了你,不过可有一次责骂过你。”
田妃见朱伟迪不像是在生气,心里安定了不少,“陛下仁爱,从未责骂过妾。”
“让你受委屈了,便是我的不对,不要再争这个。那个不喜,只是从前朕好恶分得太明,见你与皇后不和,才有所迁怒。今日朕已反省过,不会再冷落了你。”
说完朱伟迪便感到田妃刚放松的身子又紧绷起来。
“妾不敢与皇后有争执,更不敢冲撞皇后。”
“那便好,”后妃的争斗哪是这么简单一句话便能消弭的,朱伟迪也不说破,轻轻放开她,拉着她走到床边坐下,“不说这些。朕近日忙昏头了,爱妃家人来京多时也未有个好安排,这是朕的不是。明日朕便下旨再赐些宅邸田产,也好让爱妃不再心忧家人。”
田妃一听,自然是欢喜不已,脸上终于有了笑容,“谢圣上恩典。”
“爱妃应当多笑笑,你笑起来很好看。”
田妃这还是第一次得到朱伟迪的称赞,脸上不由一红,低下头道:“妾知道了。”
朱伟迪一把把她搂进怀里,在她耳边低语道:“人活着都不易,便是朕也有诸多苦楚,也总想找个人说说。爱妃若是受了委屈,说与朕知道便是,把话憋在心里,总是不好。”
田妃被朱伟迪这句触动了伤心事,眼睛里已经泛起了泪花,却还是强压着情绪低语道:“妾没有委屈,有陛下怜妾便够了。”
感受到怀中的少女正在轻轻颤抖,朱伟迪怜惜地抚摸着她的后背,“哭吧,便是男儿到伤心处也是有泪的,人不怕受苦,只怕老是憋着。”
这一夜,朱伟迪没有和田妃行房,只是和她扯了会家常,耐心地哄她入睡。一夜好眠之后,两人的隔膜也少了很多。
依照传统习惯,每当遇到日食、月食,皇帝都应该对自己的统治情况进行一番反省。
朱伟迪即位未久,值得反省的地方也只有怠政,不过他不是朱元璋那种强人,没本事整日处理那些乱麻一般的政事,对文官们的提醒直接无视。非但如此,他还把邓玉涵预测月食的方法还有自己命人写的月食成因传抄,给每位有品级的京官,还有各省官员,一人一份。
北京城的十二月是非常寒冷,比之现代要冷得多,朱伟迪老早就包裹上厚厚的棉衣。
从空间里取出的羊毛工匠们还在研究如何纺成线,羊毛衫短时间自然是不要想。朱伟迪也让人试过那些土生土长的蒙古羊,工匠们称要把蒙古羊的毛纺成线难度非常大,无法纺线,而皇帝拿出的羊毛或许可行。
朱伟迪在入冬后就特别强调过不能出现冻弊的贫民,早拨下大把的钱和棉衣,加上厂卫在北直隶查探得非常频繁,户部自然不敢怠慢,加之如今北直隶粮价便宜,愿意做善事的人也多了起来,整个北直隶倒毙的乞丐数量比往年少了许多。
各种工坊都还在筹建中,一时间招人也不多,不过京师到山海关的道路修建却是已经开始动工。大量的民夫被征集,从东江过来的辽民也在陆续投入道路修建工程。
当然,这些民夫的温饱问题朱伟迪一直都很关心,多番派出厂卫和甚至亲信太监前去查看他们的生活。效果他不敢保证,现在他也无力彻底整肃大明的吏治,不过起码要求个心安。
由于户部今年还有些节余,京城到大运河终点通州的道路修建也被提上了日程。
月食后第二天,有关蒙古形势的情报终于被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上报。也没有什么新鲜事,无非是林丹汗迫于饥荒大举进攻蒙古右翼诸部,很多部落已经投向后金。不过好在此时赵城之战还没开打,蒙古左右两翼主力还都没受损。
还有两起中等商人的走私案件,骆养性说是人已经因为反抗被就地正法,报上来的情报显示他们和晋商没有勾连。
至于朱伟迪要的具体的丁口数,一时间自然还不能查清。
听完报告后,朱伟迪面无表情地看着骆养性,“你上报之事,兵部大多都已探知,朕给你四十万两银子,你就是这么给朕办事的?”
说着他顺手将桌子上的茶杯一把扔到地上,摔了个粉碎。
他生气的是,他在怀疑骆养性顾及着晋商在朝堂上的势力,把晋商勾结后金的人证灭了口。蒙古是后金和大明走私贸易的中转站,骆养性派人去查了,似乎不应该半点消息都没有。
骆养性一听顿时吓得面如土色,慌忙跪下磕头,一边磕头他还在一边为自己辩解,“臣办事不力,只是时间仓促,臣一时还难以调齐人手。还望陛下开恩,给臣些时日,臣定将陛下吩咐的事都办好。”
“好,朕便再宽限些时日,草原之事干系重大,不可以怠慢。朕再说一次,对鞑虏任何手段都可以用,派去建奴那边查探的人手也不要少了。”
骆养性这才停止磕头,“臣领命。”
“朕要有些话,你要记住,要记牢了。这天下是朕的天下,锦衣卫只需要听朕的。你慢慢把你手下的那些个和外臣走得近的,便是稍有嫌疑,都要给朕弄出北镇抚司,一个不能留!朕的耳目也不止锦衣卫和东厂,若是朕发现你有事瞒着朕,那便休怪朕对你不客气!”
骆养性心里咯噔一声,又是重重地磕了一个头,“臣万万不敢欺瞒圣上,锦衣卫是天子亲军,万不敢胳膊肘往外拐。”
“起来吧,”
见骆养性谢恩起身,朱伟迪直视着这个特务头目,“只要你把事情给朕办好,朕能给你的很多。要知道,锦衣卫也未必非得居于东厂之下。”
威吓过后,自然是要给根胡萝卜,虽然是吊在眼前的。
锦衣卫沦为东厂附庸已经多时,若是锦衣卫重振当年的雄风,这锦衣卫指挥使又会是何等的威风。
忍着心里的狂喜,骆养性还是故作淡定地回话道:“为圣上办事是臣的本分,臣不敢向陛下邀赏。厂卫皆是陛下的耳目,位次自当是由陛下乾坤独断。”
朱伟迪点了点头,“下去做事吧。”
待打发走骆养性后,朱伟迪喊来了高时明,问了问曹化淳走到哪了,要他派人去催一下,让曹化淳加快步伐火速进京。
他此时已经有了重新组建一个特务机构的想法,如果这个骆养性还是不知好歹,他也不介意把他拖出去砍了,不听话的情报部门头目是坚决不能用的,此时这骆养性已经露出了不好的苗头。
此时蓟辽和宣大两个方向的调解人员已经派出,漠南蒙古两大势力都还在和朝廷谈条件,朱伟迪写了信给孙承宗和王之臣,要求也很简单,除了兵器和多余的口粮,无论两边是要钱还是要各种奢侈品都可以答应。
稳住林丹汗和右翼诸部联盟,这是当务之急。此时草原形势已经非常明了,漠南蒙古的两大势力之间已经是水火不容,他们斗个两败俱伤,只会让后金捡到大便宜,大明得不到半点好处,只有尽量答应他们的条件。
至于那些已经彻底倒向后金的,朱伟迪倒是想出兵干掉他们,不过那些部落都在靠近后金的一侧,出兵风险实在很大,如今政局才刚刚稳定,他还不想冒这个风险。
月食的事情一样在大臣中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对皇帝违反惯例未下诏自省,阉党不置一词,而非阉党势力的,大多都上书批评。
对那些聒噪的苍蝇,朱伟迪自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无视。
当然,朱伟迪发下去的天文学论文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东林和保守人士一致地表示这是皇帝的借口,并大肆抨击传教士妖言惑众。只有少数几个东林当的文官从学术上支持了皇帝,不过还是死咬着月食就算是自然的天象,也是上天定期的示警,皇帝依旧应该自醒。
至于阉党,倒是有不少跳出来支持了皇帝的行为。从言论上看,似乎是把那篇文章好好读了,也基本认同地圆学说和地球绕着太阳旋转。不过他们的政治目的也同东林一样明显。
对厂卫报告的大明官场众生相,朱伟迪丝毫不觉得意外,这帮人的德行他早见惯了。
他们这些没有廉耻的文人,特别是东林党的“君子”们,最喜欢的便是高举道义的大旗为自己谋取私利。世界上最不缺的便是这样一群伪君子,这个时代有一大把,后世也一样的不少,中国很多,外国也同样多。
人性便是这样,古今中外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