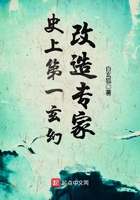(一)
是却说忽必烈建立大元都以后,为了解决南粮北调运输问题,开通了杭州到北京的新型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修在积水潭,而积水潭的万宁桥正是京杭大运河最北边的一个闸口,从元代起,这里逐渐成为交通要津和繁华的商业区。河内是商船蔽水,岸上是车水马龙,酒肆茶棚、商贾戏班云集,热闹非凡。
海子附近一处勾栏院,门首挂着许多金色帐额,屋檐下的灯笼在风中摇晃着。园子里按着那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坐得满满登登喝彩的戏迷。
珠帘秀.《望江亭中秋切鲙》,弦索动处,只见一个袅袅婷婷的丽人:扮作谭记儿,正在痛骂贪色弄权的杨衙内:“有这等倚权豪贪酒色滥官员,将俺个有儿夫的媳妇来欺骗。他只待强拆开我长搀搀的连理枝,生摆断我颤巍巍的并头莲;其实负屈衔冤,好将俺穷百姓可怜见!”歌喉宛转,腔依古调,音出天然。“好---啊”,勾栏里爆豆一般喝彩。
台下翰林院的王元鼎先带头喝起彩来,同来的翰林院阿鲁威也跟着喝起彩来。
沏茶小二穿梭在堂间,一张嘴乐得合不拢,这边添茶,那边添瓜子儿、糖豆,忙得十分带劲儿。
今天大堂下坐得满满当当,就连沿墙一溜儿高凳也全是人头,挤得瞧不见一丝缝儿。
坐在最前排,浙江才子叶子奇用鄙夷不屑的眼神看着穿着官员服装王元鼎和阿鲁威,戏台上杂剧映射着大元官员和妄议朝政的言论,作为元朝官员竟然也听的如醉如迷,可见元朝官员没心没肺到了极点,还把交子一股脑的直往台上扔。
叶子奇是浙江龙泉人,本是饱学之士与青田刘基、浦江宋濂同为当时元朝齐名的学者。通州文靖书院元里人总管赵密多次邀请,来通州讲学,今天赵密看他多日讲学辛苦,特意请他勾栏院看戏。碰到了翰林院的王元鼎和阿鲁威。“喲,这不是王大人和阿鲁威大人吗?”二人回头原来便是许久不见的文靖书社的元里人总管赵密。王元鼎惊喜而出:“赵兄,听说你请了浙东的叶子奇先生讲学,这位大概就是吧。”赵密笑道:“是呀,阿鲁威大人,今日可好呀。子奇兄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蒙古人阿鲁威。”叶子奇居住浙江,江南一般极少见蒙古人,身为南人对蒙古人一向反感,淡淡的回道:“失敬失敬,原来是阿鲁威大人”王元鼎在一旁补充道:“叶子奇是浙东人,据说静斋弟尝师王毅,明“理一分殊”之论旨,悟圣贤之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不涉猎,且多有造诣。医学也不错,我二人早就想向静斋兄讨教了。”正在这时,楼中的众多看客忽的喧闹起来,从大堂又传来喝彩声,让四人也转过目光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只见天井正中的戏台上空无一人,好像已经一曲唱罢,众人纷纷要求继续演戏,王元鼎大声喊到再来(高祖还乡)吧。叶子奇感到好笑又好气,这阿鲁威作为蒙古人肯定是“重脚跟”出身,也就罢了,你作为汉人也不懂这是嘲讽当世官员的杂剧吗?
此刻已是午时,屋外艳阳高照,王元鼎说道:“前面“海子”街区有一个新酒馆不错,咱们去吃酒攀谈,如何。”赵密笑道:“王大人有请,我们敢拒绝吗,走,咱们去坐坐。”
叶子奇跟着走出戏堂,只见“海子”的街区酒肆林立,酒客如织。四人在酒馆楼上靠窗的厢房坐下,点了柳蒸羊,炎羊心,菜,烤牛肉等等,当然也少不了香甜滋补的松醪酒、品目繁多的黑酒,——马奶酒。窗外运河上传来清晰的摇撸声,远远看见河面上被太阳照的一片金光。赏景谈天,不一会变酒酣耳热。王元鼎叫来酒楼歌甜貌美的郭氏顺时秀歌姬,问道,“可有好听的新歌吗?”顺时秀也不啰嗦,稍稍舒展了一下胸口,轻咳两声,朗声吟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首诗一出,整个厅堂里的气氛为之一变。四下里静得有些压抑,过了一会王元鼎仿佛回过神来,笑道:“都说商女不知亡国恨,你这鸟女子,何时也忧国忧民起来了。”
叶子奇几杯酒下肚,脸上泛上血色来,听了王元鼎的话不无感慨地叹气道,“天下承平已久,法度宽纵,人物贫富不均。来通州之时,一路饥民遍地,古之贤者之为贤者,在于天理与人欲分开呀。”王元鼎当然听出这话暗讽他们骄奢淫逸,但他素养极高,早已超然于一切虚荣之外。他和阿鲁威也不是高官,向来有志难酬,所以也不在乎他的话。在他的印象里像叶子奇这类人都是想入非非,和现实生活很少接触的人,于是说道:“晚生平生随性,近些时候作了一首诗,不成体制,念给大家,不要见笑。”说完吟诗道:
“正宫·醉太平
花飞时雨残,
帘卷处春寒。
夕阳楼上望长安,
洒西风泪眼。
几时睚彻凄惶限?
几时盼得南来雁?
几番和月凭阑干!
“好诗,王兄果然是多情人。”赵密笑道。“晚生随性而作,让先生见笑了。”王元鼎回答。
叶子奇道:“无妨,无妨,诗以传情,未必都要像东坡那样,大江东去的豪情。”叶子奇转向阿鲁威道,“大人也是翰林院,向来一定诗做的也不错吧?”阿鲁威知道如果不拿出真实才学,恐落笑话,答到:“正好近日也做了一首诗,与各位切磋。”说完吟道:…………“问人间谁是英雄?
有酾酒临江,横槊曹公。
紫盖黄旗,多应借得,赤壁东风。
更惊起南阳卧龙,便成名八阵图中。
鼎足三分,一分西蜀,一分江东。”
“好诗”赵密嘴里不住“啧啧”出声,叶子奇没有言语,不过内心深处,还是忍不住的震动。“此调基调雄健高昂,有苏轼“大江东去”的遗风,而无“人生如梦”的感叹。一个蒙古人能做出这么好的诗来,可见此人并非无能之辈。
叶子奇逐笑道:我曾在家乡富春江游玩,得见严子陵的故居,遥想当年严先生与东汉帝刘秀同游学,刘秀继位,严子陵不愿出士,为何呢?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说罢,举著击孟高声唱道:
君为利名隐,我为利名来。
羞见先生面,黄昏过钓台
四人直喝到月亮升起,方才尽兴而散席。当他们走出酒馆时,晚风和着酒香味迎面而来。歌女顺时秀对王元鼎轻轻道:
“相公,我最近想吃马版肠充馋。你能留下来吗?”王元鼎大声道:
“好了,就把我的五花马给你留下了,明天你让人杀马吧。”
叶子奇看到这里无奈的摇了摇头说道:
“男女授受不亲,不讲儒家礼仪。一个人不知礼,不行礼的话,即便你能说会道,那也与禽兽无别。”
(二)
外面的暴雨一直不停的下着,电闪雷鸣,狂风吹得宫外的树叶都弯下了腰。躺在床上的元惠帝,童年的阴影一直潜伏在他的内心深处,元英宗被杀,父亲的死,母亲被逼喝毒药,黑衣侠客。这些疑案一直沉沉地压在元惠帝的心头。总是隐隐不安。
近臣阿鲁辉帖木儿见元惠帝一直闷闷不乐,以为他又犯头疼病了。于是多次推荐叶子奇,元惠帝决定召靖林书院讲学的叶子奇进宫。皇帝一般是不会请宫外的医生看病的,毕竟要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但是也会有特殊情况。如果御医也没办法看好病,就只能请宫外的医生了。听说皇上总是头痛,王元鼎向阿鲁辉铁木儿说起了叶子奇的医术。
叶子奇穿着蓑衣跟着太监朴不花走到皇上居住的御书房,“皇上召见你吧,快进去吧。”叶子奇轻轻的点点头:“好。”走进御书房,御书房里一股潮湿味道,蜡烛的火焰随着开门的风轻轻的摇摆着。满殿茶香沁人心脾。皇帝正手捧奏章批览,闻得脚步声,抬起头来:
“叶先生,朕今日头有点晕,你来给朕瞧瞧。”叶子奇应声走近皇帝,看皇帝精神不振,眉头紧蹙,嘴唇泛白,轻声道:
“皇上是否心神不宁,脑中时乱时常?”
皇帝点点头:“是啊,朕几乎每过一段日子都会这样,最近就经常心神不定。”
“前两日钦天监推算出,近日有妖孽之患,需一名法力高强的术士方可避此劫数。叶子奇越加确定皇帝的心疾。
“小民见皇上,印堂无光,眼下青黑,色虚体弱,眉眼之间隐约可见一层黑气萦绕不散。怕不是体弱,而是妖邪缠身。”
“人情大体上是畏惧就会心乱,心乱就会神散,神一散鬼魅就可能乘机而入。
不畏惧就会心定,心定就会神全,心神专一邪气就无从入侵。皇上且放下手中奏章。”
叶子奇说罢坐到元惠帝的身边道:
“你闭上眼睛,不要想事,我行功给你治病,闭上眼睛,让微臣给皇上揉揉穴。”
元惠帝只觉得一股灵气注入,体内的龙气渐渐地规律起来。
感觉之前体内心神不定的邪气,正在慢慢降下去,一点点地。一点点地安定下来,太舒服了。
“叶先生你还真有法子,朕可清醒安定了不少。”
面对这个少年天子,叶子奇有一种恍如如梦的感觉,内心努力的把他和想象中的真龙天子联系在一起。
“听说先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知。你说为何我朝最近不是干旱就是洪灾。江湖人传有莽古斯(魔鬼)要作乱,可否真有此事。”
元惠帝问道。“一般龙见事件,就会发生干旱或洪涝。历朝历代莫不如此。至元二十九年,太湖曾见蛟龙出海,淹没了沿湖一带的农田,接着至元三十年又发生两起见龙事件,均让周围的州县遭遇干旱或洪涝灾害。幸而师祖在世,群龙听命。现在过去很多年了,虽然有干旱洪涝之灾,但不见有见龙事件,可见我朝天命仍在,只要皇上发疯图强,仍然是龙主,不必担心。至于莽古斯(魔鬼)作乱无稽之谈。”
说完叶子奇眼前浮现出那些吃着草根和树皮的饥民,他们衣衫褴褛流浪在街头上。
“希望皇上做好三点事,安置好饥民,现在不少饥民死后暴尸荒野,街头。没有人掩埋,还应尽快完善科举,科举对于儒生,寒门学子来说,就是转变命运的机会,也是报效国家的途径,多用那些中举的儒生。存天理、灭人欲、严教化”,整治吏治,吏败治坏,就会讼不平,河道不修,四海之民就有不安,这三点处置不好冒犯了和气,就会容易天怒。以致天旱或洪涝”。
元惠帝这么多年以来,心胸满闷,气机不畅,听了叶子奇的一席话,有豁然开朗的感觉。
“叶先生你还真有法子,朕可清醒安定了不少,叶先生可否留下辅佐朕。”
“小民乃一介书生,朝廷虽然举办科举,但并没有真正用儒生,臣有朝一日中举,定来辅佐皇上。”叶子奇回答道。
对于权利,叶子奇是丝毫不感兴趣,他对大元朝冥顽不灵感到吃惊,他们出乖露丑,居然不按儒家礼仪行事,没有三纲五常,不用儒生。这个世界运行应该按儒家的法则,改变儒家运行规则的要遭到上天惩罚。待到靖江书院讲学完毕,就远离是非,快意江湖。想到此,叶子奇嘴角微微翘起,起身磕拜告退。
“皇上,奇承娘送来茶水,已经等候多时了。”元惠帝连忙召见奇承娘,一进门奇承娘便抽抽搭搭的落下泪水,在皇帝怀里说道:
“皇上,奴婢是觉得对不起皇上,皇上病重,奴婢却是无能为力,奴婢心中有愧。”
皇帝轻轻抚着奇承娘的说道:
“爱妃说的什么话,难道朕会埋怨你吗?不要哭了好吗?”
朴不花问道:“今天晚上去总王府吗。”皇上回答“今天必须去。”奇承娘连忙说:“那我也陪皇上去吧。”
天色渐渐地暗下来,雨水渐渐减弱,不时打着闪雷。宫里早早点上了蜡烛。元惠帝带着朴不花,起承娘,全真教的完颜德明大师。绕过御花园,来到元明宗旧府,传闻这里明宗的娘娘死的冤枉,所以夜晚时候没人敢来这里。
元惠帝带着朴不花来到宗王府。“宗王府”三个字凄凄地映入眼帘,似沉淀着一生的沧桑与伤痛,当初自己没少在里头跑上跑下地疯玩,可如今已是满眼残破,衰败的气息。更悲哀的是,现在没有人敢居住在里面了。淡淡的雨水敲打在朱门地面上,灰暗的房檐啪嗒啪嗒地滴着水。元惠帝轻轻走近朱门,伸手触摸着上面的岁月痕迹,心凉如水。母亲,儿子来看你了
奇承娘脸色苍白紧紧地靠紧元惠帝,她瘦小的身体不断打着寒战。她的辫峭上蓝色结已经松开,柔软的长发被细雨打湿粘贴在潮湿的脸硖上。
院子里漆黑一片,安静的可怕。完颜德明拿着的摄魂铃挂在门上。拿出两张黄符,大师点了三根香,朝着四方拜了拜,把香插到了香炉上。随后取出一叠黄纸,在几处门上贴了起来,一直贴到那件昏暗的屋子之后,黄纸忽然燃烧了起来。“大师,有什么问题吗?”朴不花见完颜德明脸色有些不对,开口问道。
“我好像看见一个女人在院中哭泣,现在又戛然而止,好像是幻觉。但是我清楚的知道,那绝对不是幻觉!难道是这里怨气太强了,我怕我镇不住她。皇上您快把贡品献上,念到念到。”完颜德明道。
元惠帝呆呆的站在院子中央,泪流满面。摆好三牲祭品,一壶宫酒。然后点起了一推黄纸。
“娘,儿子来看你了,你有什么冤情就放下吧,儿臣会给您讨回公道的。”
奇承娘站在院子中央,愣愣的看着元惠帝,寄居他乡,漂白无定的感觉一直缠绕着她,恍惚中她似乎回到那大海边飘浮着鱼香的故乡。仿佛回到远在高丽国的父母身边,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没有劝解元惠帝。他知道至情至性的元惠帝,内心深处的郁闷压抑太久了,痛哭一场,或许是一件好事。
忽然一声门响,一位宫女装扮的中年妇女,蓬头垢面慢慢从另一个门里走了出来,元惠帝吓了一跳。那女子目光呆滞地望着这边火光,火光里只见她一直哭哭咧咧的,不停地叨念着那几个字,清丽的容颜上布满了哀伤,看样子好像精神不正常了似的。
一道闪电照在她的脸上,呈现出几许苍白,元惠帝紧紧盯着她喃喃道:“佩环你还活着。”还没等到回答,急忙地抓住她的手:“佩环,你快告诉我,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我到底是不是他的儿子。是不是,是不是?”。
宫女眼里闪过一丝恨意,忽然拉住元惠帝的胳膊:“你要给你娘报仇,她是被皇后毒死的。元明宗流落西域的时候,在你父亲赵显庙中,看见你母亲住的房子有五彩龙气,于是求赵显把你娘赠与他,当时你娘正怀着你,被元明宗接到他府上的。金叶翠花锁就是证据,这是宋室皇宫之物。当时还有虞集的大臣知道这事。”黄姑抽噎说着。
回去的路上,元惠帝缓缓的走着,陡峭山石,传来湍急的水流之声,元惠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忍不住有些慌乱,额头之上隐隐冒出冷汗。他拿出金叶翠花锁狠狠的向河中扔了过去,金叶翠花锁瞬间化作一条抛物线,飞了起来。
“嘭”的一声。狠狠的落在流淌的永定河中。
笼罩在上空的阴云随着风儿悄悄散开,雨水有中止的迹象。几只栖息在屋檐下的鸟儿从院落里飞走,皇宫院落里的花儿在风中拼命的摇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