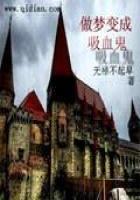余继任望着菜畦,不知心里在想什么。跋扈少年用过晚餐不见他踪影,找了半天。
跟随他的目光,白菜菜叶卷起,把菜心包围的严严实实,拿手指轻戳十分瓷实,满意点点头,却发现萝卜已经有婴儿手臂粗壮,未被土壤盖没露出的部分成暗青色,喜悦之情表露于脸。
拍拍手掌,曹振铎坐在他身边,“青青白白,宛如美玉。”
余继任轻笑摇头,“美玉虽也是青白色,只不过是些石头罢了。岂能和饱餐一顿的粮食相比。”
“石头做成印玺,可掌管政令调度,千万人生死也管得,怎不如田间瓜果。”曹振铎伶牙俐齿,立即还以颜色。
余继任不和他争论口舌之辩,想起和先生的言论,不由道:“赶明儿下山买几只**。”
“**?”曹振铎心中疑惑,又意识到说出粗鄙之语,呸呸道,“养鸡做什么?是拿来除虫吧。”
“不到三天你不杀鸡我跟你姓!”余继任看着这个憨憨少年,怀疑他莫不是个傻子,鸡只吃虫,不吃菜叶?
曹振铎被他目光看得不爽,不择口道:“你孩子跟我姓还差不多!”说完又觉得失言,呸声大起。
余继任丝毫不计较,“鸡生蛋,蛋生鸡,这样就有蛋吃了。”
“还有肉吃。”跋扈少年迫不及待地补充。
余继任用力点头,“母鸡留着下蛋,公鸡杀了吃肉!”
曹振铎闻言一愣,同情道:“小公鸡好惨的说。”
……
“说说你到底来干什么?”徐植出声问,对方大老远跑来,自然不会是和他扯皮吵架的。
孙国富收起嬉皮笑脸,如同换了个人一般冷色肃然,良久开口道:“道宗来人请我家先生回山。不过先生一早料到此事,提前避而不见。”
道宗无论地位还是行事向来超然,隐隐有凌驾世俗权贵之上。徐植听到此言有些头疼,事情麻烦大了啊,不然不至于把理念不同的徐植招回去。
徐植愁眉紧锁道:“徐渭还留下什么交代?”
“先生只道有客西来,吩咐我等候。”说完孙国富考量后,没必要隐瞒必要,还是吐露真言,“似乎时机还不对,先生留给客人说,该出现时他自会出现。”
徐渭那老小子一向喜欢装神弄鬼,徐植冷哼。好在他从言语中推测出不少线索,有客西来?恐怕恶客临门吧。徐植忧心忡忡,难道西边要起什么乱子?
“事情应该没那么糟糕。”徐植不知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孙国富,不过多想无益,既然还没到徐渭出面的时候,想来还有周旋的余地。
“你不知那客人张嘴天下闭嘴大道,对我家先生态度几如何恶劣!”孙国富作悲愤状,愤愤不平道:“既然道宗掌握天下大道,十年前为何不制止甘露变法!眼睁睁看着战事扩大,多少百姓破家?”
“禁言!你莫忘身份。”徐植面色微变,世人恍恍度日,不知天下大道,而他们两个是有资格了解的。
孙国富悲痛不已,盯着徐植一字一顿道:“何为道?又为何我孙家不得道?”
孙家虽世代平良,却靠勤俭苦耕为家训,经历几代人的打拼成为江南豪族,在上一代家主手中达到最盛,从他两个孙子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国富民安。
恰逢天下大变,就在孙家摩拳擦掌准备一展宏图时,却被当时的南梁王找了借口随意处置了,若不是徐渭收下孙家二子,恐怕世间再无江南孙家血脉。
徐植无言以对,叹道:“孙家已成过眼云烟,只有道宗孙国富。这一切都是命吧,命里注定的劫数。”
一本《道德经》,五千言道尽天下法。
《道德经》以道德为纲领,论述修身、治国、用兵、养生之道,被誉为万经之王。后人便以道德开宗立派,也因道德之争分崩离析。
道宗以道为先,认为道是德的生化,修行万物之道‘自然之道,掌管天下大势。
德宗认为德是基础,天下者有德者居之。以德作为万物行事标准,举例上古先贤尧舜禹禅让,又加以五德之说,揭示王权更迭。
在道宗看来德宗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巴结统治者,和道德宗的本意是相悖的。于是道宗指责德宗谄媚诸侯,耻于其为伍。德宗反讽道宗执掌大道不与天下,视其为反贼。
两家分道扬镳。道宗隐世出世,德宗在世间入世行事,逐步演化成百家。
两者同根同源,道宗弟子虽少,地位却高于百家。况且道宗也不屑于跑到晚辈面前耀武扬威,每次道宗下山,天下必有事变。
最近一次道宗弟子下山,就在十年前甘露之变。也不知是先有道宗下山,还是先有天下大变,总之每次有道宗出面,都牵扯不小。
……
“人好多!”潜山镇还是车水马龙,曹振铎一个多月没能下山,此时如同鸟儿归林,在集市上扫荡。
“你小心点!”应付着镇上熟人的问候,余继任紧紧追随跋扈少年,免得一不留神不见他的踪影。
如今书院采办由林家负责后,刘管家直接找上林府对接。如此两人的时间空出不少,曹振铎更是进镇后一刻也没停下来,想把这段时间的遗憾弥补过来。
曹振铎对此说起振振有词。作为世家弟子,他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只是两人生意又扩展了,代那些不能下山的学生购买些东西。
余继任也软了下去,毕竟曹振铎借此自作主张收了不少黑心的跑腿费,五五分账。
等两人回林家汇合时,日头渐西。
“继任,你再不来兰姨可要找上书院了。”刚进门就听到关切的问候声音。
“先生让我教曹振铎他们种菜呢。”余继任讪笑,拉过身旁的曹振铎挡箭,所幸刘掌柜给自己留了面子,没把事情始末告诉兰姨。
曹振铎怏怏白了他一眼,没有揭破同伴的谎言。
兰姨闻言佯怒道:“你这孩子改不了见外,在书院耕种艰难,缺少什么只需吱声,让你二叔差人送去。”
“兰姨,镇上热闹了许多,见了不少生面孔。”余继任连忙转移话题。在镇上生活五年,名字不一定能叫出,面熟是少不了的,只是今日镇上人来人往,许多人见也不曾见过。
“听说南梁和东越两国要打起来了,镇上的人大都是逃避战事,也有是来购买物资的,你二叔几日也没回家。”兰姨心生恻隐,低声告诉他。
曹振铎探出头,对两国交战十分好奇。不等他开口询问,兰姨给出了答案。
“避难的人说是因两国交界之处一处村子,东越村女在河边洗衣,刚好南梁隔岸的邻村有一男子酒醉路过,见女子身段玲珑,一时没管住嘴出言调戏,谁知女子生性刚烈,不堪受辱跳河,得亏那男子反应快救起一命。”兰姨说到这气愤难平,怒骂那男子无赖。
跋扈少年同仇敌忾出言声讨。
倒是余继任更加摸不着头脑,到此不也还好吗?
哪知兰姨接下来的话出现了反转,“可是女子回家便把事情告诉了乡老,乡老告状给了县丞,县丞出面要求惩治那东越男子。谁知南梁县丞不愿松口放人,东越县丞又把事情反应给郡守,郡守嘉奖国女气节,直接出兵要人为其讨个公道。南梁也不愿丢了面子,双方便陈兵边境相互对峙。”
余继任心领神会,潜山镇距离两国不足百里,镇上人多也能说过去了。只是这开战理由过于儿戏,偷瞄曹振铎。
“看什么看!你以为都是曹国人也如此蠢笨?”曹振铎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