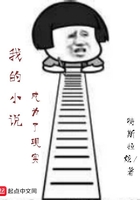安妮和肖娜各自霸占了母亲的一个膝盖,在这个逼仄的船长室里没有那么多空间去摆床,瑞秋坐在航海图桌前面唯一一把椅子上,偌大的英国展现在她的眼前,如果不是他两个叔叔动作太快,她完全可以用这两万英镑在圣乔治海峡或者拉芒什海峡买下一座庄园岛屿,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地理位置优越,爱尔兰的邓莱里和英国西部港口城市斯旺西都是著名的航线物资补充城市,在这个岛上种点葡萄或者棉花都足以维持一个富足的生活,只恨她父亲的那两个混蛋弟弟!
瑞秋不由咬牙切齿,右手紧紧握住鹅毛笔,通红的双眼中蓝色的眼眸充斥着怒火,玛格丽特静静的看着自己怒火中烧的女儿,刚想像以前那样安抚自己的“小山羊”,她抬起的手却僵在了半空,她面前的女儿现在不像是她记忆中的那个淑女,反而像是她无比讨厌的傲慢的法国女人,她还记得那个女人用刻薄尖锐的语言抨击《拿破仑法典》,她认为女人和男人先天相同,性别和生育不是束缚女性的枷锁。
虽然她的某些语言直击玛格丽特心底,但出于淑女的需要,每当这个法国女人挑剔者说出这些语句时,她总是用丝绸扇子挡着脸,当某天她得知这个许久没来的法国女人死在了一场法国女性平权运动中,她恍惚了,不愿相信那个傲慢无礼的女人也会屈服于死神,不过就算那个女人到了死神面前怕也会撩开他的衣摆,看看死神是男是女吧。
冰冷而苦涩的海风吹醒了这位三十多岁的一家之主,她无力的垂下手,轻柔的摸着两个因为营养不良而头发分叉的女儿,不禁悲从中来,她的女儿从今天开始将是一个不能使用姓氏甚至不能被称呼瑞秋的人,她们这四个悲苦女人就像是这艘无依无靠的三帆运输船一样被无穷的大海包裹。
瑞秋不知道她母亲此刻在想什么,她甚至不太清楚自己在想什么,直到上了船,坐上椅子,她才反应过来自己真的完成了离经叛道的行为,欺瞒律师,买通神父,偷窃地契,换来短暂的安宁,但她毫不后悔,从她那两个叔叔兄长刚去世就如同鬣狗一般赶来吞吃他的家产,就可以看出她们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如果瑞秋真的是个淑女,也许现在已经躺在那个瘦的像个竹竿的堂哥的床上了吧!
想到父亲,瑞秋百感交集,她轻轻地挤开椅子,生怕吵醒两个刚刚入睡的小家伙,靠在舷窗上,随着宁静的海浪上下颠簸。此时已经她们从曼彻斯特逃出已经一天了,拉芒什海峡或者叫他英吉利海峡,背面是英格兰,南面是法国,就算是深夜也能看到远处码头闪烁着光芒,风吹起她金色的卷发,她张开右手,五根指头想要去捉住风的飞逝,左手托着下巴,不禁的想起那个顽固的老好人父亲。
从她有记忆以来,他的父亲就一直在资助这个资助那个,今天要帮弟弟的儿子交海军学院的学费,明天要给没有启动资金的“好朋友”注入动力,最开始几年,母亲虽然不赞同但是也不反对,毕竟她就是喜欢她丈夫这一点;到瑞秋十岁左右,两人的矛盾就开始升级,原因是一八三四年因为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特权被取消,属于格林家族的那一份红利也被取消了,整个家庭现在只能勉强的维持体面,连每年的旅游计划都很难实现,更别说什么救济他人,玛格丽特觉得威廉铺张,威廉觉得玛格丽特小气,两人之间罅隙渐生;直到一八三九年,威廉被治安局派人捉拿,罪名是通敌叛国罪,他资助了间谍组织给美国送情报来压制英国工业发展。
就这样,老威廉失去了他的名声和地位,曾经资助过的人也拿这件事情来挖苦玛格丽特,因为在罪名没有摆脱前,玛格丽塔也不再是威廉男爵夫人,只是一个平民罢了,但只要是生活中根威廉打过交道的人就知道,这个顽固老派的老好人,绝不会有任何叛国的想法,最大的不敬就是在每天早上喝红茶时对着报纸发表一句“独到”的见解。当格林一家终于从四面朋友那里借来足够的金畿尼想要保释老威廉时,却得知老威廉自缢了,在他走后的那一段时光,是这个家庭最灰败的日子,失去了经济来源,失去了名声,甚至连庄园都不能继承,她们一家四口蜗居在曾经给法国女人租住的市场阁楼里,每天在鸡粪和喧闹中醒来。
“叩……叩……”,门被突兀的敲响。
“崴列特小姐。”一个蓄着络腮胡,顶着一头鸡窝的男人从船长室破烂的门缝里对着瑞秋微笑。
瑞秋·格林或者说是崴列特·安博,拉开门又悄无声息的走到了甲板上。
她面朝着大海,身边站着这艘船的船长,那个邋遢的男人。
男人头戴着已经洗不白的海军白帽,胸前还别着什么看不清的徽章,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不停地搓着衣角,试探的开口,问:“崴列特小姐,您觉得这艘长蛇号怎么样?”
崴列特并没有回头,只是等着这个揣着小心思的船长说出它的目的。
“额,我是说您这一路上感觉还好吧?”船长小心翼翼的开口,一双带着白翳的眼睛不住地瞥向挺立在船头的小姑娘身上。“您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大可以跟我说,或者您的母亲和您的妹妹也都是可以的。”
老船长还在为该怎么措辞烦恼不已的时候,崴列特已经洞察了他的心思。
根据购岛合约,这艘来往于约克郡和普希里岛的船也归崴列特所有,而据她所知,这艘船和他的船长已经在一起了三十多年。
“对于我来说,船都是一个样子,破烂、老鼠或者其他的什么。”崴列特夜莺一般的声音清脆出口,被海风鼓起的帆和不安的船长都想抗议些什么,但崴列特没给机会,说:“哦,十分抱歉,我指的不是这艘船,而是所有的船,无论它是风帆战舰或者快速帆船,都是腐朽的。”
老船长这个时候才回过神来,一股欣喜冲上他的脑门。
“是的!是的!”老船长咽了口唾沫,两颗金牙在月光下闪个不停,“无论是什么船都是羊毛做成的帆,木头做成的身子和粗毛做成的绳子!”他的大手放开被折磨许久的衣角,大力的拍了拍船舷,他跟他的老伙计终于不用分离了。
“那么,您想要一块怎样的土地呢?”崴列特开口,转过头,定定的看着这个激动地邋遢船长,“是一块适合种土豆的?还是适合种小麦的?亦或者你想要养几头肥猪给你的船员们吃点好的?”
船长虽然眼睛已经不大好使了,但他耳朵却清楚得很。他明白,这是这位年轻的岛主要收买他了,内心闪过一丝被看透的耻辱,不过下一秒就消散了,他大声的回应崴列特:“您不用这么客气!只要我和我的老朋友在一起,就没有其他的要求,老子……我是说我,我只要能有一张席子睡个觉,头上有片芦苇挡着太阳,喝了能喝点伏特加就行了!”
“至于船上那帮小崽子们,也是喜欢喝酒胜过香肠。”
“如您这样的贵族肯定没喝过那种烈酒吧!嘿嘿。”
……
船长说道土豆酿的伏特加就打开了话匣子,从以前海军服役时候攻打海岛聚落,说到在爱尔兰海亲眼看到巨型海蛇缠绕在战舰上,不管其中到底有多少吹牛的成分,不管崴列特听出来了多少,她都没有去拆穿,只是静静得听着。
直到说的嗓子冒火,老船长才发现自己热情的过头了,讪讪的闭上了嘴。
崴列特也没有什么表示,问了句:“您的经历很丰富,但我还没知道您的名字呢。”
老船长有些得意地背靠在船舷上,说:“别说名字这种东西,我没爹没娘的,有记忆以来就在海上,跟着路易船长,然后他死了,船也被买走了,我拿着四五个先令从爱尔兰偷渡到苏格兰,又跟着商队走向了英格兰,然后在码头打拼十十多年买到了这个老伙计。”他有些出神的说着,白翳的双眼也回复了片刻的清明,“真是飞快的流逝啊。转眼我都五十多了。那时候这艘船还破破烂烂的,如果不是……”
眼看着这个老头又有滔滔不绝的架势,崴列特不得不再开口,提醒道:“名字!船长先生。”
“哦!不好意思小姐,船上的崽子们只懂得吃喝嫖赌,我平常也没什么机会和人诉说这些。”船长挠了挠油腻的头。“叫我马歇尔或者‘红鳗’吧,那些老东西们都这么喊我。”
“好的,马歇尔船长。”崴列特从船舷上起身,最后望了一眼繁华的英吉利海峡,走进了船长室,她蹲在母亲和两个妹妹身前,看着三人熟睡的面孔,突然又觉得未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嘛。
制药她们一家还在,只要还有机会,她一定会买回那个庄园,也一定会买回她祖先的荣耀。
大海寂静无声,潮汐来回翻涌,少女无声的誓言不知道被消失在哪个旋涡,这里埋藏了太多秘密,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
顺道的风鼓起满帆,长蛇号载着一家四口向着北边航行,一路上两个小家伙都兴奋不已,她们遇见了上海面换气的座头鲸,洄游的虹鳟鱼群,偶尔能看到大批的渔船从荷兰那边驶来的捕捞船,拖着一张又一张的巨网奔向码头。
崴列特和玛格丽特的愁绪似乎也被这些奇景冲淡了,母女俩像往日一般给彼此梳头,甚至两人之间还能放松的调笑,玛格丽特抱怨着崴列特顺滑的金发变得粗糙无光,而崴列特则抱怨自己魅力的母亲变得像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她向着三个听众诉说着自己在布拉德利女子学院的见闻,说着那些伯爵小姐们华服锦缎,说着女教员的厚的像拉丁文字典的眼镜,也会评价一番学校里那几个餐厅的好与坏。
布拉德利女子学校绝对是个好学校,学校的老师们也绝对对得起他们每年五十磅的薪酬,但是它绝对不会教育一个淑女该如何去在一群男人之间求生,更惶提在海盗、原住民和税务官之间如何生存,在此之前崴列特甚至没有亲自锄过一块地。
但是还是那句话——只要一家人还在一起,就还有无穷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