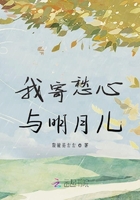哥哥走后,麻药也过了,手臂专心的疼,疼的我破口大骂爆粗口。
不过倒过的挺清闲的,现在我就是小祖宗呀,想吃啥,他们立刻去买,一直守着我。
第二天中午,伤口又疼又痒,我在病房里又哭又闹,这感觉太要命了。
不知道谁给金霏说了我住院的消息,金霏直接从剧组来了医院。
“宝宝,你看看我,我来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如果不是我问你哥哥,我还不知道你住院的事。”
我都已经快被疼痛给逼疯了:“啊!伤口又疼又痒,就像骨头里的痒,想挠挠不到,想哭哭不出来。”
金霏扶着我走到床边坐下:“这可怎么办呀,不然让护士给腻打一针镇痛剂?”
“去你的吧!我对镇痛剂过敏。”
半个小时后,我才安静下来,也可能是折腾的没力气了。
我半躺在病床上,面前是一个木板,上面放着很多我爱吃的菜。
我根本没有胃口,疼的我只想打人,金霏拿着勺子喂我:“宝宝你吃点吧,不吃身体不会好的。医生说了,吃完就可以出院了。来,我喂你,吃完后我就去办出院手续,咱们回北京去好不好?”
听到要出院的话,我才勉强张开嘴吃饭,他们坐在一旁的沙发上喘这粗气:“她可真是我们的姑奶奶,又哭又闹又爆粗口,隔壁房的病人家属都来投诉了。”
“哎哟别提了,这姑奶奶的手呀,没一年是好不了了,别忘了,她手臂里打了钢板。”
“自己养大的祖宗,那能怎么办?咱们九字科呀,难啊!”
出院后,我们开着车返回北京,金霏直接从剧组坐飞机过来的。
他开着我的车,我坐在副驾驶,后座空无一人,其他两个车跟在后面,多余的人坐飞机回北京了。
我躺在副驾驶座上,身上盖着毛毯熟睡,等我睡醒,已经到了北京,而天也暗下来了。
我向云华社请了一周的假,在家里养伤,总队长,师父,还有其他的师兄弟都买着礼物来家里看望我。
这下不用工作,我倒成了大祖宗,每天躺沙发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等真的要工作了,估计都不习惯了,金霏剧组也杀青了,电影很快就会上映。
这一天,金霏在厨房里做饭,我在客厅练习:“三呀么更二里,月影儿照花台,秋香姐定下了计,她说晚儿吧晌来哟。牡丹呀,亭前我们多恩爱呀,但愿得鸾凤早早配和谐。二呀么更二里呀,明月照花台。”
也是无聊透顶,在家里也只能唱唱太平歌词,背背贯口。
现在别说快板了,就连简单的乐器也不能碰了,倒也可以用右手打御子板。
一周的假期到了之后,我风风火火的回到剧场,再不工作,我就彻底疯了。
我手上依旧绑着纱布,吊在胸前,在后台,废了老大的劲才把大褂穿上。
所有人演出完之后,我跟着大部分一起返场,金霏搀扶着我慢慢走上舞台。
迎接我的,依旧是热烈的掌声,金霏帮我调整好话筒,我给观众鞠了一躬:“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我终于出关了,我想念舞台,想念你们。虽然暂时说不了相声,但是能穿上这大褂,也满足了。我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今儿上得台来,也是想给大家唱首歌。老汉,帮我弹吉他配个月吧,我给大家唱一首探清水河,这段时间在家无聊,倒也是把这首歌改编了,希望大家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