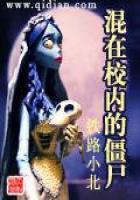氿郡-燕回
“将军!将军你慢些!”
昨日一场大雪,晨起燕回城已是白茫茫一片,如玉砌冰封,琉璃剔透。
不过此时的氿郡破雪卫主将左怀清早没了什么欣赏雪景的心情,只是心中焦急,脚下步伐愈发快了。
昨日那位泝殿下进城时已是傍晚,主上在无极殿上亲自迎了,后又在尺素阁里设宴款待,气氛融融,宾主尽欢,左怀清也就多饮了几杯,后来饮得多了,唐纪那小子又是个混不吝的,惯会挑事劝酒,左怀清一高兴就醉倒了,昨夜直接睡在了尺素阁中。
按说主上设宴,他们哥儿几个多饮几杯是常有的事情,尺素阁里本就常设了供他们歇息的间子,然而昨夜确是忘了形,竟是没有派人回去与夫人说一声,这还了得,左怀清脸上又青了青,胡乱与身后喊他的内侍摆了摆手,脚下不敢怠慢了分毫。
“将军,将军!”身后的内侍又唤道,这内侍年纪不小了,眉毛头发都白了,却是没有胡须,说话声音较寻常男子细弱,乃是一位宦臣。
“常公公,左某家里确有急事,回头再与您唠叨,公公您多担待些。”左怀清心里急,嘴上却仍是十分有礼,对着宫里这位老公公,语气颇恳切。
“将军呐,”常春紧着赶了两步,总算追上了左怀清,一把将他拖住,气喘吁吁道,“左将军呐,老奴是要说,昨夜主上早派人与府上说过您不回了,将军莫急。”
左怀清回过头:“那您不早些说。”
“老奴从尺素阁一路追您追到扫雪门,将军也不给老奴说话的机会呀。”常春委屈巴巴的抄起手道。
左怀清有些不好意思的撇撇嘴,方方正正一张脸上不自觉红了红,小声道:“确是家中有急事,家中有急事。”
“如今不急了吧。”老宦官常春眼中有些促狭的意味,随即又道:“主上交代老奴,等将军离宫时与将军言明,破雪卫即将南下,却不是去什么太平地方,家小留在燕回反而安全,若府上有吵嚷,主上可代将军解释一二。”
左怀清心中感激,向无极殿的方向拜了一拜。
“另外主上还有一言,命我务必捎与将军,”常春正色,左怀清一愣,回神却是整整齐齐的跪了下来。
常春挺直了一直弯着的脊背,才道:“孤继氿郡王位一十二年,幸有将军安我氿郡邦界,孤感念,将军过往,可既往不咎,但今日之后,将军府所作所为,务必三思而后动,言于此,将军切切记之。”
说完这句话,常春又是弯腰对左怀清拱拱手,没再说什么,便转身离去了。
半晌后左怀清才从雪地中站起身来,脸上神色复杂。他遥遥望去,老宦官的身影早消失在茫茫深宫之中,燕回不名宫,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像是一座冰雪国度里的巨大牢笼。
雪地中冰冷,然而此时,左怀清的内衫却已是冷汗淋漓,早湿透了。
忽然他又似是想起了什么,转身赶紧向将军府方向疾步而去。
-------
氿郡-凭栏雪坞
“既然他知晓凭栏雪坞,那你的身份,他也应一早知道了,”李千袭叹道,“原是我小看了这位氿郡王。”
李千袭面前坐着个人,身上裹的严严实实,看不清面目。
听闻李千袭说话也没动,只是将头上黑色的风帽又紧了紧。
“虽说如今结盟无虞,但有白夜舟在,今后氿郡进退仍不好说,你且回太安城去吧。”李千袭道。
“我不回太安城了。”风帽中的人说,声音不高不低,竟是雌雄莫辨。
李千袭尚未说话,一旁墨白却是眼神一瞬凌厉,右手已扣在了语冰刀柄上。
“怎么,要动手?”风帽里的人低低笑了两声,“你尚嫩些。”说话间那人冲着墨白扣刀的手勾了勾手指,墨白右手一颤,腕处就已是血花迸出,墨白一惊,就要后退。
红绡却不知是从房间的哪个角落忽然出现,一把扶住墨白后退的肩膀,同时青丝出鞘,剑身柔柔在空中一搅,便似是绊住了什么东西,又被她使力一挑,只见青丝刃上碧色闪动,几能见几丝透明的丝线缠绕,竟是紧紧勒在剑刃上,丝毫没有崩断的迹象。
红绡掐住墨白流血不止的手腕,扭头秀眉一竖:“丝线,你疯了?”
“我不回太安城了。”那人又说了一遍,已是站起身,五指一收,青丝刃上的丝线悄然不见踪影。
“够了。”李千袭低低道,墨白和红绡立刻跪了下来,风帽遮面的丝线迟疑了半晌,也终是跪下了。
“歃血堂向来没有什么不能退的规矩,”李千袭平静道,“你想走,不拦着,但丝线今日起就算死了,若江湖上再有你的手笔,歃血堂便不能容你。”李千袭坐了下来,看着跪在面前的丝线,“所托之人是不是真的可以相托,值得与否,你自己权衡,决定了,把玄冥留下,你自去吧。”
戴着风帽的人缓缓起身,一一取下五指根上细到几不可见的指环,依次整齐的放在李千袭面前桌上。
摆好后丝线又跪了下来:“堂主大恩,丝线不敢忘,但那人之于丝线,是敢信终身之人,多谢堂主成全。”说罢端端正正磕了三个头。
红绡嗤笑一声:“他若知你始终,还能与你终身相托?真是贻笑天下了。”
话音未落,忽见墨白腰间语冰出鞘,墨白右手受伤,竟是眼看着被丝线夺了刀去。
正是惊讶间,只见丝线手起刀落,硬生生削去了自己的右手小指,接着语冰堪堪归鞘,一截血淋淋的小指落在地上。
“玄冥归还,丝线已毁,今日起世上再没有杀人的傀儡师。”丝线喘息着说。
红绡震惊中竟难以回神,喃喃说了句“何至于此”。
墨白只是握着受伤的手腕,定定看向李千袭,自始至终,李千袭面上皆是毫无波澜。
-------
青郡-梅涧
什长代邕张满了弓,正指着大金城关下信步走来的一人,毕竟也是有年纪的人了,持弓久了,手臂就有些抖。
“来者何人!”他冲城下喝道,张弓的手缓了缓,又拉满了。
那人着一身黑衣,一路从鹄部大营里走过来,脚步坚稳,似乎关前尘土都为他让了条路出来。
“再往前一步,北府弓射无眼!”代邕又喝了一声,见那人脚下不停,牙缝里“嘿”了一声,便是一箭离弦。
手下几人皆是纷纷射出,十支北府过甲箭入土扬尘,在关下黑衣人面前整整齐齐排成一排,使得他终于停下了脚步。
代邕向身旁的人嘱咐道:“速报与霍帅,此人也不知什么来头。”
手下领命去了,代邕又是向城下喝了一声:“来者何人。”
那人不答,却是在从身后掏出个什么东西,送与嘴边吹奏起来。
羌笛,徵调《夜沉吟》,一曲罢了,黑衣人仰头望向大金城关城上。
城上赶来的霍诚微微皱眉,继而又是眉头一展,冲城下之人抱拳,朗声道:
“北府霍诚,见过柳先生。”
黑衣人扯去覆面黑巾,一张苍老的脸显现在风沙中。
老人身材微胖,长得慈眉善目,面色红润,看起来活像一尊弥勒,唯一的区别可能就是这老人有一头花白头发,整整齐齐束在头上,未簪未冠。
老人将手中羌笛默默收好,对城上霍诚拱手道:“柳潜冒昧,请霍帅一叙。”
天门教柳潜,祉座大教长。
相对于谕座的彬彬有礼、玄之又玄,天门教祉座向来是一根棍子扫天下,不守规矩我揍到你守规矩就是了,如今这位祉座大教长柳潜在年轻时,即使是在西北那种民风彪悍之地,也是凶名远扬,罕有敌手,乃是名副其实的狠角色,长成这副模样实在令霍诚意想不到。
而祉座大教长手下铁律僧兵,数量虽说一直不多,但早在太祖灭燊朝时,就很能令起义军头疼。
燊朝末年太祖楚春深对天门教赶紧杀绝,最后一役中,八千铁律僧兵在祉座大教长被擒的情况下,仍是攻守有度、不慌不张,虽说终是难逃覆灭,但起义军也没讨到什么好处,当时主帅为慕容青渊的北府军,在那一役中烈焰卫两营尽灭,盾山卫折损过半,传说中的北府奔雷卫,也是从那一战之后,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一战后,天门教余众只得避往西北守阳关外,他们并没有自此一蹶不振,反而于广袤的戈壁黄沙中蛰伏,往来于鹄各部之间继续传教,西北鹄八部的开化,大多与天门教的传播有关。
自教义遗失后,天门教谕座和祉座常年不和,在对待新建立的统治阶级方面的意见,更是针锋相对:谕座认为应该亲附、利用新建立的统治阶级,以重新找回教义为第一要务,毕竟楚春深一人国仇家恨,并不代表其后代子孙代代国仇家恨,仇恨就算不能被忘却,也总归会淡化,谕座主张逐步向宣朝内部渗透,借由新的统治阶级,恢复天门教往日荣光。
孙显林几乎要成功了,美梦一直做到公主楚泝出生那一夜...
而祉座则秉持一贯的铁血作风,认为你毁我教根本,夺我教圣物,欺负人欺负到了姥姥家,我吃饱了撑的还要在你手下讨生活?他们深恨打破世间规则与秩序的楚家,意图扶植新的政权,最终向楚家讨回公道,报仇雪恨。在这两百年中,随着传教范围逐渐扩张和信教者的不断加入,天门教铁律僧兵逐渐恢复建制,如今五千兵信仰坚定,武艺精熟,在付影章找到大教长柳潜谈国教东归时一拍即合,归于鹄部,成为八部南下中的一支精锐步军力量。
凶名赫赫的祉座大教长柳潜,如今笑眯眯的看着霍诚开了大金城关城门,拎着个酒坛子,独自缓缓向他行来。
“不怕我使诈?”柳潜眯着眼睛问。
“柳先生说笑了,对我一个小辈,用不着。”霍诚道。
“我十分喜欢你那一手弦子,因此才前来与你说一声,”柳潜道,“明日我要拿下梅涧了。”老人语气平静,脸上仍是和和气气的。
“柳先生拿便是,给不给,就是霍诚的事情了。”霍诚仍是恭敬道。
老人哈哈一笑:“性子我也喜欢,那明日,老夫就不与你客气了。”
“有今日一叙,柳先生已是对霍诚客气了。”霍诚又道,“拨子霍诚就收下了,却没什么能回赠老先生的,这坛青梅,乃是霍诚自酿,埋了这许多年,好喝不好喝的也就这一坛。虽说天将入冬,时节不衬青梅,但既然撞上了,今日便与先生在此处饮了。它世上走一遭,也算有所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