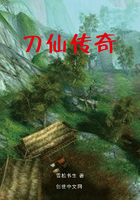陈殉目光呆呆的,看着眼前那个和年龄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孩子,心中却是思索着身边之人为何救自己,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年岁不大,但生在氏族府邸,思维自然要比同年人复杂的多,仿佛天生就是冷静沉着的性子。
与外表所展露不同的是,他此刻的心脏还在砰砰直跳,冰凉的小手上,仿佛还依存着母亲血液的温润,那种感觉很不好,很难受。
他很想大哭一场,喉咙仿佛被什么塞住了一般,很苦也很涩!
远处蹒跚的陈非也同样如此,他担心父亲,但是距离那柄铁剑越近,那种可怕到令人窒息的压迫感也越发浓郁,以至于仿若乐曲律动的呼吸节奏,也随之乱了起来。
“爹你千万不能有事啊。”
他在心中呐喊着,紧张着,同时也惧怕着。
陈荀身边的柳抑道,此时也笔直的站立着,他身姿是那样的挺拔,以至于让人觉得此时的他,就是一柄直来直去的利剑,或者说他无时无刻不是一柄矗立于世间的利剑。
他看着远处的陈非,微微点头,目光中带着些许的赞赏与期待。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你错了!”
这句话是他对着身边的陈殉所说。
“你对我并没有什么用处,我救你只不过是出于好奇和欣赏,我好奇像你这样天生冷血的人,连自己母亲都下得去手的人,是否有活下去的勇气。”
他没有说欣赏陈殉什么,他也不必说,因为他还不配知道。
本来生性有些多疑的陈殉,听到柳抑道的言语,似乎释然了许多,目光中也流露出一些悲伤的情绪。
不知何时起,原本迅猛疯狂的火焰,也渐熄渐止,遗留下的,只有满地的黑色灰尘,那早已燃烧殆尽的草屋,脆弱的如同风中的残屑,伴随着夜晚的凉风飘然逝去。
陈非距离那剑越发近了,乃至于此刻他眼中映如出的是,父亲那被一穿而过的胸部,以及生死不知的状态,他有些痴了,身上被剑气所切割出的一道道血痕已然显得那么的无关痛痒,只因心中的疼与痛越发强烈,强烈到他细嫩的脚踝处正在往外流着涓涓血水,他也感觉不到了。
陈非一张小脸上首次出现了一种极为狰狞的表情,转过头去,死死的盯着柳抑道,一言不发,似是要将此人的面目牢牢记住,恨之入骨。
柳抑道似乎并不在意,缓缓的说道:“那小子还死不了,李某那一剑避开了他的心脏经络,不过若是剑气继续在他体内横行,怕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是回天乏术,哼,在下稍微离开一刻,便生出这样的变故,不杀他,已然是李某手下留情。”
说罢,他的目光从陈非那曾经被陈天常用钝器所伤的小脑袋上收了回来。
“哼,今天的老鼠有些多,来来去去甚是烦人,难道李某不杀上几个,便源源不绝了?”
这一刻他迎风而立,儒袖飞舞,手中并没有剑,但又有谁敢说他手中的不是剑?
只因他在这里,
剑....
便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