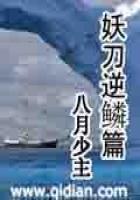我能看到唐僧玄奘在宽敞的凉殿中翻译《心经》。他
悚惊于自己的国师地位。身边的长案、鲜果、名贵的
印度檀香,与空气中弥散的诗酒风骚相掺和
他的光头静静泛着天光。头发在仪规中属于污秽之物
必须持久性剃去。如同五蕴,如同挂碍
我也看到在不远处研墨铺纸的我。和所有唐朝的
抄经生一样,宽袍轻履。喝着陆羽亲煮的新茶
世界只剩下佛陀的声音和练气的坐姿
还有座旁的一瓶东洋插花,熬着药石的瓦罐
语言和绘世的危机像一名名肥硕的妓女紧靠在门扉
我们大声诵唱着。玄奘是个老和尚了,老就意味着比较
接近神。他偶尔触触众人的额头,自语道:照见,
照见。而咒语爆响,宛如雷鸣:快去啊,快向彼岸
渡去。我记得我跳上船,操起一根新削的木桨
渡口精瘦的船夫冲出来朝我大吼:放下!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