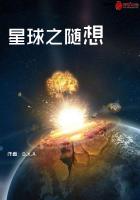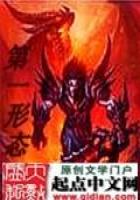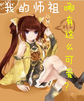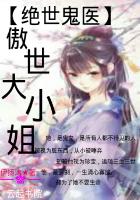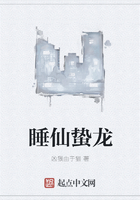老太太摇摇头:“岂止不受待见,简直就是人人眼中的羔羊。上下都恨不得挖下他一块肉吃。
早就听闻三房上下短视,只知地里刨食,今日看,此话都算夸是他们了。
恐怕除了那个老糊涂的三老实,还有几分真心实意的疼爱。
其他地人全是些虚情假意的东西。如此恶劣的境遇,我以前只当是书上讲的故事,没想到竟然在身边就有。”
四房嫡子不解道:“难道您也是嫌弃他的出身,害怕那歌姬之子不上大雅之堂?可是考取了解元,朝廷自会给他生母一个交代啊。
还是您嫌弃三房太乱,怕表孙女嫁过来受苦?可考中了解元,要是日子过的不舒坦,自己另立一房也是可以的呀。”
老太太用拐杖轻轻敲了儿子的脑袋,“憨货,为娘就是太惯你了。倒不如那些个贫贱的寒士了,你就这般看不起你的老娘。
为娘岂会不知,朝廷会给他生母一个身份。
我又岂会在乎三房那些蠢物。哪怕整个茂陵吴氏中,我又在乎过谁人脸色。
我兄弟家将门虎女,难道还治不好个家么?你就那么轻看你外甥女。
憨货呀,憨货。”老太太点了点儿子的额头。
嫡子赶紧赔罪:“母亲请消消气,还请母亲解答孩儿心中疑惑。”
老太太踱步前行,走回屋内,在躺椅上坐了下去。说道:“我且问你,你舅家与查氏孰强孰弱?”
“自然是舅舅家强,毕竟开国元勋、将门之后。不过...”嫡子想了一会,“查氏如今在朝中也颇有几分势力,应该只能算是稍有逊色。不,大致在伯仲之间吧。”
老太太赞许地看了看儿子,又问:“我吴氏心腹大患是谁?眼前之患又是何?”
嫡子思考了一会答道:“心腹之患必是查氏。
眼前之患么?应该是家族人才青黄不接,官场无可用之人。
子瑜虽然新中解元,而且看南京传过来的风评,进士应该也是在望无疑。
但是想成栋梁之材,恐怕还要十数年。在这十数年里,恐怕家族会颇多磨难。”
老太太点头道:“确实如此,所以天降了一个如此聪慧的解元,实在是吴氏祖先庇护啊。”
老太太看了看,儿子求知若渴的眼神。让她满意地点点头,道:“解元想要与查氏联姻,这实在是一步好妙手,真正的胜负招啊。
与查氏联姻可解眼前之患,更可以解吴氏心头之患。
你想,这几日查氏恐怕也颇为坐立不安。一个解元,就是代表着一个稳拿的进士。
而应天府这天下最贵重的解元,自然是个铁打的进士,说不得就是个一甲或二甲。只要成了庶吉士,入了翰林院。那时只要正常升迁,自然都有入阁为相的可能。
要如何应对这番未来劲敌。恐怕查氏那几位老货,都是伤透了脑子。
所以现在的局势是,查氏当下势强,但未来必是吴氏兴隆。故而现在就是我吴氏最危险的时候,如何应对查氏更加猛烈的打击。在这样的打击中平安的活下去,才是吴氏当下第一要务。
这点上大房那个大老爷与我都很清楚,二房应该也有所察觉。
恐怕只有三房老爷,才是那个蒙在鼓里的人。三房那些蠢东西,竟然还以为解元的婚姻是件私物,还你争我夺真是何等的愚蠢可笑。
现今,解元的婚姻就是我们吴氏最好的筹码。是生是死,全靠压得对宝。
所以,我才想联姻你舅舅家与解元,以求得一外援,保护解元与吴氏平安度过这十几年。
大房老爷应该也有所思量,但是他那房门槛太低,怕也没有太合适的家族可以备选。
却没想小小五郎,心智高绝。竟然自己想到破局之法。”
老太太激动的有些气喘,嫡子赶紧给他顺顺气。老太太缓了一会,继续说:“娶查氏小姐楼藏娇之女,是步好棋。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窈窕淑女,人恒爱之。娶她为妇,最差也只会稍稍损失点风评,却不会降家族名声。
而且,这样对于查氏来说也是上选。未来的隐患没有了,打击隐患的后手不用出了。现在也可以压住我们一线,朝堂上更是可能会得到一个强力臂助。就算是五郎万一没中庶吉士,他们不过失去一个小枝庶女,回过头来继续收拾我们也不晚。
查氏那几个老家伙,甚至还会收她为义女。这样就连名分也不会差了。
这样原来道路上的敌人,反而变成了前行的拐杖。
果然是好计算,好策略啊。
此计若成,吴氏与查氏今后互相扶持,为家族未来铺平了道路。从此而后,吴查两氏都没有了心腹之患,更是可以全力发展,以求更进一步。
就算看透了这样的阳谋,谁又能不跳进去呢?真是个绝顶的聪明人啊。
有得此子,真乃是吴氏之福也。”
嫡子挠挠头:“母亲睿智。但是这样虽然百利吴氏,却不是要亏待舅舅家么?母亲怎么这回不管娘家人了?”
四房老太太翻了一眼嫡子:“去问问你媳妇,她比你清楚。”
见母亲不悦,嫡子只好告退。回到房中,询问正妻。
正妻笑道:“夫君有所不知,但凡钟鼎世家,教女都是嫁夫从夫。
我等自幼便知,栾祁害夫灭子与雍姬买夫救父的故事,您让老夫人为娘家而放弃夫家利益,岂不是骂她人尽可夫么?
何况如果嫁出的女子,伤害夫家利益维护父族,又有谁敢与此家联姻呢?栾祁的娘家范氏、与雍姬的父亲祭仲,不都是没有外援而一世速亡了么?
所以但凡百年家族,所虑必是深远。又岂会,因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而且伤害自己的名声呢?故而嫁女儿如联合友邦,深怕伤了两国情谊。
岂可如市井小民一般,只考虑一时一世得失,而不管身后事情呢?恨不得女儿掏空夫家,以肥自己。这不是嫁女,而是树敌。
而升斗小民者,犹如蚍蜉。只管一时生死,确实看不见两日之事。但虫可无冷暖之所感,人岂可无寒暑之见识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