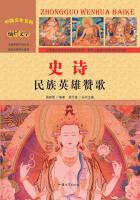坐上“宫廷前座”
丹麦政治高速发展的时期存在着优劣之分。如今,人们不受约束地高谈阔论,这与过去的交流方式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遇到一些时兴的话题事件。过去更多地是把一些鸡毛蒜皮、不足为道的小事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看待,似乎在培养自身的哲学大家风范。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既不认为我有参与这件事的必要性,或者可以说觉得自己也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存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如果把自己和政治扯上了关系,那将是一个灾难,这一点我坚信。利用政治手腕和智能将诗人们卷进政治泥潭并且让他们不可自拔。淡如炊烟可以用来形容诗人们的创作作品,当人们阅读后未曾在阅读者的脑海里留下不可抹去的印象。即使在品读当下得到了高度赞赏的评价,但最终也飘散逝去,犹如炊烟一般。控制欲望充斥着所有人的大脑。或许很多人不曾记得,理论和实际往往存着巨大的差距,主观美好的意念在现实中也许就是无法切实可行的。可曾记得站在山脚下抬头所看到的风景与站在山顶一览的开阔风景是存在着差异的。具有自己的信仰并且坚持到底的人都应该得到尊敬,不管他是以何种身份出现。只要心存美好,都是最难能可贵的。对于政治前程,我并没有多少追求,也并没有想过从这方面实现任何价值。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赋予我的神圣使命感在我灵魂深处不曾改变过。
在我所接触的丹麦上层社会人群中,我极其幸运地遇到了很多真诚、善良的人,他们关注我良好的个人素质,给我融入他们社交圈的机会,在休闲别墅中体验到他们的乐趣和绚丽多姿的生活内容,在宁静的山林间放松身心,得到真正意义上的灵魂释放。在这里让我体验到了回归自然的感觉。我的很多作品,包括《两个男爵夫人》这部小说都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成型。小动物们环绕四周,活泼可爱,足长且红的鹳鸟闲庭迈步。不闻政治、不近论争,黑格尔哲学更是不知为何物。身处自然之中,心中容纳不下除了自然之外的其他。自然成为我的宣讲者,身心都体验到了神的感召。
我与丹尼斯约尔德一家相识是源自于斯坦普男爵夫人的介绍,前者来自于吉塞尔菲尔德,后者来自于尼索。圣诞节是在丹尼斯约尔德的古老别墅中度过的,别墅古老经典,日耳曼风格充斥着整栋别墅内外。年华逝去的丹尼斯约尔德公爵夫人魅力依然不减,是女性中的杰出者。我所受到的礼待如同高贵身份的宾客一般。她的墓地选择在了一片高达的山毛榉树下,这片树林是她最为热爱的地方。在威尔海姆·莫托克的盛情相邀之下,我离开吉塞尔菲尔德,来到了这位财政大臣的庄园,位于布瑞根特福德的庄园是那样的令人向往。在得知他心爱的妻子已逝,我默默虔诚祈祷。我的生活洒满阳光离不开与他们共处的那些美好家庭生活。
有托瓦尔森的相伴,我在尼索度过了几段美好的时光。花园里的工作室是他们为了托娃尔森专门修建的。不管他是一个平凡的人,还是一个艺术家,我都是在这些时光中真正走近他。我将细说我在尼索所度过的这些日子,那是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
在不同的生活圈中穿梭,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也逐渐地习惯这样的生活,不管是在皇帝权贵身上,还是在平民百姓身上,紧密地联系着人类的各类高贵品性。人们的优良品性都是共同存在的。
我更多的时间是与哥本哈根的约纳斯·科林一家相处度过,在他的家中,他的儿女都已成家,并且孩子们也在成长中,与哈特曼的友情日益深厚。他具备作曲家的天赋,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令人向往,温馨幸福,这些都要归功于他能干可人的妻子。同样,她热情似火,善良纯洁,招人喜爱的她也有着出众的才华。日常生活我离不开科林,奥斯特德则是我的每部作品最好的良师,他总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正因为这样,我们越走越近,了解也不断深入,感情稳固可靠。他对我的重要性甚至影响到了我的性格,我会在后面道来。
每天晚上我都会去俱乐部,这是固定的节目。同年,我获准能坐到有铁杆和正厅前座分隔的“宫廷前座”。要知道,“宫廷前座”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为剧院贡献一部戏的作者是被安排就坐在楼下的正厅位置,如果坐在前座那么就代表是拥有两部作品的作者,“宫廷前座”也就意味着是提供了三部的作者。要知道,这表示三个晚上都演出,都围绕这些短剧或者是能撑满一晚全场的三部戏。
一般情况下,只有朝中要臣、外交使节、高级政府要员才享有“宫廷前座”的资格。就算是能坐在这个区域中的一位既是演员也是作者的诗人同样也被人告知在这片区域中出现的大多是贵族,需要保持低调谦虚。如今,我和托瓦尔森、欧伦施莱格、卫斯等人也得到坐在这里的资格,这是一份荣耀。为了方便与我交流,托瓦尔森经常与我邻座,在戏剧上演的同时,我能为他解析剧中所呈现的各类情节。除了已经去世的他以外,还有欧伦施莱格也经常挨着我坐。每当我和这些名人们同坐一排时,我的内心就会被谦卑感充满,但我是虔诚的。这样的夜晚有很多,别人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欧伦施莱格
人群中的欧伦施莱格表现得特别放不开,默默地站在一边。他那善良纯洁的性情只有脱离了人群之后才能表露出来,这是他特有的性情,让人很愿意和他亲近。他的重要性在斯堪的纳维亚可以称得上是无人不晓,他的创作天分与生俱来。在他的晚年时期,比年轻人都要高产很多,体现了他常青树的品质。我将自己创作的第一首抒情诗诵读于他听过之后,他对我的作品表示有极大的兴趣,虽然他并没有作出一些明显的表示,但是只要我受到了大众与所谓评论界的抨击时,他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成为我的辩护者。一次,我受到了一顿狂轰滥炸的攻击后,情绪非常糟糕。他走向我,并给予了我温暖的怀抱,安慰着我说不用理会那些人的论调,真正的诗人正是如我一般。他向我诉说起了他心目中的诗和诗人,还说到了在丹麦诗人需要面临着的各种评判。他温和的语言安抚着我的内心,告诉我他是高度认可我这样一名讲述的诗人。我明白,有些人在我的作品中发现了严重的拼写错误时,毫不留情地表现出了对我的轻视。但欧伦施莱格却会表达他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些错误正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小纰漏,不影响大局,又何必苦纠于此。他认为改动的必要性都不大。关于他的个性,他与我之间是如何建立日益深厚的友谊我会在后续的篇幅中再陆续进行一些介绍。
在《丹麦的诸神》一书中,欧伦施莱格与我共有的一个特点有被传记的作者提到。导言中是这样阐述的:“成为诗人或者艺术家的人如果仅是以自身冲动作为出发点,并由此所产生的强大力量的情况,现下趋于罕见。诗人与艺术家早就离不开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与个人经历,并不是仅以本能影响所唤起的信念。思维的撞击发散、各类环境的存在以及个人经历都成就了这个时代的我们。可以说除了安徒生与欧伦施莱格之外,在其他的文坛作家身上是不存在这样的现象。正是这样的情况,才更能够解释在国外前者能得到赞誉,后者在丹麦却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国外与丹麦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我们仍然是拘于过去老旧学士的守旧学院派。国外已经厌倦了学院派的墨守成规,已经趋于一种古老文明的方向发展。”
托瓦尔森
还记得我有提到过1833年、1834年在罗马第一次见到托瓦尔森,1838年的秋天,在丹麦上上下下所有人的渴望之下,他来到了丹麦。他所在的船还没完全靠岸时,圣尼古拉塔就已经有一面旗帜在风中飘扬迎接着他。那一天成为了国家的节日,在特瑞克若纳和朗格里尼之间的水面上,装饰着三角旗和鲜花的众多小船都在游走。具有自己标志的旗帜可以看出是哪些画家和雕塑家制作的。那些画着希腊女神雅典娜的旗帜一定是学生的。还有个诗人在旗子上画上了神马珀伽索斯的金像。现在还能在托瓦尔森的博物馆里看到这个富有暗示性的雕带装饰。欧伦施莱格、黑伯格、赫兹和格兰德维格都能一一从画中诗人的船上认出。站在横贯船体座板上的我左手抓着桅杆,右手不停地挥舞着帽子。
迎接托瓦尔森的那天因为布满大雾,直到船离城很近了,人们才看到它。马上有人鸣枪作为信号,立刻就出现了大量人群涌向海关大楼去迎接他。和欧伦施莱格同行的还有黑伯格,他是当时的领袖人物,这些诗人都是由他决定邀请谁或者不邀请谁。拉森广场庞宾就停着他们的船。诗人们等待着欧伦施莱格和黑伯格的到来,逐渐听到了船抛锚时才会鸣放的加农炮炮声。我估计在我们来之前,托瓦尔森就已经不在船上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歌声伴随着微风阵阵飘来。我十分想参加,尝试动员其他人把船划过去,但是得到的反应是:“我没听错吧。我们都还在等欧伦施莱格和黑伯格呢!”这时又有人说:“他们要是还不来,仪式就要结束了。”一名诗人指着那面有珀伽索斯像的旗子说道:“他们要是不来,我是绝对不会在这面旗子下航行的。”我一边摘下旗子一边说:“摘下旗子放在船上不就解决了嘛。”黑伯格和欧伦施莱格同我们会合后,换至我们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