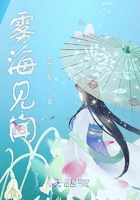才华的挫折——即兴诗人
现在很多曾经我的反对者现在已然不再保持那时候的观点,甚至诗人霍奇也变成了我的朋友之一。他常年旅居海外,现在才刚从意大利回来。现在的哥本哈根人在精神生活和艺术品位上受到黑伯格的轻歌舞剧的影响颇深。黑伯格曾表示,即使我创作出不错的抒情诗也将不可能获得别人的关注,我不过是一个被娇惯过头的幸运儿。现在,他在读过《即兴诗人》后才出乎意料地意识到我的诗歌天赋,还有思想深度。为此,他还写信给我表达了先前对我不公正评价的歉意,并请求我的和解。自此,我们成了至交好友。他每每总是试图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帮助我实现最大利益,并为我的每一个进步关注最深切的热情和兴趣。然而,他的这种优秀品德很少被人所意识到,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也很少遇到知音。其后,他创作了一部名为《莱茵河畔的城堡》的小说,其中他塑造了一个真正漫画化的诗人形象——由于过于自负最后被关进了疯人院。显然,这种表达方式对于丹麦人而言是过分且不公正的,因为他试图将我所有的缺点剖析在阳光之下。其实,绝大部分丹麦人是这么想的,并且也将这种想法如实地表达出来。如此一来,导致霍奇不得不专门撰文评价了我作为诗人在艺术界的地位。他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舒沃主编的《评论周刊》上。
我曾被人告知,西伯恩曾猛烈批评过我的作品。并且,他并不欣赏我的诗人身份。他的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并和他一样,认为帕鲁丹·缪勒的《丘比特与普绪克》是一部杰作。因此,当我看到他在为英格曼辩护的一本小书中表示,希望某些人能在文字中善待我,对此我感激不尽。拜读《即兴诗人》后,他寄给我一封充满热情的信。这是唯一一篇除了卡尔·博格的那篇短评外,真正发自内心的赞许。文如其人,从文字中我仿佛能看到他的形象。西伯恩写道:致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
拜读《即兴诗人》后,深感喜爱,并为书本身而欣喜。当把它与你的早期诗作做了对照比较,能发现其中巨大的差别,就好像是躲在市场柱子后边嬉闹的小阿拉丁,变成了成熟、富有朝气的阿拉丁一样。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即兴诗人》。刚读完前面的24页,我深有感触:“太精彩了!”以至于到了次日,我根本无法看进去任何一本其他的书。你要知道,这本书所给我带来的满足感是如此地强烈。
对书及其作者,我心中满怀真切的欣慰。我明白,你在德国人眼里是一个“善良的人”。如今我还从你身上看到了一颗一丝不苟的心。在和别人的交往中,你表现出柔和开朗、坦诚、乐观、敏感的一面。而在国内的诗人里,你却又是深沉、激情、热烈的,想象力也非常丰富。从你身上,我看到了你性格的两面性。因此,切勿用整个的心灵和批判的态度来思考,也可以不用看任何一篇批评你的文章。缪斯女神就在你身边,无论如何,都要精心呵护,不要让她逃离你身边。
你曾在意大利生活过,你在那里的目的并非要将它变成画境,而是为了生活本身。你的描述是发自内心的描述,这幅意大利画卷也因此变得更加美好。
或许,哪一天即将,或者已经到来,在另一片广袤的土壤上——历史的王国,你将冒险前行。我期待在那里将能看到你优秀的著作。
另外,你也会在哲学的王国里自由翱翔。我希望你将向我们展现你与缪斯同在,把你的哲学思想带给所有人。
以上所言,发自肺腑,我真切地希望你能更好。如果这封信光临的那一刻,你心中闪现出缪斯女神的影子,就不要让这封信影响你们,你只管静静地把它放在一边。如果不是这样,我倒希望缪斯女神早日降临你的心灵和你的房间。如果有什么东西要来打扰或分散你的精力,就直接说:“别缠着我,走吧!”
最后,请接受你诚挚的朋友的真诚祝福。
西伯恩
话题回到《即兴诗人》一书。这本书拯救了我沉沦的命运,我身边再次聚齐了很多朋友们,并且朋友的数量得到增长。这种结果告诉我,我首次赢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肯定。
克鲁斯教授随后着手用德文翻译这本《即兴诗人》,并为之设计了一个较长的题目《一个意大利诗人的青春与梦想》。虽然我并不赞同他使用这个标题,但他却坚持认为这样可以吸引读者注意。事实上,结果却证明他是错误的。或许,一个简单明了的标题《即兴诗人》更能将之引入成功。众所周知的是,卡尔·博格对此书发表过评论,在该书每个细节都被探讨清楚前,并没有一篇真正意义上的评论。结果是,在《文学时报》上出现了一篇语言更为客气一些的评论,虽然对这本书的好处并无只言片语。对他们而言,“这本书毫无长处可言”。他们眼中只有这本书的纰漏,甚至将我在书中的一些意大利语拼写和表达错误罗列出来。彼时,尼科莱还出版他那本著名的《意大利的真正美丽在哪儿》。在他心目中,意大利的自然风光远不及德国,卡普里岛上只有海怪,除了美第奇的维纳斯,阿尔卑斯山只有一侧的美貌。当然,这不过是尼科莱自己的审美结果。正因如此,国内的丹麦同胞才开始看清楚我这本书的意义。而尼科莱向丹麦人展现了一副真正的意大利的模样。
好评如潮
我把这本书呈献给了当时还是克里斯蒂安王子的克里斯蒂安八世。在接待室,我碰到一位当时并不太出名的诗人,虽然现在的他在《国家年鉴》里已经声誉斐然。他以一副足够屈尊的态度对我说,我们都是作家,拥有相同的职业。然后,他就开始在这位后来的显要人物面前对大斗兽场“Collosseum”这个单词大加谈论。这些话是针对我而出的,我拼的“Coliseum”与拜伦的拼写并不相同,我的显然是错误的。他说,真可怕,书中净是这样草率马虎的拼写,会使得读者忽略作者本身的才华。当然,他的声音很大,传入了整个接待室所有在场者的耳朵里。我试图指正拜伦是错的,我的才是正确的拼写。可他却微笑着耸耸肩,把书递给我说道:“这样的印刷错误真是糟蹋了一本好书。”在场的人在自己的圈子里议论着:“哦,他就是这本书的主角。”“他们正以永恒的赞美使安徒生走向毁灭。”
作为一份最为文化精英所看重的刊物,《文学月评》是美的王国里的高等法院,其中甚至还包含了很多小文论以及古来陈旧的喜剧。可是,对于我的《即兴诗人》,就连一句像样的话也没在月刊上出现过。或许正是因为它再版印刷,已然引来了公众的关注。为此,我才重拾勇气开始着手写作一部新的小说《奥·特》。1837年,关于这两本小说的评论才首次出现在《文学月评》上,我又被恶意批评、教育了一番。后文详叙。
关于我作品的真正意义上的一篇评论——或许言过其实,是来自德国的,我就好像一个病者,贪婪地恋着那缕阳光,心中满怀着快乐和感激。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并不像《文学月评》暧昧地旁敲侧击,以及对《即兴诗人》的批评中近乎公开的声明那样,可我对于在书中那些曾给予过我帮助的人却不会持有感恩图报的心态。因为他们不过是把我当成一个乞求救济维生的穷小子安东尼奥,对于那些必须或者应当承受的压力怨声载道。
据我所知,《即兴诗人》还有一个瑞典文的译本,并且在所有的瑞典报纸我都收获了很多对于作品的好评和赞赏。英国基督教贵格会教徒玛丽·豪维特还将此文译成英文,并对书中的重要描写给予了恰当的重视和赞美。
对于我的作品,他们如此作出评价:“该书中的浪漫是诗歌里‘哈罗德少爷’的浪漫。”因此,十三年后当我首次访问英国伦敦,就听说《外国评论》对我的作品给予了十分客气的批评,这一切应当归功于那位聪明且挑剔的司各特的女婿洛克哈特。那时候我并不会英语,对于该篇评论知之甚少。虽然这篇评论性文章发表在伦敦发行量和影响力首屈一指的评论刊物上,并被寄往哥本哈根,但并没有引起任何一家报纸的重视。此前,凡是被英国评论界提到的丹麦的作品都会被所有媒体跟风评论。该篇评论如下:“《即兴诗人》原创是丹麦语,这种语言来自于《哈姆雷特》的独创。事实上,这个存在于莎士比亚头脑中辉煌梦境里的‘丹麦王子’,俨然成了我们头脑中的现实存在……我被朋友告知,《科丽娜》是《即兴诗人》的祖母。也许她真的是。无论如何,在相比较下可以想象得出一位古板的、夸夸其谈的祖母形象。在其烘托下,这位意大利孙子显得更加可爱。”
另外,《科丽娜》也有被丹麦《文学月评》以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口吻评论过:“作者可能就是因为要刻意模仿斯塔尔夫人的小说《科丽娜》,结果误入歧途。”
与丹麦评论界一句话把我打发相比,英国、德国评论界对《科丽娜》的评论却是大相径庭。
有几种英文译本在北美出现。即使到1844年才出现瑞典文译本,但随即俄文译本就出现在了圣彼得堡。紧跟着,波西米亚译本也相继问世。与此同时,这本书还受到了荷兰人的关注,并受到了一份发行量不低的期刊专门载文极力推荐。法文译本在1847年由勒布朗夫人翻译在法国出版,最终得到外界的赞誉,法国评论界还特别以“纯净”来形容该作品。在德国,也存在有七八种不同版本的翻译,其中不乏有的版本多次再版。言及于此,我必须要特别强调著名的希兹格版查密索的译本。在诗人给我的一封信里,他表达了对我作品的喜爱,他对《即兴诗人》的评价甚至超过了《巴黎圣母院》和《蝾螈》。
总的说来,在其后的数年间我收到了来自海外越来越多的赞誉。这让我保持了追随本心的勇气。因此,可以说即使我在丹麦成为一个诗人,可我所得到的赞誉却并不源自于此。所有的父母都愿意细心呵护他们的每一棵幼苗,愿意相信哪怕只有一株幼苗也可能是天才的起源,然而绝大部分丹麦人却反其道而行,竭尽全力去抑制他们的发展和成长。事实上,上帝为我之后的发展带来了来自异国的阳光,并允许我按照最初的愿望自由写作。与此同时,读者大众也组成了我比所有评论家和各个学派更强势的力量。因此,我凭借着《即兴诗人》在丹麦文坛赢得了立锥之地。我对于某些人来说,已经通过努力奋斗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却极其高兴,精神上仿佛增添了一双飞翔的翅膀。
在《即兴诗人》出版后的几个月,我出版了第一本童话集。事实上,那本书并没有立马得到认可。即使那些过去曾经真心祝福我的人也会为此表示遗憾。当然,如果相信它能马上获得好评就错了。这些人方才从我新出的《即兴诗人》中寻得一点希望,却发现我没能在“有价值”的路线上走下去,又开始写“孩子气”的作品。虽然《文学月评》对童话类文章并无意见,但另一份当时颇有影响的评论性刊物《丹诺拉》却载文请求我不要浪费时间写童话作品,并说,我的作品中缺乏童话写作必需的创作元素。如果要写,就要认真向他人请教。可他们显然知道我不可能这么做,最终的结果只会是放下童话写作。就是在这种喜忧参半的情况下,我的第二本小说《奥·特》出版了。慢慢地我能从内心情感中寻找到自己强烈的创作欲望,并自觉从这本小说里寻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叙述方式。于是,我分别于1835及其后2年里连续创作出版了三部小说《即兴诗人》、《奥·特》和《不过是个提琴手》。《奥·特》这部小说,尤其是奥斯特德将很多读者打动,并凭借着幽默获得了后者的欣赏。就这样,我被鼓励着写下去,并从这个圈子里获得了认可和欢乐。
我的朋友们
在收到西伯恩关于《即兴诗人》的信后,我特意登门拜访,并于他家中大声地朗读了《奥·特》。从挪威来访的西伯恩的保罗·穆勒当天晚上也正好在场。虽然他不欣赏我的《步行记》,却专注地听完了《奥·特》的朗读。他深深地被我笔下描绘的日德兰半岛、荒野和西海岸的场景所吸引,并对这本书表示了由衷的赞叹。随后,有人以几种德语译本为参照,翻译了瑞典语、荷兰语和英语的版本。《即兴诗人》曾因校样问题导致意大利单词的错拼或漏拼,触怒了我哥本哈根的同胞们。于是,有一位大学教授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主动请缨,为我出版的《奥·特》通读校样。他对此说道:“我习惯了看校样,并能做到精准细致,颇受大家赞誉。我这么做是为了避免你因作品中的小毛病受到他人的诟病。”在他逐页读完后,稿子又经过两个细心人的核对方才出版。一经出版,国内评论界还是得出了“安徒生在语法及拼写上从来都是粗心大意,这本书中依然故我”的结论。那位教授说:“他们太过分了。我就像对自己的书一样对你的书进行校样,他们显然对你真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