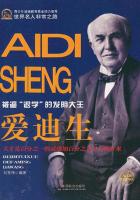来到意大利
十四年前穷小子来到了哥本哈根,十四年之后同样的时节,意大利将敞开双臂迎接我的到来,希望它能给我带来惊喜。我顺着罗纳河谷穿过寒冷的辛普朗山口,一片神奇的自然景色展现在面前。由拿破仑下令修建的岩石路上缓缓行驶着负重太多的马车,他的豪迈气魄随着岁月的流逝烟消云散。温度越来越低,头顶闪耀着光亮的冰川。披着牛皮的牧羊的少年紧紧裹住自己,缩在有火炉的小旅馆里借着火苗取暖。仿佛已经是冬天了,马车再走几小时,便会出现在都是栗树的林荫道上,有温暖的阳光照耀下来,这就是意大利的街景画面。昏暗的山间浮现出湖泊的轮廓,那是位于意大利北部的马焦雷湖,湖中的岛屿看起来就像开放在湖中的花束,娇小可人。天空倒是和丹麦一样,阴沉沉着,灰蒙一片。当夜晚来临,月亮从吹散的云层中探出明亮的脸庞,视野瞬间开阔,风光一片大好。路两边有大片的葡萄架,仿佛举行盛宴一般,一眼望不到尽头。比我想象中的漂亮多了。
米兰大教堂是我到意大利见到的第一座艺术建筑,此后我游览了更多的名迹,都远远不及它给我带来的震撼强烈。月光萦绕下,大理石材料的墙体让我拍案叫绝,不知动用了多少艺术家才完成那拱门、尖塔和雕塑。在这儿还能看到阿尔卑斯山被冰川和白雪覆盖着的山岭以及肥美的伦巴地区的绿色田园。歌剧和芭蕾舞剧正在拉斯卡拉剧院上演。在大教堂中聆听着宗教音乐,安静、虔诚地向真主祷告,这是一件多么圣洁而庄严的事情。
我遇到了两位同乡,我们一起离开了这座璀璨壮观的城镇。驾车前往热那亚经过平坦的朗巴德地区时,仿佛看到家乡的绿色岛屿,它们同样美丽、丰饶。让我感到新鲜的是这里的玉米地和翠绿的垂柳。不过比起阿尔卑斯山,现在要穿越的山脉太过渺小了。到达目的地热那亚之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国外的大海。
从阳台上的栏杆远眺蔚蓝的大海,无比亲切。丹麦人是非常热爱大海的。即便是第一次见到的陌生海洋,却让人感觉如故交一般。晚上我们去寻找热亚那的剧院,原本以为很容易,因为这里只有一条主街道,而剧院这么高大的公共建筑物,就在街边上。不承想街上矗立着无数宫殿,一个比一个雄伟,找到它可费了一番工夫。剧院前有一尊巨大的大理石雕像,主人公是阿波罗,这尊艺术品晶莹透白,好像密集的雪花耀眼地飘着。恰逢《爱神爱莉舍》这部多尼热地区的新歌剧在这里首次演出;接下来还有一部芭蕾舞喜剧上演。这部芭蕾喜剧非常有趣,长笛的伴奏响起,舞台上所有东西都渐渐开始起舞,结束的时候连最高委员会和挂在墙壁上的画也跟着舞动起来,很奇妙的构思。后来在童话喜剧《沙人》里我就借鉴了这个手法。
“阿森纳尔”号是一艘低舷大帆船,上面一共有六百多名囚犯,他们生活、工作都在船上。得到海军部的书面许可后,我们上了船。船上内部监狱的墙上挂着一排铁链,作用是在囚犯休息的时候把他们锁住;一溜木板床沿着墙边放着,这是宿舍。有几个带着锁链的囚犯待在病房里,其中三位蜡黄的脸色和凝滞的眼神让我记忆犹新,他们就快死了。有一个囚犯从床上半抬起身子,轻蔑地朝我笑着,向我投来恶狠狠的眼光,满眼的邪恶。他肯定以为我们是来看热闹的游客,来这里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看他们过得如何悲惨。一个苍老的瞎子也躺在里面,他已经无法承受身上锁链的重量。船的下方是工作坊,分不同的工种,囚犯每两个锁在一起进行工作。他们也许要在这里待上一辈子了。我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囚犯,他穿着同样款式的囚服,红衬衫和白裤子,质地却要精良得多。他是一个年轻人,没有被铐上。他要在这条船上服刑两年,原因是偷窃钱财,还有欺骗。他有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坦诚待告诉我们,他白天不需要干活,也不用被锁上,妻子定期会邮来生活费用。不过到了晚上,他同样要被锁在那张木板床上,犯人们总是喜欢嘲笑他,即便他吃穿不愁,却还是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受他们的讽刺和挖苦。
旅途中最美丽的景致出现在从热那亚顺湖往南行的第一天。山坡上的一片油橄榄林中热亚那耸立其中。花园里有甜和苦两种口味的柑橘树,结满了果实,闪亮的柠檬树青翠欲滴,这里就像一幅春光无限好的油画,叫人难以忘怀。此刻的北方可是一片冬天的景象,能够看到如此春光,怎不叫人激动呢?常春藤爬满古桥的桥身,一群头上戴着红色头饰的渔民在海边忙碌,许多座精致的别墅沿着海边建造,点缀着海岸线。海面上行驶着白色帆船和冒着烟的游轮,船身反射出耀眼的光线。不一会儿,远处出现一片朦胧的蓝色的山峰,那是科西嘉,拿破仑在那儿出生。塔形建筑底下三位留着银白色长发的老妇人,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底下纺着线,白发散落在她们金褐色的肩膀上。
意大利的自然美景让我留恋。有人担心接下来的经历以及见闻全是叙述性质的,都以这种方式诉说我的人生,可能又将遭受到非议,不过马上就能看到那些在旅途中遇到并给我留下印象的人。另外,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所见所闻都给我的灵魂和思想带来了很大的震动,特别是自然和艺术品。比起外界长期留给我的印象,这段新的生活历程给我的启发和震撼要深切得多。这里的田园风光让我陶醉,在黎凡特我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晚,旅店紧邻大海,巨大的海浪冲洗着礁石,浪花在沙滩上翻滚。天上的云彩好像被涂上了红色条纹,让山峰也变得多彩。常春藤吊起一团团树状灌木丛,就像一筐筐被收获的葡萄。
在比萨和佛罗伦萨
在摩德纳公爵生日的当天我们到了卡拉拉。为庆祝公爵的生辰,装饰的花环布置了所有的房子,爱神木的树枝被插在士兵们的帽子上,耳边还传来加侬炮轰隆的声响。我们很想去采石场参观:一条波光粼粼的小河从紧挨着集镇外的路边淌过,到处都能看到如星星一般的白色大理石碎片。开采出来的有白色和灰色大理石两种,偶尔在里面还能发现水晶的踪影。在我眼里,它却是一座魔山。远古的大石头里禁锢着男神和女神,只有伟大的魔法师托瓦尔森和卡瓦诺这两位分别来自丹麦和意大利的雕塑家能够解救他们,让他们重获人间,他们只需等待。
我们已经见过不少稀奇事和美丽的自然景色,意大利给我们的印象就像尼古拉家族,大体很相似。这里让我感到意外的却是我们必须习惯这里的一些不同方式——在旅店时我们经常被要求出示护照,短短的几天被查了不下十次,还要求必须在上面签名画押。我想我们是被骗了。因为马夫走错道,半夜三更我们才到了比萨。进城要经过一系列冗杂的检查,花费不少时间后我们才顺利的地了城。街上没有路灯,唯一发出的光亮来自于马车夫手中的火把,那还是他在镇口买下的。靠着这支大火把引路,我们才顺利地走了下去。
到达目的地阿伯佝·德·乌萨罗费了我们不少力气。我在家信中写道:“我们前一天在粪堆上睡觉,第二天就到了男爵的城堡里,好像吉卜赛人一般。”我们现在住的地方的确是男爵的城堡。可惜我们实在是太累了,只有睡觉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城里有着不少好的景点,教堂、洗礼堂、公墓以及著名的斜塔。戏剧《魔鬼罗伯特》中,公墓经常被使用到,剧院画家通常会用它来布置修道院的场景。公墓拱道里的纪念碑和浮雕其中有一块是托瓦尔森的作品。这块浮雕的内容表现的是《圣经》中“多比亚斯治疗盲人父亲”的主题,他把自己勾画成年轻的多比亚斯。我们还攀上了不在计划内的比萨斜塔,圆柱形的塔身,许多根柱子环绕在周围,顶端没有护栏。朝向大海的塔身上,上面的铁质物件因为海风常年侵蚀的原因已经腐锈不堪,石料也要松软得多,整座塔是泛黄的颜色,很脏的感觉。从塔顶远望,可以看到利古里亚海滨的里窝那。现在想去那里坐火车很快就行,而那时,在马车上坐那么远的路程可不会让人感到舒服。
我们的导游没有一点用处,他说的我们都知道。他最有趣的地方是八卦,“那家没开门的商店住着一个土耳其人”,“有人拿走了教堂里原本挂着的一幅画”以及“刚刚经过的那个人是个大款”。他领我们去看犹太教堂,根本不像“欧洲最精美多彩”的宗教建筑,更像一个证券交易所。人们戴着帽子随意进出,大声说话,让我很不舒服。椅子上站立着邋遢的犹太小孩,几个犹太教士在讲坛上咧着嘴对犹太老人笑着。上面的走廊中有一个个精巧的格子,里面藏满了女人。这里吵闹熙攘,没有任何一丝神圣感。观赏日出是在里窝那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太阳升起的时刻,云变成了火红的颜色,海水波光粼粼,连山峰都被染上了颜色。
佛罗伦萨是整个意大利的象征,很快我们到达了这个华丽辉煌的城市,终于可以一睹它的艺术奇迹。
我并不怎么会欣赏雕塑。我在丹麦甚至见都没有见过。在巴黎的时候也只是像游客一般随意过了几眼,没有见到能让我产生灵感和激情的画作。在佛罗伦萨,美术馆中装满了名画,教堂里拥有着无数纪念碑和精美的艺术品,参观完后我艺术的细胞才真正被叫醒。我站在《美第奇的维纳斯》前不愿离开,我全身心都在体会着艺术奇迹,不可自拔。
她圣洁、高贵、美丽,是神创造了她,她升起在大海的泡沫中。人世间肉身消亡,爱情永恒存在,爱之女神永远长存。
参观美术馆成了我每天都要做的事情,每次我都会被“维纳斯”和“尼俄柏”群雕所吸引。我感受到这组举世无双的雕塑中蕴含着一种永恒的真理;它们放置的位置都相差一段距离,穿行在当中,让我仿佛也成了它们的一体。雕塑中,有一位母亲抱着女儿的头颅,想用石头削成的长袍挡住即将射向女儿头顶的箭。我还看到了拉斐尔的圣母玛利亚像。这里就像一座艺术的宝库,一件件精美的艺术杰作让我对瑰丽奇妙的艺术有了新的认识。从前我没有对此有过特别的印象,也许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图片和石膏模型,所以无法体会到其中蕴含着的艺术底蕴。而现在,我的艺术灵魂仿佛得到了新的升华。
拥有许多巨大的大理石碑的圣克罗大教堂是我参观的最重要的教堂。米开朗琪罗的灵柩周围,被无数极有特色的雕塑、绘画以及建筑物所环绕;但丁的纪念碑也立在其中,尽管他的墓在拉维纳,诗人的巨大雕像眺望着整个意大利,诗歌是诗人最好的灵歌;意大利戏剧家阿尔菲耶里公爵的雕像也放置在此,那是卡诺瓦为纪念他而创作的,公爵像戴着面具,还有一只里拉琴和月桂花环装饰在上面;还有伽利略和马基雅弗利的墓,尽管没有特别宏伟的气派,却丝毫没有影响它们散发出的神圣感。
看到拉斐尔眼中的景色
某天,我们三个一起去拜访另外一位同乡——雕刻家桑尼。正当我们在他居住的区域大声交谈时,一位男人走来用丹麦语问我们:“先生们找谁?” 他只穿着衬衣袖筒,围了一条皮围裙。原来他是一位来自哥本哈根的锁匠,已经在这里定居了九年,并和一位法国姑娘结了婚。我们向他讲述了一些关于家乡的事情。
离开的时候我们决定顺路去特尔尼瞅瞅那里的瀑布,再去罗马。这次旅途实在是受罪,白天被太阳晒个半死,晚上还要跟无数只毒苍蝇和蚊子战斗。这次这个穷马车夫不但没给我们提供便利,还在一路上给我们造成了许多不便。旅店里的窗子和墙上被人涂上了许多关于意大利名迹的赞美之词,但这种行为对它们是一种轻渎,这并不能代表什么。我只知道,这片土地给我带来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我打心眼里热爱它。
穷马车夫的马车还能将就,它带着我们从佛罗伦萨开始了一段痛苦的旅程。准备出发的时候门外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看起来有些像《圣经》中的伯约,浑身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还在用陶瓷片清理着身体。他围着车绕了很多圈,表达着自己要上车的意图,被我们坚定地拒绝了。还在僵持的时候,马车夫告诉我们,这是他的第四个乘客,是一位罗马的贵族。我们只好让他坐了进来。可是他从上到下的衣服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和他在一个车厢简直坐如针毡,浑身不自在。一到下一站,我们就向车夫表示,如果他还和我们一起我们就不去罗马了。手舞足蹈比画了好久,这位绅士才坐到了车夫旁边的位置上。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我心里有些愧疚,不过我们没办法和这个家伙坐在一起,也只能让他淋淋雨了。
路上有不少散发着浪漫情调的景色,就是阳光太过恶毒,还有一群群恼人的苍蝇在头上飞舞,吵得人心神不宁,我们只好用香桃木来驱赶它们。马比我们更惨,苍蝇不停地扑向它,仿佛看见一块腐肉一般。晚上我们住在黎瓦纳的一家小旅店里,旅店难看又简陋。我看到那位贵族一边帮店主收拾晚上要吃的鸡,一边借着烟筒边的火烤着身上湿淋淋的衣服,还不停地诅咒我们早晚会有报应。报应来得很快,睡觉的时候为了透气,我们敞开了所有的窗户,结果第二天起来,我们身上鼓满了被蚊虫叮咬的大包,有些已经被抠出了鲜血。大致数了下,光我一只手臂,至少起了五十七个包。脑袋还有些发烧,真是痛苦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