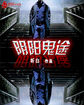村里新盖了一栋商业广场,几个朋友约我去看电影。尽管现在管这儿叫做街道,我却还是喜欢叫它村,街道是这两年前改的,同它一起改的还有户口本上的城市。除了马路边那几栋窗户挨得密密麻麻,看一眼放弃数数的楼层建筑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小的变化还是有的,比如村里的人说话的声音更大了,穿得也花花绿绿了。
其实电影在自家的白墙上完全可以投影着看,可是总有小孩在跑来跑去尖叫喊叫和大人争吵谩骂或者划拳劝酒的声音常常震得屏幕都是抖动的,没过一会儿就忘记之前在讲些什么了。所以我并不害怕看恐怖片,相比较之下,如果它能安静不伤害我,倒是愿意把我的空间分一半给它。可是我朋友一点儿都不喜欢这类的电影,他们更喜欢那种理解真爱的剧情。
影院里是两两一座的沙发,我们五个人,我选择自己一个位置。现场一片哗然之际我却觉得像是看邻居小孩玩家家酒一样想发笑,不到二十个人的场冷气开得很足,我甚至看到出风口上夹着的纸片被吹飞,不知道是不是也有细碎的纸片瘙痒着我的鼻腔,我有些难受,双手捂着打了喷嚏,鼻水不自觉要流出来,抬头看着满屏的鲜黄艳红让我眼睛发涩,突然响起的大声配乐猛地我寒毛直竖,悄悄从后门出逃便发消息告诉他们我先行离开。
八月的天气,全国都普遍高温,商场里恨不得直接带你到下个季节,橱窗口的针织外套看着柔软舒适,心里还想着穿上会是什么模样,走出玻璃门马上打消这个念头。像是从冰箱里捞出来的冰棍额头上立马冒出大大小小的汗珠,嘴唇也干燥起来,道路两旁全是不足我高的小树苗影子都没有我的大,脑袋嗡嗡直响,像是一只苍蝇飞进了我的脑子却找到出来的路。
到家一千米的距离我的双腿抖擞,双脚打颤看起来像是马拉松的最后一千米,我甚至都没有力气拂去任凭汗水流入眼眶,咸得才想起我带的隐形会不会损伤到眼睛。终于到家了,简单收拾了一下回到轻松的状态,打开手机发现没有网络了,家里的路由器坏了,维修的人说至少明天才有空过来一趟。现在我又后悔了,要是我还在影院至少现在还有点事做。
想是这么想,可让我一个人又重新走过去我也是不愿意的。路上有很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人总喜欢盯着我看,尽管我的帽子大到足以罩下到我的肩膀,可他们同阳光一样炙热的目光还是能够穿过层层防线,他们是极喜欢这么做的,然后在你走开不到三步的距离用你还能听见的声音说着话,“这是谁家的孩子。”
“怎么会干瘦成这个样子。”
“实在是不好看。”
“遮得怎么见不得人。”
“是外地来的北子吧。”
“……”
我没有常常在路上走,也没有去串着认识村里头的人。每一个陌生的面孔,不熟悉的声音遇见几次都是这样。我试图忘记刚刚听见的声音,燥热的夏天需要可口的西瓜,被我放到井里的小桶上乘凉,冰箱已经满满当当,尽管里面全是一些不需要的塑料和纸盒,那是妈妈的地方我一点都不能乱动,我怕极了她发脾气的大喊大叫,似乎要穿透我的耳膜震碎我的脑仁,如果村里举办大声喊叫的比赛,她一定可以拿到不错的名次。这么想着我边小心翼翼地钓上来我的西瓜,只有小桶那么小的西瓜,爷爷说除了皮什么都没有,我偏不信,便要了来,我要亲自剥开来看看。
瓜很硬,不过爷爷说是熟了的,小而熟注定不是什么好果子。
磕磕绊绊地我终于剖了开来,我愣愣地看了一会儿,黑黑的籽甚至都不匀称,厚厚的皮,里头粉的白的就是看不见红色,才没有多久,不知从哪儿飞过来一只苍蝇便开始嗡嗡地舔舐着瓜里淌出来的汁水。我奋力地挥着手臂,可是很细它甚至都能从我的指缝里飞过,我气愤极了,找来半米长的杆那头连着方形网格的柔软塑料,可它实在是太快,我的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不足以分辨它在哪个位置,它又扑腾着翅膀离开。
它停在桌上的粉红汁液里,我一掌过去,它却又飞走了,只有被我溅得到处都是甜水等着我收拾。好几分钟都是这样,任我如何突袭它都游刃有余。它趴在瓜皮上像是啃食,我瞧了一眼,累了,任由它去吧,我又看了一眼,它似乎没有再动作,我便一起身,猛地挥过去,果然,它踉踉跄跄地要起飞,又被我一掌拍掉在瓜囊里。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整个瓜都给它陪葬了,它是死了,这个瓜也不能要了。小而熟就不会是好果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