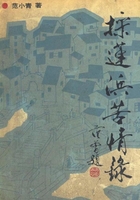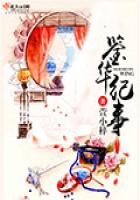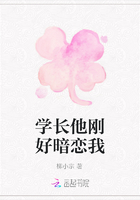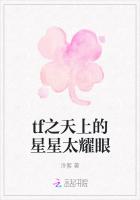2008年7月,李思达28岁生日刚过完没多久,他这间租屋便迎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客人”。这人便是程玫儿,贵州一户农民家的女儿,也是李思达的母校武汉大学的跨届校友。因为她是贫困生,所以有缘成为李思达的资助对象,也是他唯一的资助对象。
李思达对程玫儿的资助是从2005年秋季开始的,正值程玫儿大一升大二。
那年,离校有年的李思达受邀参加武大的校庆,在母校与两位昔日同窗偶然相遇。老同学久别重逢,煮酒论英雄势在难免。开怀畅饮间,李思达得知那两人与他相似,或早或晚地选择了去上海发展事业。面对这种不谋而合,李思达给出的理由最为充分。
“其实说白了,理想不就是离乡吗?离乡去哪儿?北京拼的是背景,我早就输在起跑线上了,上海是商海,来碰碰运气也还算明智吧?想必二位也是。”
同窗加同城,此类相聚,虽不似“冤家路窄”那样夸张,可口味寡淡的家常联谊远不及辛鲜麻辣的同门攀比来得酣畅淋漓,这是不争的事实。那种快感,好比十年一度的华山论剑,同样惊险刺激,任你三十年河东还是河西,酒走一圈便可分出高下。
这一攀比,就攀比到“回馈母校”这个焦点上来,这也许是当下展示各自实力最完美无痕的表现手法。说到底,无论是为了报恩而狂秀肌肉,还是为了狂秀肌肉而报恩,都还算是健康可爱的。
李思达自然也不甘示弱,当下表示正有此意。第二天,他与那两人结伴,与学生会帮扶结对活动的联络小组取得联系,在一叠名单里相中了经济条件最糟糕的程玫儿。
最终,李思达虽在资助人数上不比那两位,但有幸选中最急需的资助对象,其意义也相当非凡。装×有时也未见得就是坏事,正如李思达平日无心哼唱的那首被改了词的老歌:只要人人都装出一点×,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李思达当场签下一份贫困生资助协议,承诺资助程玫儿三年共六个学期,每学期的资助金额为6000元。这在2005年算得上一项慷慨的善举,只因那时李思达有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
可他当时没有计划与程玫儿见上一面再走,甚至连权衡那样做的必要性都省略了,校庆一结束便匆匆返沪。
此后,李思达每学期都会收到一封校方寄来的成绩单。他与程玫儿也同步保持着书信往来。他的书信,多是些礼节性鼓励的话语,催她上进。程玫儿对恩人自然是感激不尽,每每总要长篇累牍地表达那样一种味同嚼蜡的单一情感,其间少不了还要点缀些“学成后报效祖国”一类足以铭碑的励志豪言。直到程玫儿毕业,三年间共六个来回。
尽管李思达这种小人物对资助生将来是否真会报效祖国并不十分关心,也从未奢望能得到她任何意义上的回报,这是他善良的一面,至少保全了做人的本分,可他无论如何也难以设想,因果循环有时也会离谱地跑偏,终有一天,曾经对他感激涕零的人也会在他胸口插上令人绝望的一刀。
作为一个新上海人,李思达曾经小有成就。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来上海之初,曾就职于一家报社,第二年便跳到了房地产行业,一干就是五年。起先他在一家房地产公司搞企业宣传,一年后这家公司成立了一个有关地产广告的子公司,由他负责,管理着十几人的小团队。
到了第三年,他们的业务独立出来,拓展到全行业,并独立创办了上海市第一本房地产期刊。后来他又与高校联合,挂着房产经济学会的招牌创办了一本房产金融学术杂志,吸引了很多投资,也拉来了大量的广告,为母公司挣了不少钱。李思达本人也因此有资格认购了母公司一定份额的原始股。
2007年,母公司在A股上市,李思达一夜之间跨入了“百万富翁”行列,新股上市15个交易日内浮盈500万。母公司的老总,也就是李思达的大老板赵浮云,更是坐拥近8亿股票资产收益。
春风得意之时,李思达交往的都是上层名流。他与海外投资商谈过合作,跟大开发商打过高尔夫,也曾频繁出入高级会所,与同行精英交际,与售楼小姐逢场作戏。但喧闹繁华过后,他还是要回到自己的租屋里睡觉,而且睡前唯一不会缺席的一件事便是读书,他只读文学,那能让他的心安静下来。
很显然,这个阶段,李思达手头的现金不足以买房。曾有温州炒房团的女业主通过开发商认识了李思达,见他长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才,开价一套内环内三居室,想长期包养他。那女人四十出头,早年死了老公,手里有39套内环内公寓的房本,和16套内外环间大户型的钥匙。
李思达起初把那女人当朋友交往,当对方提出了如此龌龊的交换条件后,他甩下了两句话,便再也没和那女人通过一个电话。
他反问那女人:“你觉得我是缺女人呢,还是缺房子?”
女业主说:“当然是缺房子,我知道你住在哪儿。”
他又反问那女人:“那你觉得我是缺一套房子,还是缺55套房子?”
女业主愣了半天,明白过来,恼怒地说:“别不识好歹,你顶多就值一套房子!”
李思达牢牢记住了这句令他每每想起都会备感耻辱的话:“我顶多就值一套房子?”可他不会想到,未来的某一天,当他再次想起时,这句话竟然完全变了味,变成了,“唉,我好歹也值一套内环内的房子。”
李思达的原始股进入流通领域发生在股改之后,属于“小非”,一年内限售。不过即使不限售,他也坚定不卖,因为大多数人都抱定了三年不卖的想法。与他份额相近的人甚至都在憧憬着成为千万富翁的那一天。
可他怎能想到,根本不需要三年,仅仅一年多,他的持股金额已缩水到不足80万。2007年到2008年,那是一场全球性的世纪股灾,而A股在那场全球高台跳水中,又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悬崖跳水表演。
李思达很清楚,要想在上海立稳脚跟,尤其是在上海的地产圈立足,他最起码要有一套中环以内的房子,面积还不能低于100平方米。那时的中环,基本上等同于上海的全市均价,可即使他全部抛空股票,80万连半套房子也买不到。
在经历了A股惊心动魄的大波浪之后,全民疯狂炒股演变为全民谈股色变。而此时的李思达非但没有理智地止损,反而渐渐爱上了这个令人血脉贲张的刺激游戏。
2008年4月,他孤注一掷去抄底,新老资金一起参与搏杀,此时的李思达已经红了眼,欲罢不能。他从小并未吃过多少苦头,一向不信邪、不服输,哪怕是在这样一场血淋淋的金钱游戏之中。
到了7月,也就是程玫儿站在他门口的这一天,他已经彻底绝望了。A股持续下跌,深不见底,他的持股金额只剩40多万,而他的银行账户,也只剩下10万余元。
恰逢此时,他又遇上家乡的死党赵勇找他借钱,这一借,又借去他存款的一半。他在心里算过一笔账,假如解禁当天立即抛空,他如今至少已经拥有两套中环内的房子了,而且都是百平米以上的面积。不过想必他的老板更有资格捶胸顿足,赵浮云属于“大非”,禁售限售的规定更严格,据说至今都未出手。
李思达对程玫儿的资助,到了第三年,也就是程玫儿大四这年。金融危机波及房地产市场,由他一手创办的期刊停了,公司业务也一路下滑,入不敷出,他终于被母公司扫地出门。
此后的李思达,除了在一家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公司打过一阵子短工之外,整个一年几乎都处于失业状态。存款也基本耗尽了,最困难时几乎付不起房租。
可他不仅没回长沙老家,还没中断对程玫儿的资助,倒不是忌惮曾经签下的协议,而是他觉得,那样做的话就等于彻底认输了。他发狠似的咬着牙跟自己说:就算死也要死在上海!这辈子大概只会做这么一件正儿八经的善事,如今只做到三分之二就放弃,成何体统?
这不,一晃三年,如今刚毕业的程玫儿来上海找恩公了,正赶在苦苦支撑的恩公最为潦倒的人生阶段。
按照程玫儿三年来的想象,恩公理应是位足以配得上“显赫、成功、辉煌”等一系列华丽词语的爱心大叔,最低限度不会辱没武大的招牌。她早有耳闻,李思达曾是当年武大的“风云人物”,而今又无可辩驳地拥有着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实力。
其实呢?当年李思达曾是个要求进步、善于经营关系的学生干部,上海话叫“头子活络”,否则校庆时也断不会有人念及邀他。可谈及“风云人物”,那便言过其实了,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拿不出点特殊贡献,最终都是“浮云人物”。
涉世未深的程玫儿来不及懂得,现实就像惊蛰后的春蟹,撬开幻想之壳,里面只有满满的失望。而且更要命的是,她此番来访,真心是拿李思达当“贵人”来投奔了,寻求深一步援助的念头压倒了一切。当然,“特别想与恩人见上一面”是必要且合情合理的“荫头”。这是她跟舍友们讲的原话,也是真心话,也因此又得到一张额外捐赠的火车票。
开门看见程玫儿的第一眼令李思达永生难忘,因为这也许是他这些年见过的与这座城市最格格不入的人了。为了给恩人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程玫儿特意穿了一身素蓝底印花旗袍。
那是有一年过年她娘亲为她置备的新衣,语重心长地交代她:“娃儿,乡下不比城里,虽说时髦不是我们赶得上的,可进出总得有件上点档次的衣裳。”
这身行头映射到李思达的眼里,以为她初来上海之前,一定恶补过电影里的老上海。可即便是老上海,也鲜有此等极品“怪咖妹”。只见她脚蹬一双大红圆头皮鞋,脸上化了极致浓艳的妆,唇似生食过死婴般的血红,眉似儿童标高线般的浓重,大圆脸盘,覆以墙灰似的粉——本是白底,却混合沾染了硬座车厢里舟车劳顿的尘灰。不过幸好这一幕发生在光天化日下。
程玫儿眼里的恩公,也同样令她吃惊不小。
他有着七分英俊、三分斯文的脸庞,换在她们乡下,这顶多也就是一张20岁出头的面孔,怎会有30岁“高龄”(信中李思达自称“而立”)?只不过被那一头乱发及懒散的背心短裤打了折后,英俊只剩下五六分。
酝酿已久的“大叔”称谓顷刻被程玫儿咽回肚里,开口便叫他“李大哥”。
事实上,在她从火车站一路赶来的途中,心里还一直在纠结见了恩人要不要“跪”的问题,在她们乡下这是必须的。可接受了四年高等教育,如今又身处摩登之都,她忽然感到不合时宜,生怕这一跪反而疏远了三年来与恩公以六封书信建立起来的朦胧亲近,那是一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
问明身份后,李思达热情中夹带着意外与尴尬,请她进屋。当然,随后的交谈中他是不会直白地告诉她,这副妆容差点把他给吓死了,只因他很了解贫困生的日子有多艰辛。就他定期给的那些钱,四年来她怕是连一场电影也没机会看,更不要说经常领略电影里的老上海了。
程玫儿暂住了下来,就睡在小客厅的沙发上。除了见面一刻的尴尬,李思达对自己的境况倒也坦然得很,这缘于他在既陌生又亲近的程玫儿面前无愧于心,尽可以大大咧咧。可他意识不到,这其实也算得上是一种隐性的心理优势。
接下来几天,两人相处得和谐融洽。程玫儿把屋子里里外外好好收拾了一遍,李思达几次要给她搭把手,都被她拿手一挡,“大哥你可别沾手,玫儿生就劳碌命,一刻闲不下来,一闲下来就浑身不自在。”
李思达笑,只当她客气,不再与她争。可接下去几天,李思达发现这丫头还真是闲不住,啥活都干,想必苦孩子都是这般勤劳。李思达这回倒也心安理得地享受起全方位的家政服务,三餐来时张嘴,拖把来时抬腿,过的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
渐渐地,程玫儿发现李思达无班可上,每日除了面对股票的K线图发呆以外,就是疯狂地打游戏。他偶尔也出门,但多半不是去面试。因为就连一次面试经验也没有的程玫儿都不相信,会有人穿得那么随便去面试,她起码还晓得要穿上隆重的旗袍才有足够的底气来敲他的门。
也算是让程玫儿赶上了,李思达以往没日没夜赶稿的情景她是没看见,电话里与同事研究策划方案到凌晨她也没听见。她只知道,自她走进这间房子的那一刻起,见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大闲人。
来上海之前,她对上海及在上海奋斗的人,印象绝不是这样的。上海的白领们难道不都是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瓣用的吗?她竟然是被这样一个大闲人整整资助了三年?
就在程玫儿上门之前,李思达正处于人生中最颓废的阶段,人性中一切负面皆被放大并释放了出来,在他身上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懒散,从未有过、难以自制的懒散。那一阶段,无论懒人能够被分为多少层境界,李思达都绝对稳居“高处不胜寒”的那一层。
李思达终究明白,他在上海没有半点根基,若不想以失败者的面目回到长沙,他必须迅速站起来。程玫儿的到来,对李思达而言曾有过小小的触动,让他回想起过去三年自己走过的路。他暗下决心,待他的股票稍有回升,他定要割肉出局,然后告别这间租屋,去万航路买一套仅容纳得下他一个人的酒店式公寓。
李思达意识到,要想真正让心安定下来,进而去开创另一番新事业,只有一条路可走,那便是尽快了结他与股市之间的恩怨。当一切都还没有到来之前,他无法说服自己重新走回职场。
但凡与股票这个魔鬼打过交道的人都会理解,这是一笔纠结账。当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即使他把自己宝贵的时间全部奉献给职场,每月领到的薪水都未必够在股市上赔一天时,纠结账就变成了糊涂账。
后来有一天,程玫儿眼见着刚拖好的地板又被外出归来忘记换拖鞋的李思达踩成个“大花脸”,他还将脱下的T恤揉成一团,从客厅中央穿越厨房门,像掷保龄球那样朝洗衣机抛去。结果偏了,掉在厨房间湿漉漉的地板上。
“懒人!”程玫儿第一次以中性语气骂他,脸上还不敢不赔着苦笑。
李思达先是一愣,转而笑了,振振有词道:“不要忘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程玫儿:“这我知道,然后呢?”
李思达:“然后,懒惰、安逸、恐惧,始终是推动人类科技不断向前发展的三大原动力。”
程玫儿:“嗯,所以呢?”
李思达:“所以,追根溯源,懒惰是第一生产力!这很容易推导。”
望着他光着膀子认真的表情和久久竖在半空中的那根食指,程玫儿被逗乐了,彻底拿他没辙。不过李思达这人除了懒,倒是一点恩人与主人的架子也没有,这让寄人篱下的程玫儿深感精神上的自由快慰。
可转过身去,李思达的心里却没那么快慰。如今竟连上门投靠他的人都对他不耐烦了,他可真的需要痛定思痛了。可他又有什么办法,至少此时此刻,程玫儿的勤快似乎并非是在帮他,反而将他往懒散的深渊里又推了一把。
无聊时,李思达会主动跟程玫儿聊些都市生活趣闻。比如时下的新潮玩意儿、上海的风土人情,当然还有她即将面对的职场生态。可唯独避而不谈值得一去的好玩好吃的地方,因为他没心情更没钱带她出去玩,同时也想当然地以为,像她这种苦出身的孩子,应该不会有多大的玩心。
谈及上海的帅哥美女,李思达表现出异常的兴致,却又突然显得口拙。尤其是被程玫儿追问有没有女朋友时,他的眼中瞬间失去自信的神采,犹疑不定地交代,他正追求着一位名叫花想红的女孩。
据李思达描述,那女孩生在富贵家庭,才貌不逊柳如是,名字里又有个“红”字,所以熟人偶尔会玩笑似的叫她“红富是”。再多他就不乐意说了,最后只用“水中月镜中花”草草结尾,可心里却没有嘴巴那么洒脱。
至此,程玫儿的恩人终于从天界落入凡间,与她站在了同一条地平线上。
但这种和谐只持续了一周半的时间,随着一个女人的闯入,宁静很快被打破了。或许,说那女人半道“闯入”是不恰当的,因为她已在李思达凌乱的生活里存在了好几个月,成为一串串间歇浮现的“省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