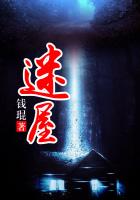“阿春,生日的愿望是什么?”
白酒色的加长跑车穿梭在城市里的一头,周遭的建筑如同钢筋铁骨的森林,密不透气,人群很多很杂,路不算宽、人也不守纪律,所以车速提不起来,只得透过车窗往外静静看着。
三类城的人口比例是最多的,比起十几年前,这里可翻了八九倍。
车内放着Enigma的《Sadness》,原本天籁之音却在此时显得神神叨叨,阿春想着昨晚的噩梦,现在看着路上密集的人群,各个都像光头。
连同这辆印着“公务”的两字,与周遭的人群显得格格不入。站在街道两旁的人,红男绿女的,有穿着嘻哈的、朋克的,也有古朴的,性感的,高跟鞋和木屐,破洞牛仔裤和破洞丝袜,红色襦裙和黑色氅衣,机甲的,又有不少个伸直了自己的一只义眼,眼珠转动着往这车里看,可惜被这车子屏蔽了。
“诶,这导航也真是的,往巷子里撞。”山也看着窗外形形色色的人,很烦躁。
“省电,山科长。”小木倒是见怪不怪,四处望着。
“哎!南方这边怎么搞的,脏乱差。”山也说着,又伸手指点着车玻璃,“你们看你们看,那边是不是在打架了,围着一群人。还好不走那条路,真是的,官定城没有压路机吗,开出来跑两圈,教他们做人。”
“三类城都差不多吧,城中就有蓄电的了。”小木伏在方向盘上,手跟随着音乐打着节拍。
山也左顾右盼着,“阿春啦,申报赶紧的,往铳都填,我这边有人,想办法给你办下来。”
“这里人多热闹。”阿春头靠着另一边车窗。
跑车在街道扭过来扭过去,终于突了出来,来到了一座桥头,这是一座长长的跨江大铁桥。
官定大桥。原本一公里多一点,由于沿海水位上涨,已经漫到了这座城,使得城市被原本不算宽的河流,愣是分成了五块岛城一般,因而桥身又加长了五六公里;桥有三层,在使用的两层,最下一层可能过几年就要被淹了,已经不在使用和检修状态。
“呐,你看看,海水都漫过来了。我说你这丫头,年头跟你说到现在了,你放了心在上面没有?”
“这里不好吗?”
“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呐,我跟你说,今年五七年,呐,再过三年,新世纪了,乾纪一元一运,一运,‘一白坎’知道吗?呐,八卦里坎为水为险,再过三年,满世界都要被水淹咯,还不走!”山也把手伸到了阿春脸前,掰着手指头数着。
“哎呀臭!”阿春拿掉山也的手,“真那到时候,走到哪里还不都是死。”
“诶我说你这丫头,不听教,”山也着急了,“我说小木,是不是,现在沿海都沉没一大片了,我今儿个早上开的会,堂里还在讨论,呐,现在海里还出了未知生物,抢险工程出很多问题,我们铳都还得紧急往那边派人想办法哩!”
“是的,山科长说的对,现在沿海情况不容乐观,但是水位涨得也不算太快,三年后按这个速度估计有个三四十米,铳都啊,往内陆和西北都是很安全的。”小木回头说道。
“听到没有,人家一个二十岁的小伙都比你有觉悟!”
轩国记年是按的“三元九运”。在太阳系的九大行星中,土星与木星每隔20年就要相会一次,处于同一直线;而每隔60年,土星、木星、水星就要相会一次;最后每隔180年,九大行星就会处于太阳的同一侧,分布在一个小的扇面中,形成“九星连珠”。古人根据这种规律划定“三元九运”的时间体系,以180年为一正元,为纪,有“乾纪代表天、坤纪代表地、仁纪代表人”依次循环,而每一纪又分一、二、三元,每元60年,每元分三运,即一至九运。
古人又将这九运纳入八卦中,是谓“一白坎,二黑坤,三碧震,四震巽,五中黄,六白乾,七赤兑,八白艮,九紫离”,因此每运20年,对应的卦象往往预示着这20年的时运。
仁纪三元五十七年,正值九运,九紫离,为离,离为火,为网络科技;再往后三年,就又循环到了乾纪一元零一年,值一运,一白坎,为坎,坎为水,为险境。所以按如今的时事,山也这老头子说得也不无道理,不过平常老百姓看这个东西,信则有、不信则无。
“啧啧啧,神神叨叨的。歌曲也是。”阿春望着江流。
“诶你们年轻人,就喜欢唱跳Rap。切歌。”
“好。”小木应道。
“不喜欢。”
“那就情歌?!”
“都不喜欢,关了。”
白酒色跑车驶过大桥中间时,阿春打开了车窗,呼呼窜进来的风,吹开了她的头发。外面阳光刺眼,她望着远方那片不算高但是崎岖又连绵的青山脉,那个山头,是城里规划的一片公墓地。那里有她舍不下的人,那个雨夜即使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却依然在她心中轰隆轰隆的下着,晴天也一样,每一天都一样。
你是最棒滴!
要有自信啊!你是最好滴……
努力,加油……
嗯,努力加油。
*
阿春他们来到一座环形布局结构的大厦,驿马堂的购物广场。
三个人在里面洄游逛着,左边的小木一身休闲装,套着的墨绿色钓鱼马甲,很工装很攻壳;中间的是阿春,穿的是灰白的、宽松又性冷淡的那种衣服款式,还背了个大书包;再一旁的,就是古朴的老头子了。高矮高,三人转来转去,在大厦里一会上,一会下,手上要提的袋子包包也渐渐多了起来,在这座热闹的大厦里,算得上是一道风景线。
一路上对小木有意思的性感女人,抛的秋波也是不少。
大厦的旁边,外面,刚好挨着的是夹在高楼林立中的一座博物馆。
这是南方这一片算得上非常贵气有名的博物馆了,不高,九层,不单是天长地久的意思,因为南方在八卦“离”位,数九。单从外面看,你不会想到这是个博物馆,更像个老写字楼,一座方方正正的黑色建筑,不过里面确实精美堂皇。
观赏的人比起马路上的人头攒动,不算太多,多半是这城里的人不太注重这些老古董老文化,又或者他们足不出户也能在网上看得真切仔细。结实的全景摄像头到处安放着,它们突出来的现代机械化造型显得跟室内文艺古代的设计很不和谐,但是就是这样突着,大概是在头上警告每个观赏的游人,不要乱搞。
三楼,一个束发的男子径直来到了一件宝物旁,他把围脖套在了脸上蒙了起来。
玻璃箱里面的宝物,是一支精美的四十公分高的大花瓶,下面写着:
史家塑·元朝官窑特供瓷
“导师,是这个吗。”
“是的。”
这个束发蒙面的人的电子脑回路里,在跟另一个人远程对话着。
“好的,马上开工。”
“神与你同在。”
“神与我同在。”
嘭!————嘭!————
一楼博物馆大门,那里连续炸响了巨大的两声,整栋楼都震动了!这是两颗早就安放了的定时炸弹,竟然瞒过了所有预警系统。不幸在门口的保安和几个普通平民都倒在了硝烟和废墟中,随之现场发出了杂乱惨叫声,此时馆里的各种指示灯全部亮成了红色,滴唔滴呜的警笛声也随之响起,顿时一片混乱。
博物馆的其他安保和机器人正在赶来,另一头城中派出所也接到了警报。
三楼,这个束发蒙面的男子趁着混乱,接着手里又拿出一些装置,对着面前这个玻璃就开始各种干。
嘭!——嘭!——
又是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原来三楼这一层的一面墙,也被炸了个大窟窿,竟然联通到了对面的驿马堂购物大厦!从烟雾中探出来的两个人,应该是接应的同伙。
这一层的人们也是被吓得鸡飞狗跳,纷纷逃离此楼层。
咔咔咔,此时坚硬的玻璃这时候也被钻破了……
露出的一个圆孔,刚好够宽,束发蒙面的男子随即伸手去拿大花瓶,结果一刹那被防盗装置放出的电流电得在原地抽搐,自己埋在身体内部的各种机械、电路和显示灯也乱跳了起来。
另一个扎着黑色脏辫的同伙见状赶忙跑过来,一脚想把他给踹飞了!结果也吸在一起……两人姿势奇怪地在黏一起抽搐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的冒着火花!真是始料未及,一波又起。
我靠哟!
“断电!断电!还没搞定?!”还剩下的那个同伙,蓝色的头发,他看着心急又无能为力。
“89%,预计六秒攻破……”
“他两个傻逼要被电死了!”这蓝色头发的家伙也用着电子脑回路跟人沟通着,看来外面还有人对接,他随后又向三楼左右两边通道各扔了两个定时炸弹,接着从后背掏出了两把UZI轻型冲锋枪摆开,“有人上来了没有?”
“有!前门五个,后门三个!”
“黑了他们机器多少了?”
“67%。”
哙!但愿机器人没赶来。
一秒。
两秒。
嘭!嘭!
两颗定时炸弹炸响了,蓝色头发的家伙开始往两边狂射子弹。因为像博物馆这种国家机构,是对义眼做了限制的,他们在这些环境即使有网络有数据也不能全面定位透视,因此需要外接黑客来入侵系统获取数据,此时他是估着时间提前开枪了!
子弹“突突突”地往两边凶猛地打着,大楼电力此时突然全部中断!室内一片漆黑,那个炸出的墙洞,这时候像个大圆月一样,衬托着这个人影,他双臂摆开大字型,两手中的机枪口冒着持续闪耀的花火。
“你两个赶紧的!”蓝色头发喊道。
“呼噜呼噜,”柜子旁边的两个家伙,嘴巴都电麻了,还好这防盗的电、罪不至死,“呼噜呼噜,妈妈的,麻哦。”两人吃力地控制着,调整着,然后拿起花瓶往皮袋子里装,好不容易搞定,又边走边颤抖了两下,“呼噜呼噜……”然后往大厦那头跳了过去。
随后开枪掩护的蓝色头发也跟着转头就跑了。
三人的脚下都伸展出了一排滑轮,快速地在大厦里上下穿梭着玩命逃跑。人们被他几个撞的撞开,打的打到,另一些围观的看着吹起了口哨,管他犯了什么罪,在他们眼中更像一出精彩的跑酷舞蹈。
他们三个这种的,在三类城市不少,他们干着黑客、偷盗的事情,因为标志性的经常使用机动直排轮和喷气滑板,速度快而灵巧,因此人们戏称他们为滑滑头鬼,他们自己也欣然的接受着这个舶来名,还加了个英文,KK,KingKong,酷酷的KK滑头鬼。
……
阿春这边,他们也被刚才一连串的爆炸给震住了。
大厦里的人群也嘈杂了起来。
“官定城每天都这样?”山也骂咧道。
“不少。”阿春靠着围栏,探了个脑袋出去,想看看下面发生什么事了。
“诶太危险了,赶紧来铳都。”
“小木你把我的背包给我吧。”阿春转过身,原来她已经换了个妆容,头发盘得有模有样、还插了个蝴蝶发髻,一身古风的浅绿色的短款右衽,上面的图案也是大大的蝴蝶和花草,露出的一双乳白色大腿,很漂亮。
“好?”小木应声着。
“你包里什么东西,你干嘛?闺女你今天休假的!”
“除暴安良呗。”
“喂!”
没给山也这老头子拦住,阿春带了个黑色的眼罩装置,滴滴滴地启动后,她竟然直接从大厦的中庭跳了下去,这层可是十七楼啊喂!随即她又在半空中,从后背包里唰唰地扔飞出了两个白色金属圆球,后者呲呲地打开螺旋翅膀飞了起来,那是公安配备的新型XJ-031无人机,而她自个则头朝下脚在上、一股脑地往下直直坠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