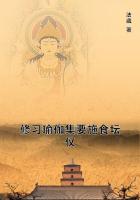但他包子少爷的速度,也不是盖的。
玄气可借万物之息利为己用,今日正巧刮的是南风,包子脚底聚微弱蓝光,轻巧踏风,小巧的身躯不需使太多的力,便能十分迅疾前行。
半刻功夫,到达军库附近。
收势,隐于树后,君小宝闭眸倾听由风中传递的院中动静,确定守卫巡逻人数。
守卫不少,却没几个中用的。
武阶纷纷处于低下的二三级别。
感觉到巡逻的侍卫在自己所在的方向晃荡几圈后,便绕向了另一方,君小宝神色一敛,低道:“花花,别睡了,我们进去。”
悄声吩咐之下,君小宝跑到库房墙跟,脚下借风奔走,在不被人察觉的施力之下,从墙头一翻而跃入,身形如闪电般,快至不能辨别,闪身到了库房把守较为松散的后门之处。
有两人把守。
为了速战速决,包子决定不闹过大动静,悄然潜入便可,他本就是来偷东西的。
包子躲在花圃之后,从袖中拿出花小虫,压低声吩咐,“花花,快去。”
花小虫不情不愿的爬出来,伸懒腰,又是跳脚又是挥爪的,唧唧哇哇的无声比了一堆虫语,叉了腰很得瑟的哼唧两声,这才转身趴在地上,像一般的小胖虫一样,向库房中爬去。
君小宝无语。
玄叔叔说兽宠不能纵着来,否则会蹬鼻子上脸的,它刚才那一系列动作分明就是在说你又要劳烦本虫爷,还打扰了我虫爷的睡眠,不过我虫爷大发慈悲,就帮你这么一回,谁要你君包子离不开我呢!
这虫,也许是因为越来越胖的关系,最近真的越来越放肆了。
君小宝一抬头,只看到花花悄悄爬上了一个人的脖颈后,张开口,啊呜一口,咬在了他的脖上,随之跳到另一人身上,同法炮制,也是深深咬了一大口,才跳了下来。
被咬的两人,不出一会儿,两眼就泛起昏,纷纷倒了下去,坐在地上睡着了。
来前特意要花蛟喝了迷魂香。
这药对兽宠无效,若是以迷香散出也容易留下痕迹,但通过咬噬将迷魂香渡入人体内的话,不留证据,效果更佳,是能成为瞬间令人沉睡的高级迷药。
一举两得。
花花竖起身躯,摆出胜利姿势,示意君小宝赶紧跟上来。
一副相当臭屁想当主导的架势。
小宝嘴角抽了抽,快步跑了过去,抓起了花花放在了肩头上——然后,蹲下身,凑近那两人闻了闻,突然朝花蛟呵呵一笑。
花蛟一哆嗦,心有戚戚的打了个问号。
这娃,越笑越没好事。
“我猜,这两人至少半年不曾沐浴了”,君小宝一笑,话语听似感激,“花花,要你亲口咬他们,辛苦了。”
花蛟虫身唰的一下全白,僵化了。
这死小子……
呕……它要吐了……它要三天喝不下海水了……
小宝看到自己善意的提醒和善良的感谢获得如此效果,满意一笑,拍了拍它的头道:“乖,以后听话。”
花小虫趴在他肩头,无力呜咽……
它有个恶魔主子。
君小宝进库房,一路谨慎前行,保持着不慢不快的速度,观察机关,黑色小靴经过步步估算后,才小心翼翼踩在地砖上,慢慢前行。
到达深处,他立即停了脚步开始搜寻,谁道两脚一动,右手旁忽然一道高大的身影闪过,那人与君小宝同样穿着夜行衣,带着银制面具,月色下只能看到那一双眼睛,是一种淬寒的明亮。
君小宝一愣,气息好冰冷的男人。
浑身都是冷意,就连目光,都没有掺杂半点温度。
那人盯着君小宝,一双手,似动非动,好似下一秒便会使出杀招,致人于死地,又好似会停在那里,一动不动,一直看下去。
君小宝还未及分辨对方是敌是友,那人便冷漠转过眼神,什么也不说,脚踩侧墙,腾空向上飞起,轻盈的跳至天窗处,无声离去。
那一瞬,君小宝感受他使出的气息,不甚又看到他那夜行黑袍底端绣制的徽痕,不由变了脸色。
琅邪宫印!他琅邪宫使用的徽印!
玄气,因为那人收放自如所以包子感觉的很微弱,但这却能辨出这是玄气没错!
他抬脚便追,踩上天窗时,竟见那库外早已没了那面具人身影,徒有半轮明晃晃的月亮,挂在天边亮的灼目。
是爹爹吗?
他不敢肯定。
花花在他肩头蹦跶,示意包子别发呆了,门外护卫快醒了,时间不多了,我们还有事做啊啊啊啊!
包子醒悟,便跳下天窗,开始认真在库房里搜寻自己想要的东西。
却是搜寻了好几遍,足足找个半个时辰,都不见那活血红莲,徒劳无功。
“莫非被人早一步拿走了?”他低语。
是刚才那人么?
花花在他肩上激动的跳来跳去,愤慨的虫身大扭。
我那牺牲的两咬!我的初咬!包子你还我初咬!
包子皱起了聪秀的眉,走到前方一排武器前,停顿看了一会儿后,低道,“马上去找顾先生。”
说罢将花蛟塞到袖子里,翻身出库,朝天凤阁跑去——天凤阁前,君小宝摘了面罩走进去,向掌柜询顾先生所在房间,不料掌柜却道,顾先生一直在大堂候至二更半,仍没等到该等的人,如今去到灵通寺里接人去了,至少也要明天傍晚才能回。
包子走出门,一脸担心与挫败。
她想起娘亲的伤和受伤的臂,勾下头,对花花小声道:“花花,那个方法,可以用么?”
“王爷,您从下午就在书房里绘丹青,天晚了,该歇了。”
管家掀开珠帘,哗然作响中,看到那一身黛色长袍,执笔立在案前的清俊男子,不由再次出声提醒,“明儿个一早,您还要到丞相府去见沈小姐呢,王爷……”
“福伯”,他笔下动作停滞一下,终将笔毫离开宣纸,搁到了笔格之上,转首道,“什么时辰了?”
“快三更了。”
“又是这么晚了。”
他沉吟一声,低低长叹。
那日之后,他就已是夜夜难寐,从前亥时前必当已入寝,却不道现在,竟是时辰越熬越久,越撑越晚。
拿起案几上的茶杯,放在唇中抿了一口,却已是凉透了,突然沁在舌尖里,有种透骨的凉意。
“王爷,我去给您续杯热茶……”福伯见状,忙转身欲去煮茶,被他挡住了,“免了,我这里不用伺候了,你去歇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