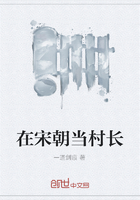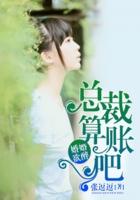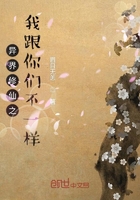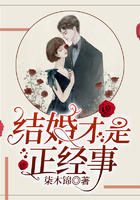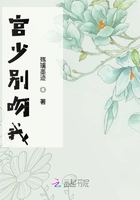[莲宅有译者]
地址:福州鼓楼区莲宅新村
若说晚清与民初的奇人,林纾自是不可不提。他是近代译界泰斗,数十年间翻译了一百八十余部西方小说,约一千二百万字,却偏偏不懂任何外语,全靠他人口述,再将叙述转为文字,实在神奇。
那年去福州,先寻了林觉民故居和严复故居,然后便寻林纾故居。那时我喜欢以字代名,只因觉得“琴南”二字好听,所以逢人就问林琴南故居在哪里,结果无人知道,只好自己找个地方开电脑上网查——那时还没3G 手机,不似如今这般方便——才知他的故居在水部街的莲宅社区。
这莲宅社区当年是城中村,后来改造为莲宅新村,都是颇有些年头的单元住宅楼。村口有一个四角方亭,上有灰瓦,红色柱子支撑,亭名“莲宅”。周围是个小小广场,有石桌石凳、健身器材,边上有大树,绿荫遮盖,显然是村中住户休憩活动的场所。林纾故居就在亭后,长形条石为基,灰白墙身与灰瓦,是典型的清代建筑,在福州极为常见。值得一提的是,正门所挂牌匾上所书的恰恰是我此前屡问而无人知的“琴南书院”四字。
如今的林纾故居已修缮一新并免费开放,不过当年也经了些波折。据说早在1993年莲宅村改造为莲宅新村时,当时的晋安区政府就有意修复林纾故居,于是迁走了故居内外的二十户居民,次年决定将故居辟为纪念馆,产权归区政府所有。1995年对残旧不堪的故居予以修复,继而又征集资料筹备陈列馆,但1996年福州区划调整,林纾故居所在地被划归鼓楼区,与产权相悖,中间各种问题难以解决,一拖就是七年。直到2004年,这事儿才由福州市政府协调解决,2005年初得以开放。
之所以将这资料尽录于文,是因为太多名人故居都曾经历坎坷,即使能抵挡几十年风雨留得原貌,但要想混个招牌,得到保护,彻底免去被拆之虞,也需大量批示、手续、沟通协调……甚至曾有故居就在大家开会研究的当口被拆。
我们其实仍没有学会尊重历史,或者说,我们对历史欠了敬畏之心。人往往有所畏,才会有所谓,进而才会有所为。林纾自号畏庐居士,我不知这“畏”字可有敬畏之意。他在这莲宅中出生,在他的《畏庐文集》里,有《浩然堂记》《畏庐记》和《苍霞精舍后轩记》,分别写故居堂、庐、轩的修造过程,并忆念亲情,也就是著名的“福州三记”。
故居坐西朝东,四进三开间。我去寻访时,正门紧闭,只能从侧门出入,绕到正厅,可见天井与左右厢房。左厢房是林纾出生的房间,目前陈列着他与妻儿的照片,还有书橱、衣橱和床,右厢房和二楼如今是陈列室,展示其生平事迹、主要译著和著作。
最抢眼的自然是林纾1899年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原版书,当年他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即《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如归》等书,风靡海内,使无数国人得以在书中了解西方国家。当时,西方思潮传入正盛,但理论虽好,还需具体呈现,有血有肉,林纾的译著恰恰有这效果。他译书极快,古文功底又深,喜欢用古文译小说,也善于将西方伦理与传统观念相观照,引读者共鸣,比如狄更斯在他笔下就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
我想象中的林纾,或是因为饱读诗书,更七次参加礼部会试的缘故,总是一副老夫子形象。可在展厅里走上一圈,却发现他的侠气,比如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清军惨败,林纾拦截钦差大臣左宗棠的坐骑,当场状告闽省官员谎报军情。袁世凯称帝前,写劝进表者甚多,同乡严复更是晚节不保,误入筹安会,林纾却拒绝顾问衔头,还曾说“将吾头去,吾足不能履中华门”。
又如他曾抚养友人遗下的孤儿多名,一友病故,妻子自缢相殉,林纾破窗将她救出,并将其幼子抚养成人;友人林崧祁(即林述庵)病故,临终将幼子林之夏托付给林纾,林纾不但将之抚养成人,还尽传所学,林之夏后来曾参加辛亥革命,为陆军中将。
除了侠气,还有名士气。不过晚清和民初时,但凡名士气,都伴着官场失意,若是官场得志,谁又得闲纵情山水?林纾曾中举人,但七次上京参加礼部会试,屡试屡败,失意中就断了走仕途的念头,反倒成了名士。名士都爱随缘,林纾的事业也恰恰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年,他的母亲和妻子在短短时间里相继病逝,自不免消沉,几个朋友便邀他一起翻译西方小说,本意是让他有点事情做,权当寄托,谁知作品大大畅销,就此一发不可收。
想来,冥冥中确有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