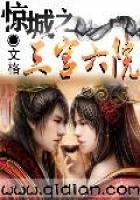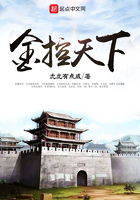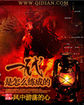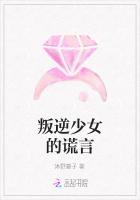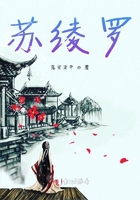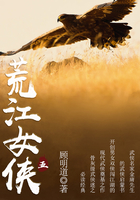[观海上夕阳,书一首《奇迹》]
地址:现中国海洋大学校内
私认为,中国最美的大学是中国海洋大学(原国立山东大学校址所在处)。这所位于半山、早年曾是德国兵营的学校,景致无处不在,各式欧式老楼隐藏于树丛中,大片的樱花、紫薇,还有众多无名小花点缀其间。留着岁月痕迹的墙面上,也总有遮蔽整个墙壁的爬山虎,那是一种深沉的绿。
闻一多故居便在校内,也就是俗称的“一多楼”。1930年6月,闻一多应聘来到国立青岛大学(当时尚未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1932年夏天辞职离青。
当时,住在校内的教师并不多,大家多绕校园而居,如梁实秋住在学校正门口的鱼山路上,两任校长杨振声和赵太侔分别居于左近的黄县路和龙江路,洪深和沈从文等居于学校后门不远的福山路……闻一多也曾暂居于校外,但在青岛的两年中,有一年时光居于校内这栋二层小楼。
年少时虽热衷整天背着书包闲逛,也常去海大操场看学生踢球,但却从未去过一多楼。上次回青时才头回寻访,却因不爱问路,遍寻不获,闷闷不乐出了校门,走到红岛路上。这条路依山而辟,遍布老房子,我沿着学校围墙在法国梧桐下缓行,终是不死心,向路边报摊的老大爷询问,他往后指指,说“围墙后面就是”。
这怕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了吧,我二话不说,返回校内,拐个弯便来到故居前。这是一栋红瓦黄墙的小楼,墙面斑驳,后来曾看过夏日一多楼的照片,发现那才是它最美的时候,几乎整个墙面都被爬山虎所覆盖。
当年,闻一多住在楼上,后来,楼下还曾住过国学大师游国恩。
1950年,山东大学将这栋楼命名为“一多楼”,1984年,当时的青岛海洋大学又在楼前建了广场,立碑塑雕像,碑文由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撰写。据说,那花岗岩雕像还曾获得不少大奖,可我对这类雕塑始终无感,整齐的广场也显得俗套,至于臧克家的碑文,有太多意识形态的痕迹,行文也刻板俗套,为我不喜,甚至认为这广场与雕像都打破了故居的宁静。
只是,如今的故居也不算宁静。开辟展室倒属寻常,但成了“王蒙文学研究所”所在地,在我看来便有些突兀——虽然王蒙也曾在此住过,但那种恨不得把所有名人一起贴在身上的求大求全做派,实在与故居那遗世而独立的气质不符。
后人一般认为,闻一多在青岛完成了由诗人到学者的转变。他早年是新月派主力,到青岛后专攻学术,如《杜少陵年谱会笺》《离骚解诂》《诗经新义》等,便是闻一多在青岛时所著。
他的诗人身份在青岛作结。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有《红烛》《死水》两部诗集问世,其后本已歇笔,却在1930年客居青岛后,写出一首被徐志摩称为“奇迹”的《奇迹》。这是他在青岛的唯一诗作,也被誉为他作为诗人的最高峰;“只要奇迹露一面,我马上就抛弃平凡。我不瞅着一张霜叶梦想春花的艳,再不浪费这灵魂的膂力,剥开顽石,来求白玉的温润,给我一个奇迹……”
这首诗便写于一多楼上。旧时,楼前广场该是一段小径,总有小花盛放。闻一多会与挚友梁实秋比肩而行,两人各“携手杖一根”,高谈阔论。
闻一多写青岛,只有一篇散文——据说这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写景抒情散文。他写青岛海上夕阳,说“西边浮起几道鲜丽耀眼的光,去别处你永远看不见的”。他也写青岛遍布的樱花,“公园里先是迎春花和连翘,成篱的雪柳,还有好像白亮灯的玉兰,软风一吹来就憩了。四月中旬,奇丽的日本樱花开得像天河,十里长的两行樱花,蜿蜒在山道上,你在树下走,一举首只见樱花绣成的云天”。
与他一起观日落的,自然少不了梁实秋。梁实秋曾回忆说,闻一多总在海畔夜诵安诺德的诗,那时他已开始用西方文学理论解读中国古诗。
如今,海上依旧会有绝美的夕阳,小楼依旧静立,即使故人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