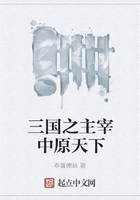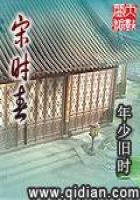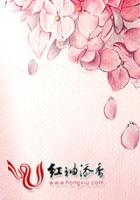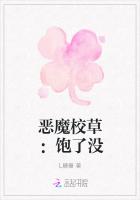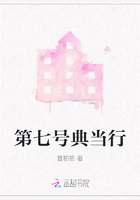[名士风采总在记忆中若隐若现]
地址:青岛黄县路7号
说起青岛的历史,1891年建置,历史极短,文化与古迹自然也乏善可陈。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个新兴城市却一举成为文化重镇,又俨然世外桃源,众多作家、学者客居于此,一部部传世之作也在此诞生。
这虽短促却绚烂,至今仍令后人怀想的光辉,与国立青岛大学(后更名国立山东大学)息息相关,也与首任校长杨振声分不开。
杨振声的一生以“五四”为界,此前青春激昂,此后春风化雨。
在学生时代,他是新潮社创始人之一,也是五四闯将,与傅斯年、罗家伦等并肩。留学归国后,他投身教育,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1930年出任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
据载,初建校时的国立青岛大学,一年经费仅40余万元,是同级院校的1/3甚至1/4,杨振声便在行政编制上尽量缩减,全力投入基础建设。他曾说“在行政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虚耗;在基础上多花一文,这一文便是建设”,并以身作则,连公家的信封信纸也绝不私用。为节省开支,他还把校长住宅让给了普通教师,自掏腰包租住黄县路7号。
黄县路是一条石板路,悠然清静,呈缎带状,曲线迷人,两侧都是独立庭院。年少时我常常在此经过,那时,总能见到午后阳光打在石板路上,两侧院落里的老人坐在小凳子上聊天,却不知时光就此流过,更不知在许多年前,这里和周边的几条街道曾经承载了一群人的教育救国之梦。
黄县路7号并不太起眼,半椭圆形的外部结构,花岗岩墙面与红瓦相接,二楼的环形阳台加了窗子,成为了住宅的一部分。当年,这里常高朋满座,任教于国立青岛大学的学者们喜欢来这里谈诗论道,杨振声总是热情接待。
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秉承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加上杨振声名气大人脉广,为人又坦荡豁达,竟延揽大量名家,建校之初便有“豪华阵容”,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是闻一多,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是梁实秋,教育学院院长是大教育家黄敬思,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是数学家黄际遇……梁实秋和闻一多的到来颇有意思,杨振声用的是“体验式营销法”。他亲自前往上海拜访二人,表示“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决不勉强”,结果二人来青岛待了两天,便沉迷此城,签下聘书,梁实秋晚年思念大陆,最念念不忘的地方仍是青岛。
也正因为杨振声的个人魅力,虽然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师待遇稍低于同类院校,但大家仍愿俯就。
当时,国立青岛大学还有“酒中八仙”,杨振声亲自带头,另有赵太侔、闻一多和梁实秋等。此举其实也是用心良苦,因为青岛虽景致迷人,但开埠未久,人文气息不够,文化人在此久居,难免觉得单调,四处饮酒谈诗,也算一种调剂。梁实秋晚年的文字对这段时光提及甚多,他在《酒中八仙》里回忆杨振声,“今甫身裁(材)修伟,不愧为山东大汉,而言谈举止蕴藉风流,居恒一袭长衫,手携竹杖,意态潇然。鉴赏字画,清谈亹亹。但是一杯在手则意气风发,尤嗜拇战,入席之后往往率先打通关一道,音容并茂,咄咄逼人”,一派名士风范,跃然纸上。
好玩的是,酒中八仙的彪悍酒风还曾吓怕著名“妻管严”胡适。胡适与杨振声堪称半生知己,1931年春,胡适应杨振声之邀赴青演讲,不料风浪太大,轮船无法靠岸,他便给杨振声发电报,仅“宛在水中央”五字,杨振声则回电“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前者化用《诗经》,后者引古乐府,一时传为美谈,还被人发表在《大公报》上。到青岛后,胡适见酒中八仙划拳斗酒,赶紧出动私家武器——戴上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要求不参战。更好玩的是,回到北京后,胡适还写信给梁实秋,表示你们喝酒太凶,青岛不宜久居,还是来北京吧,公然挖老友墙角。
如今,在原国立青岛大学正门所在的鱼山路与杨振声故居所在的黄县路之间,修起了一座矮矮的立交,以减轻因道路过窄带来的交通压力,看起来有些煞风景。而在七十多年前,每日经过这里的杨振声想必是悠然的,不远处的海浪声伴随着他的脚步,手杖触碰石板路的声音想来也清脆。
也许就是在这海浪声中,杨振声动了一个影响中国科学史的念头:在他看来,青岛的气候和地理位置都极适宜海洋学研究,故首创海洋科学学科。此后,国立青岛大学(后易名国立山东大学)的海洋学科始终是国内第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山东大学搬至济南,但却在其原有基础上创办了青岛海洋大学(今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青岛就此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杨振声还有一个创举,他于1932年将文学院和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此举得教育部称许,蔡元培亦对此赞不绝口。合并的用意是让文科生必修某些理科课程,理科生也必修一些文科课程,杨振声认为“文学院的学问、方法上是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文学院中的人,思想上越接近科学越好;理学院中的人,做人上也越接近文学越好……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这等见识直到今天仍不落伍,断然割裂文理,会极大影响学生的学习能力,文科生缺了逻辑思维,理科生则往往墨守成规,也缺少人文气质,杨振声显然清晰地看到了这一点。
可惜的是,1932年5月,杨振声便离开了青岛。当时,学生为敦促政府抗日,前往南京示威,引起当局不满。杨振声一方面坚持教育独立,保护学生安全,另一方面却也希望学生克制,专注学业。作为当年的“五四”闯将,他的隐忍令很多人不解,但实际上,这是许多经历过五四的知识分子的共同选择。结果,当局怪他包庇学生,学生怪他支持太少,加上人事关系纷杂,他被迫辞职,梁实秋为此曾感叹杨振声“彬彬君子,不善勾心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