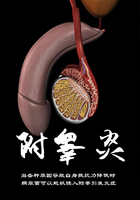“来吧!人家问了你好几遍了,说想见识一下‘藏漂’的名花是什么样子。”
“一朵凋谢的花有什么好看的。”我说。
“这么贬低自己?是不是失恋了?被藏獒抛弃了?”默默嘿嘿地笑。藏獒是“藏漂”们给嘉措取的名字,说他又黑又壮像藏獒。
默默不等我说话,便又喊着来吧来吧,这哥们可帅了,你要不来,我们今晚就得自己买单,你知道我们是穷人,这儿的柠檬酒好贵的。
想了想,这样窝在家里也是一夜流泪,出去狂欢也许能好过些吧?便说好吧,我一会儿就到。
起身化妆,换了一件黑色低胸的薄绸衣,什么首饰都没戴,套了件风衣就出了门。
酒吧里灯光暧昧,很吵,男人女人如喊一样说话。
默默他们看到我,吹着口哨站了起来。阿能和狼人、沙子、海鱼一一跟我拥抱。
介绍一下,益西江村,这儿的歌唱家。默默指着长发帅哥说。
你好。我说,对益西江村点点头,然后脱了风衣,拂开遮脸的卷发。
益西江村眼神一亮,接过我的风衣和包放在身后,然后叫过服务员,说来两罐柠檬酒。
服务员不一会儿就送来两只精美的陶罐。
益西江村说尝尝,柠檬酒是我们这儿的特色。便给我倒了一杯。
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怪怪的味道。皱了皱眉,给自己再倒了一杯。此时的我,很需要酒精的麻醉,混混沌沌的,让这世界都迷糊成一片才好。
对面的海鱼醉眼迷离地看着我,口齿不清地问,你的藏獒呢?你的小天使呢?
我头也不抬地说死了。心里又马上骂自己神经,为什么要咒天天?对不起佛祖,我说错了,天天好好的,嘉措死了。
“你失恋了?”黑衣红裙的默默提了瓶啤酒,斜着眼睛看我。
“好像你很高兴?”我说,白了她一眼,再灌了口酒。
“完了完了,姐妹们,看好我们的男人,这妖精一失恋,就注定有女人要倒霉了。”
“为什么是女人而不是男人?”沙子好奇地问。
“女人哭哭啼啼地找不到男人了啊,因为男人都上了她的床。”
“切。”我抓起一把爆米花砸过去,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狗嘴里吐出象牙的那不是狗,是妖怪。”默默哈哈大笑,脱掉小外套,里面仅穿一小背心,几千公里骑出来的小蛮腰引得周围的男士都往这里看。
来两个小罐,咱们玩“六一”。海鱼也脱了外套,里面一件大红的毛背心,醉胸微露、惺眼半醉。
我们这几个女人,说实在的,无论是外貌还是才华,都不比大街上任何一个女人差。默默行走各地,常在各大杂志上看到她的大名。海鱼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语,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当翻译,沙子正在准备考研。这些女人,只要不碰感情,在各自领域里都可以摆个主子的谱。今天拉萨的生活,不过是大家放松情绪的一种方式而已。彼时回到都市,照样签合同下订单,人五人六的受人尊敬。
我和海鱼各自拿了个色子罐摇得“哗哗”响,打开后把六拿给对方。很简单的一种游戏,适合我们这些不动脑子的人玩,赢了的喝酒。十局下来,我已经半醉。看到益西江村在抽烟,吐了好看的烟圈,便一把抓过放在自己嘴上。
我不抽烟,但我不拒绝把烟作为道具来表演情绪。此时的我,就像一只燃烧后的烟,亮丽过后只剩颓废。
灯光突然暗了下来,益西江村说他要上场了,把外套披到我肩上,说等我回来陪你喝。
“你会贝司吗?”我突然问。
“会,学校里学的。”
“会《深夜》吗?”
“会。”
“我唱,你伴奏。”我说,站了起来,拿掉外套,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下,拖了他的手往舞台走去。
默默他们鼓着掌敲着杯子。
到了台上,我坐在高椅上,益西江村接过贝司站在我身边,对着话筒说我俩今晚为大家演唱一首老歌《深夜》,献给有情的、无情的、恋爱的、失恋的人。听之前我希望你们先举起手中的酒杯,尝一口我们这儿柠檬酒的味道,是不是跟恋爱的味道一样?
然后,他把话筒递给我,我点了点头,揉了揉巨疼的太阳穴。
随着清脆的金丝弦音响起,我唱起那首古老的歌。
一杯接一杯的酒啊
入口的甜回味却像消毒水
今夜 只想求醉
抱着陌生人压抑地哭泣
低声诉说心中的委屈
从来说不出口的话 因为不熟悉
如那滔滔的江水决了堤
如果我没醉 明天都会如昨天一样继续
如果我没醉 我仍会天天天天混日子忘了自己
爱了就该承受 跟了就该无悔
上天啊 如果给我来世
请让我无爱地过一辈子
反反复复地唱着,歌声如泣如诉。超的脸、明的脸、浩的脸、卓一航的脸、嘉措的脸、甚至水儿的脸、天天的脸、莲的脸、卓嘎的脸……一一在眼前晃过。这些人,在我生命里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或让我笑或让我哭,让我欢乐也让我悲伤,如果真能重来一遍,我宁可选择不要,谁也不认识谁,谁也不需要谁。有爱的日子,欢乐是极其短暂的,后来那些长长的黑夜啊,以泪洗面痛入骨髓。
十天,比我过去所有的痛加起来都还要深。
睁眼想起的是天天,闭眼想起的还是天天,那个可爱的小男孩已经在我的生命里了,再也丢不下、再也忘不了。
卓嘎,你为什么抢走了我的男人还要抢走我的孩子?给我留一个就委屈你了吗?剥夺我的所有你就真的那么快乐?
醉兮兮地去了莲的家,保姆说他们找一航去了。
于是又去了卓一航的家。我只想找莲,告诉她我心里的委屈。
进门却看到天天的笑脸,情不自禁地直奔天天而去。心里有一万个声音大叫着,天天,我的孩子啊,你知道妈妈有多想你吗?眼泪不听话地流了下来。只记得天天看到我有些畏缩,直往那个女人身后躲。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天天,她没来的时候,你是多么黏人的小家伙啊,天天黏在我身边,晚上还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你说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阿姨,你好喜欢我,将来长大了要跟我去内地上学的,天天,这些你都忘记了吗?
看到天天害怕的眼神和那个女人的笑脸,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我想要回天天,他是我生的,凭什么要叫别人阿妈而叫我阿姨?凭什么她享受天伦之乐却让我承担思子的痛苦?我疯了一样拉着天天大叫大嚷,天天也大声哭着。然后,那个女人打了我一耳光。
第二天醒来时额上贴着毛巾,莲坐在床边担忧地看着我。
“明知要来的,为什么就想不通呢?”她说。
“莲,我后悔了,我想要回天天。”我说,泪水潸然而下。
“水儿呢?她怎么办?”莲说。
“我找不到她,我找不到她啊!”
“所以你就想要回天天?”
“他也是我的孩子啊!莲,这些日子他天天跟我在一起,我教他学英语教他写作业,我放不下他了啊!”
“你想过卓嘎吗?他视天天为生命。”莲说,一点也不吃惊地看着我。虽然我以前没有说过,不过以莲的聪明,她大概早就猜到了吧!
“她老家不是还有两个孩子吗?她不是还有那么多男人吗?我什么都没有啊!”
“好好,你还是这么主观。我说过,卓嘎的婚姻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她的痛苦不比你少。”
“再怎么着她也比我好。莲,你帮我劝劝她,让她把天天还给我。她不是一向听你的话吗?你帮帮我好不好?”我拉着莲的手,像一个迷途的孩子般无助。
莲搂着我的肩,轻轻抚拍着说:“好好,先冷静下来再说好吗?你昨晚那么一闹,卓嘎那儿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我今天要去看看她。你知道卓嘎的性格,我怕她一旦知道天天的身世,家里还不天翻地覆啊!”
我低了头,不敢看莲的眼睛。
“先什么都别想,冷静下来再说。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哪里像个女人啊?简直就是个疯婆子。”
“你才是个疯婆子。”我啐了她一口,缩进了被子里。
“会骂人了,就表示恢复正常了。”莲说,“给我倒了杯水放在柜上,说我走了,你先睡会儿,醒来后打电话给我。”
莲走后,我对着天花板流泪,想嘉措。此时的我,是多么需要他的支撑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就无影无踪了呢?难道他也跟卓嘎一起,合伙设计抢走了我的天天吗?掏出电话,试着拨了他的号码,响了五声没人接。挂了不一会儿就接到他的短信:燕子,对不起,我在陪阿爸看病。
我回说,陪阿爸看病就不能接我的电话吗?
他说不是,她也在。
这一个“她”再次把我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人家为了顾及她的感受,连电话都不接我的,我还在这儿傻乎乎地盼什么啊?所有的付出所有的牺牲,不过是为那个男人增添一份骗取女人感情的经验而已。还有那个放羊女卓嘎,看着像阳光般灿烂,实则呢,自私自利恨不得一个人独占了世界所有的好。我给她孩子让她享受做母亲的快乐,她又怎么对我的?一记响亮的耳光,现在脸颊还红肿着呢。
一个念头疯狂地滋生出来:对我好我会记得,对我不好我也会记得,并让你加倍偿还。
我坐起来,开始收拾东西,把不需要的打包找货运公司寄走,然后拿了天天的两寸照片去派出所开了乘机证明。回来写了封信,想了想,把天天所有的照片放进去,退房时交给房东,说我要回内地,过两天有朋友来找我,请她把这封信交给一个叫莲的女人。
带走天天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卓嘎没来拉萨之前一直是我在接他还去给他开过几次家长会,跟他的老师很熟了。我只说他家里出了点事要马上接他回去,老师就会让他跟我走了。
带了天天出来打车直奔机场。
还不懂事的天天只是好奇地问我:“好好阿姨,阿爸他们在哪儿啊?”
“在很远的地方,我们现在去找他。”我说,然后把事先准备好的玩具车递给他,转移开了他的注意力。
一切都很顺利,到北京下机才五点半。此时,他们大概已知道我带走了天天吧?想象着卓嘎此时的样子,不禁冷笑一声。你不是魔女吗?你不是仗着自己野蛮敢打人吗?好啊,去死吧你!孩子现在是我的了,你再也休想见到他。
因为我和公公的到来,嘉措按时回来吃饭,天天按时上学放学。朗结和蓉也会来,还有莲和洛桑,一航和央金,家里经常一大堆人,大家嘻嘻哈哈地打闹着,要我唱歌,要蓉跳舞,要莲表演瑜伽……晚上大家轮流下厨做饭。公公总是很高兴地看着我们,说多做点,吃不了下顿再吃。我定时打电话给扎西,把拉萨的情况说给他,让他放心,我过些日子就会回去的。抽时间我们还去德仲寺看了宇琼。离开时宇琼送我们到大门外,回头时看宇琼站在一棵歪脖子的古柳下,一只胳膊裸露着,手腕上缠着一串黑色的佛珠,表情沉静,风鼓动着绛色的僧衣向后扬,身后是寺庙金碧辉煌的顶。
宇琼,好像他天生就属于这里。
“世间的事啊,什么时候有个定数?今天你来了,明天他走了,总是这么不停地变幻着。”莲回头对宇琼按了一下快门,然后把相机挂在他男人的脖子上,感叹地说。
洛桑笑了一下,握了她的手,在莲耳边轻声说了句什么,便见莲绯红了脸,目光温柔得就要滴出水来。
山道上,一航阿哥走在前面,央金提着他的包和三角架跟在身边。央金是个活泼开朗的姑娘,爱唱爱笑也很能干,有些像未嫁时的我。只不过央金比我幸运,她碰到了一航阿哥,这个温柔体贴的男人,把爱情看得至高无上。他俩,真像是佛祖故意安排好的一样。一航单身多年,就像在等着央金。央金呢,就像是给一航量身定做的一样。
蓉和朗结才办了结婚手续,最近在忙着看房。蓉的舞蹈班越办越大,有了身孕后就不再上课,另外请了老师,朗结也不开车了,而是帮着蓉管理舞蹈班的事务,还学会了做菜,照顾老婆。
我和嘉措走在最后,一人一边牵了天天的手。这样跟他走在山道上的感觉真的很好。在我印象中,阿爸阿妈牵了我的手去拜佛,那是最幸福的时刻。从来没问过他和好好的事,不是我大度,而是这样的事在我们的习惯里根本就不算个事。这段时间他一直陪着我,给我买首饰、买衣服、买鞋子,周末就带我和天天去寺里。
家长还是我的家长,儿子还是我的儿子,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