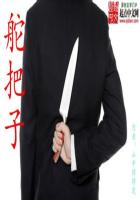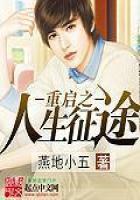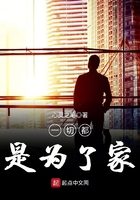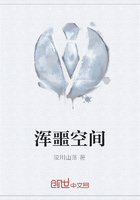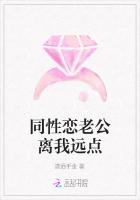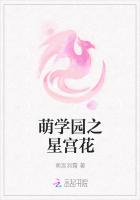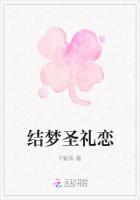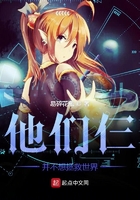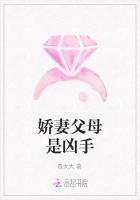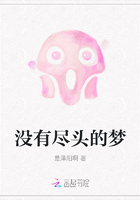我认为,这才是研究《红楼梦》的根本要旨!
上文曾向大家提出了“‘时飞’二字必指贾雨村”的论点。理由是在前
八十回中只出现过两次的“时飞”二字,在同回文字中相隔仅一步之遥,这一定是作者的刻意安排。
可以设想,一本写了十年的传世名著,以曹雪芹的旷世奇学(怎么夸
他都不过分),我们可以肯定,他自创的原文绝不可能有太大的疏漏。如果出现了文字上的疏漏,那其中一定另有隐情,这也就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条蹊径——“抓漏法”。
利用这一方法,我终于又捉到了一条大鱼!
书中第五回有一段文字:“当下随了仙姑进入二层门内,至两边配殿,
皆有匾额对联,一时看不尽许多,惟见有几处写的是‘痴情司’‘结怨司’‘朝
啼司’‘夜怨司’‘春感司’‘秋悲司’。”甲戌本侧批:“虚陪六个。”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怎么“怨”字会出现两回呢?这样岂不重复了
吗?如果不是作者刻意安排,这段文字就一定有问题。洪昇《长生殿》第十八出就是“夜怨”,借用他人文字?这恐怕不是曹雪芹的风格!
果然,在查阅了现存包含此段文字的所有九种不同底本之后,按照甲
戌本的文字,才发现“夜怨司”应当是“夜哭司”。其余八种底本,除梦稿本增加了“夜梦司”(不仅又重复了“夜”字,还变成了七个司,与脂批“虚陪六个”更加不符)之外,只有甲辰本把“夜怨司”改为了“暮哭司”(擅改),其他各本都是“夜怨司”。由于各本都晚于甲戌本,当然只有甲戌本中的“夜哭司”才是作者的原文(这些古抄本,甲戌本最早,文字最接近作者的原文)。《红楼梦》全书,根本找不到“夜怨”的影子,“夜哭”却出现了至少四回:1.第一回:“夫妻二人,半世只生此女,一旦失落,岂不思想,因此昼夜啼哭,几乎不曾寻死。”2.第三十四回:“宝钗满心委屈气忿,待要
怎样,又怕他母亲不安,少不得含泪别了母亲,各自回来,到房里整哭了一夜。”3.第六十一回:“五儿心内又气又委屈,竟无处可诉;且本来怯弱有病,这一夜思茶无茶,思水无水,思睡无衾枕,呜呜咽咽直哭了一夜。”4.第六十二回:“彩云赌气一顿包起来,乘人不见时,来至园中,都撇在河内,顺水沉的沉漂的漂了。自己气的夜间在被内暗哭。”
甲戌本的抄手先将“哭”字写错,后又依错字改回(详见影印本),使得后来的抄手辨认不清,从而造成了“怨”字重复出现的“夜怨司”的漏笔。假如曹公在九泉之下看到后人如此擅改他呕心沥血十载才写成的文字,岂不真正大“哭”焉?
就连以细微出名的巨匠——红学前辈邓遂夫也难逃此劫。纵观各种
校订脂本,恐怕只有蔡义江的校本改回了“夜哭司”。所以,周汝昌才称蔡义江的校本为“到目前为止,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本子”。
因此,这个“夜哭司”在版本上的价值极大。甲戌本在“夜哭”二字旁有一朱批:“虚陪六个字。”庚辰本、梦稿本、乙卯本、甲辰本、舒序本、卞藏本皆无,显示了此回底本的同源(甲戌修订稿),而王府本、戚序本则在“秋悲司”后面分两行叠印了“虚陪六个”四字,显示了这两个古本的同源(立松轩本)。尤其是戚序本在此页上方有非常清晰的批语:“朝啼、夜怨、春感、秋悲四司列名皆各有意义,今本改夜怨为暮哭,哭与啼合掌不如原本远甚。”我们可据此得出以下结论:1.批语所称“今本”为甲辰本(今本改夜怨为暮哭)。2.戚序本过录时已有甲辰本的原抄本,甲辰本由原抄本校改而成,甲辰本原抄本与戚序本为同一时期的抄本(今本改夜怨为暮哭)。
3.戚序本过录原本时曾参照甲辰本原抄本。4.戚序本过录的原本并非甲戌本(因“不如原本远甚”,而原本为“夜怨”,也抄错了,非甲戊本)。5.卞藏本的过录者曾擅改原文,各本中唯独卞藏本把“秋悲司”擅改为“秋愁司”,
“悲”与“愁”二字差别很大,应该是改动的,并非抄错了。
以上结论有力地支持了郑庆山关于立松轩本的考证,也支持了他关于
甲辰本的“原抄本即当抄于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 年)之前,今本为甲辰本原抄本的过录本”的结论。
其实,我们的收获还不止如此。经过仔细研究,这十二个字居然生动
地概括了金陵十二钗的性格命运,“痴情”“结怨”“朝啼”“夜哭”“春感”
“秋悲”这十二个字正如戚序本批语所言:“列名皆各有意义”。加上薄命司的“薄命”二字,恰好构成了十四个字的七言对联:“痴情结怨朝啼夜”(前七字),后七字“哭春感秋悲薄命”反过来是“命薄悲秋感春哭”。合起来便是:
“痴情结怨朝啼夜,命薄悲秋感春哭。”
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哟,曹公真乃神人也!
其中的“情”字自然是说秦可卿,第二十九回“痴情女情重愈斟情”指
黛玉,所以“痴情”是指黛玉和秦可卿(同属五情,详见拙文《“十二钗”的灵感源》)。
“桃李春风结子完”与“上结着长生果”两句判词,显示了李纨与惜春
和“结”字的关联,我在文章《“十二钗”的灵感源》)中分析出了四怨:惜春、巧姐、妙玉、李纨。“结怨”自然是喻李纨与惜春。而“哭”字由于有“哭向金陵事更哀”也自然是说王熙凤,上文曾述十二钗中只有宝钗有“夜哭”(“整哭了一夜”)的情节。第三十七回又有“蘅芜苑夜拟菊花题”,“夜哭”必然是指宝钗和凤姐。
第七十三回:“迎春劝止不住,自拿了《太上感应篇》来看。”后来又
写:“当下迎春只和宝钗阅《感应篇》故事。”这些文字当然是作者对“春感”的照应。而妙玉判词中的“红粉朱楼春色阑”,也分明就是“春感”的写照。因此,“春感”是指向了迎春和妙玉。
史湘云的判词《乐中悲》中有“这是尘寰中消长数应当,何必枉悲伤”,而探春居住在秋爽斋。因此,“秋悲”无疑是喻湘云和探春。
这样,剩下的“朝啼”就只能对应剩下的元春和巧姐了,“朝”字暗喻
元春之贵,“啼”字暗喻巧姐之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