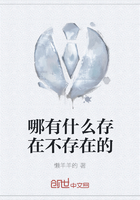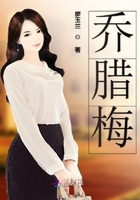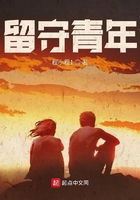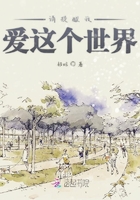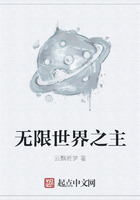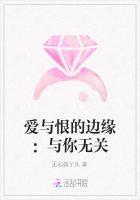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即事诗”和“省亲诗”之中所隐藏的秘密。且认为书中所有的诗都与故事情节或者人物关系有某种关联,大部分
的诗歌都是十二钗的判词,其中或多或少隐藏着她们的命运结局。要想最大限度地推测出后三十回佚文的情节,必须把它们隐藏的线索全部挖掘出来。下面介绍我关于“海棠诗”“螃蟹诗”以及“五美吟”的理解。
第三十七回是全书的三等分点,这一回写到红楼众人物海棠结社,开始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建社后第一天所作的咏白海棠诗共有四首,分别为
探春、宝钗、宝玉和黛玉所写。我们先来看一看宝钗的诗:
咏白海棠·宝钗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
胭脂洗出秋阶影,冰雪招来露砌魂。
淡极始知花更艳,愁多焉得玉无痕。
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
蒙本在首句后面有一条双行夹批“宝钗诗全是自写身份,讽刺时事。只以品行为先,才技为末。……最恨近日小说中一百美人诗词语气只得一
个艳稿”,说明批书者认为这是宝钗对自己的吟咏。我要说,批者又被作者的烟云模糊文字所蒙蔽了,这首诗显然不是咏宝钗,而是寓探春。
“珍重芳姿昼掩门,自携手瓮灌苔盆”,用于宝钗尚可勉强,但“胭脂洗出秋阶影”中的“秋”字,明显是在说探春住的秋爽斋,而不是宝钗所住的蘅芜苑。其中的“洗”字与探春深谙书法有大关联(洗笔),与宝钗却无丝毫联系。“冰雪招来露砌魂”中的“招来”显然是说突然而来的大事,“淡极始知花更艳”中的“花更艳”则表明了这件大事与人的身份提升有关。“愁多焉得玉无痕”中“愁多”也不能用于形容宝钗,而形容探春的庶出却恰如其分。最明显的是最后:“欲偿白帝凭清洁,不语婷婷日又昏”。其中的“欲偿白帝”点出了后三十回探春远嫁成妃的情节,再也无法与宝钗联系起来。“不语婷婷日又昏”还道出了探春的婚姻也是悲剧,“不语”和“日又昏”隐喻着她的薄命。
如此看来,诗的隐喻人物与诗作者不同,这是作者保持的一贯作风
(烟云手法)。那么宝玉的诗又是寓谁呢?
咏白海棠·宝玉
秋容浅淡映重门,七节攒成雪满盆。
出浴太真冰作影,捧心西子玉为魂。
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
独倚画栏如有意,清砧怨笛送黄昏。
书中第三回形容黛玉相貌时有“病如西子胜三分”一句,这是全书唯一一回以西子比喻人物的文字。所以,“捧心西子玉为魂”肯定是在说黛玉。“晓风不散愁千点,宿雨还添泪一痕”,是说她的还泪情节。庚辰本这句后面有一条双行夹批“妙在终不忘黛玉”,这次批书者的理解是对的。“独倚画栏如有意”中的“倚画栏”再次与第十八回“怡红快绿”的“凭栏垂绛袖”和第七十回黛玉“桃花行”中“斜日栏杆人自凭。凭栏人向东风泣”的诗句遥相呼应。“清砧怨笛送黄昏”,正合了黛玉与湘云在第七十六回“夜静月明,且笛声悲怨”的联诗情节。其中的“送黄昏”三个字,暗示了她的还泪命运行将结束(回归天界)。黛玉写的诗是咏湘云。
咏白海棠·黛玉
半卷湘帘半掩门,碾冰为土玉为盆。
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
月窟仙人缝缟袂,秋闺怨女拭啼痕。
娇羞默默同谁诉,倦倚西风夜已昏。
首句一个“湘”字便点出了她的名字,“偷来”和“借得”是意义较为活
泼的文字,恰好用来形容湘云的灵动性格。“缝缟袂”正合了她的针线活计。
第三十二回有袭人托湘云为宝玉做鞋的情节,还有这样的文字:“我近来看着云丫头神情,再风里言风里语的听起来,那云丫头在家里竟一点儿作不得主。他们家嫌费用大,竟不用那些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多是他们娘儿们动手。”这段话既合了“缝缟袂”,还表明了湘云在叔叔家的处境并不好,正合了“秋闺怨女拭啼痕”一句。末句中的“同谁诉”和“夜已昏”应当是指她的新婚不久即丧偶的命运。
探春的诗是咏宝钗。
咏白海棠·探春
斜阳寒草带重门,苔翠盈铺雨后盆。
玉是精神难比洁,雪为肌骨易销魂。
芳心一点娇无力,倩影三更月有痕。
莫谓缟仙能羽化,多情伴我咏黄昏。
“重门”寓宝钗的显赫家世,“玉是精神”寓宝钗与宝玉的金玉之缘,
“难比洁”和“雪为肌骨”寓宝钗的相貌,正合第二十八回关于宝钗“宝玉
在旁看着雪白一段酥臂”的描写。末句“多情伴我”隐宝钗与宝玉的婚姻。
这一回中,还有湘云写的两首海棠诗。庚辰本诗末有双行夹批:“二首真可压卷。诗是好诗,文是奇奇怪怪之文,总令人想不到忽有二首来压
卷。”显然批书者也觉得这两首诗很奇特,却不明白它们在书中的作用。
其一
神仙昨日降都门,种得蓝田玉一盆。
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
秋阴捧出何方雪,雨渍添来隔宿痕。
却喜诗人吟不倦,岂令寂寞度朝昏。
其二
蘅芷阶通萝薜门,也宜墙角也宜盆。
花因喜洁难寻偶,人为悲秋易断魂。
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
幽情欲向嫦娥诉,无奈虚廊夜色昏。
第一首的“何方雪”似寓宝钗,而“隔宿痕”和“寂寞度朝昏”又似在寓黛玉。当我们对这两首诗进行细致的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她们是
专门隐喻黛玉和宝钗的。在书中的作用是为第四十五回的黛钗合一作铺
垫。其中,第二首诗的意指最为明显,“蘅芷阶通萝薜门”肯定是寓宝钗,而“玉烛滴干风里泪,晶帘隔破月中痕”则一定是寓黛玉。这句诗是与第七十回黛玉“桃花行”中“寂寞帘栊空月痕”一句,相互照应的文笔。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第一首诗中“偏爱冷”是指宝钗(冷香丸),“离魂”指黛玉(合《牡丹亭》之回目)。第二首的“花因喜洁难寻偶”,指宝钗在第四回“待选”(宫廷选秀)未成的情节,“人为悲秋易断魂”则是第四十五回黛玉所写“秋窗风雨夕”的伏笔。由此可见,作者写这两首诗的真正意图在于为黛钗合一埋设伏笔。这样就产生了疑问:难道作者在此回中仅仅以四首海棠诗来分别隐喻四钗吗?
后来我终于在第三十八回又找到了含义特别清晰的三首螃蟹诗,这三
首诗明显是凤姐、妙玉和李纨的判词。
宝玉的螃蟹诗:
持螯更喜桂阴凉,泼醋擂姜兴欲狂。
饕餮王孙应有酒,横行公子却无肠。
脐间积冷馋忘忌,指上沾腥洗尚香。
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
首句“持螯”和“兴欲狂”,寓凤姐在贾府的飞扬跋扈,“泼醋”是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的伏笔。“饕餮王孙”以及“横行公子却无
肠”的寓意指向了凤姐的丈夫贾琏。“积冷”和“馋忘忌”指凤姐的残忍留
下了后患,“指上沾腥洗尚香”也是比喻凤姐为了金钱不择手段。末句“原为世人美口腹,坡仙曾笑一生忙”,与第十八回省亲诗《杏帘在望》中的诗句“何须耕织忙”的含义相同,都是说凤姐判词中的“机关算尽太聪明”,“生前心已碎”,“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讽喻了凤姐虽忙碌一生,却“竹篮打水一场空”的命运结局。
黛玉的螃蟹诗:
铁甲长戈死未忘,堆盘色相喜先尝。
螯封嫩玉双双满,壳凸红脂块块香。
多肉更怜卿八足,助情谁劝我千觞。
对斯佳品酬佳节,桂拂清风菊带霜。
这里的“螯封”“嫩玉”和“佳品”,显然不是普通的泛词,“螯封”和“佳品”意指妙玉身份的高贵。“嫩玉”正合妙玉的名字,以及判词中的“金玉质”和“无瑕白玉”。“壳凸红脂块块香”,反寓在第四十八回和第七十六回出现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暗喻了妙玉的生活原型——脂砚斋(详见关于妙玉的文章)。“更怜卿八足”,是作者对妙玉虽然身份高贵却陷于平庸的感慨,“桂拂清风”,暗喻她的带发修行,“菊带霜”,寓她的薄命。
宝钗的螃蟹诗: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酒未涤腥还用菊,性防积冷定须姜。
于今落釜成何益,月浦空余禾黍香。
“皮里春秋空黑黄”,正是关于李纨“槁木死灰”描写的翻版;“性防积冷”,正合了李纨判词中“如冰水好空相妒”的诗句。最为贴切的是末句“月浦空余禾黍香”,其中的“禾黍香”,正是关于李纨的居住地——稻香村的描写。
这样一来,十二钗中已经有了七位的判词。那么,其余的五位呢?是
不是被作者给遗忘了呢?我们很容易就联想到了第六十四回的“五美吟”,原因很简单,因为恰好剩下了五位金钗。果然,经过分析,“五美吟”正好隐喻了其余的五位金钗。
西施
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
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
这首诗寓巧姐。“空自忆儿家”,自然是描述后三十回巧姐的误落荒村;“东村女”,更点出了这一点;“尚浣纱”隐射她的纺纱。
虞姬
肠断乌骓夜啸风,虞兮幽恨对重瞳。
黥彭甘受他年醢,饮剑何如楚帐中。
这首诗是说迎春。“肠断”和“幽恨”暗喻她痛苦的婚姻,“甘受他年醢”寓她性格的懦弱,“饮剑”我认为是描述她死亡的方式。由于《红楼梦》中作者设计的人物死亡方式都各不相同,因而她的“饮剑”方式不会和尤三姐一样,它应当是被中山狼——孙绍祖酒后误伤的。
明妃
绝艳惊人出汉宫,红颜命薄古今同。
君王纵使轻颜色,予夺权何畀画工?
这首诗是元春的判词。“宫”字寓她的特殊身份,“红颜命薄古今同”
和“君王纵使轻颜色”,暗寓她的命薄和失宠。“夺权”,寓宫中的权力争夺,“畀”字音毕,意为给予,该句暗示了元春死于宫中的权力争夺。
绿珠
瓦砾明珠一例抛,何曾石尉重娇娆。
都缘顽福前生造,更有同归慰寂寥。
这首是说秦可卿。第十三回有文字:“因忽又听得秦氏之丫鬟名唤瑞
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也都称赞。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殓殡,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中之登仙阁。小丫鬟名宝珠者,因见秦氏身无所出,乃甘心愿为义女,誓任摔丧驾灵之任。贾珍喜之不尽,即时传下,从此皆呼宝珠为小姐。那宝珠按未嫁女之丧,在灵前哀哀欲绝”,作者交代得十分明确,秦可卿有名叫瑞珠和宝珠的两个丫鬟,而诗中的绿珠和明珠正是暗喻这两个丫头的名字。“尉”字正合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顽福前生造”,正合了第五回“收尾飞鸟各投林”中关于秦可卿“欲知命短问前生”的判语(详见文章《关于收尾飞鸟各投林》)。末句“更有同归慰寂寥”的意义不仅在于暗示了她的早夭,还透漏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后三十回佚文中有一位和秦可卿死亡方式相同的人(自缢)。她一定与秦可卿具有相对映射关系,既然不是死去的金钏和可人,那就应当是龄官或卍儿(详见文章《关于书末情榜》)。
红拂
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
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
此首诗隐惜春。“雄谈态自殊”,正合了第七十四回“谁知惜春虽然年幼,却天生成一种百折不回的廉介孤独僻性”的文字描写。“美人巨眼识穷途”,则合了她判词中“堪破三春”和“将那三春看破,桃红柳绿待如何?把这韶华打灭,觅那清淡天和”的评语。“尸居”和“羁縻”(意牵制),暗示她最后的结局是身居荒村野店,并失去了自由之身。
到此,十二钗已经会齐,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这十二首诗分别在第三十七回、三十八回、六十四回,作者为何要这样安排?我想这里面有两种可能:一是作者的刻意安排,他试图以此模糊观者的视线。另外还可能是修改文本造成的结果,作者(或其他编撰者)对原有的文字进行了大幅的移动。总之,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关于后三十回佚文的关键线索。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些诗的新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