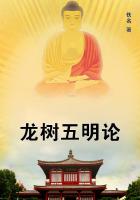皇甫寻轻柔地抚着花晚晴的脸,他脸上的笑容却叫花晚晴更加害怕了,他已将他的真心藏去更深之处,并且铁了心不听她的解释,或是他根本也再不需要她解释了。
“那一天我是见了易名扬,也给他做了汤圆。”花晚晴喃喃,他的手将她下巴抬起又使她在微微的光中清晰地看见了他的表情。一瞬,因提及易名扬,她似看到他眉头一紧。
“很好,这又是你第几次狡辩呢?噢,是做汤圆,那为何是相思汤圆呢?我只记得他信里说过,这可是你们的定情之物呢!”他的手划过她的脸颊,低声说道,危险的气息僵住了她的身体。
“我知道你看了那些信,我也知道你藏了我的信,只是我和他已无相干,至少没有让你介怀的干系。我见他,给他做汤圆是为了他心愿,若是不能再——”
“再爱他?花晚晴,你听好了,”皇甫寻打断花晚晴的絮语,就像是怕听到什么反抢了白,“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即便我看了你的信又如何,我烧了那些又如何,我从来不需要你的谅解,如不能爱上我,你就尝试说服自己认命吧。汤圆我可以不稀罕。但你,就算只是一个物件,既我看上了,就不会轻易让出去,我也不是第一次说明了。更何论是让这物件自作主张的待价而沽呢?”
“我待价而沽?汤圆的事儿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花晚晴叫道,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她的笃定让他愕然,这坚定的模样一时还真叫他以为这并不是她编造的借口。
“怎么又不说了?”他问。
“那碗汤圆……”
他仍不信,看他的表情也猜得出,他仍将她的话视为借口,但她始终要说清的,“那日将汤圆做来,只为要将方法告他,并非你想的那般。可即便我的心已无法予他了,易家仍是我的恩人。恩人所求,我岂能置之不顾?”
他讪笑着将她拉了起身,至始至终听不进她的辩解。
皇甫寻坐回了榻上,又迫花晚晴坐在他的腿上,虽是耐下心听了她的解释,他好似也不曾动怒的模样,但那双曾能让花晚晴望见心底的眼眸中却再找不到真诚的影子。花晚晴并非刻意回避皇甫寻的善意,然而在那日见过他震怒的种种表现,又只当他的手触及她的身体,她便会不由自主的开始颤抖。
她怕他,因他的身份是能将她捧于怀里又能将她轻易捏碎的那种男人。
“一会儿你舅舅会来。”皇甫寻说,鼻中清晰地嗤了一声。
她怕他,她竟能爱慕地望着易名扬,却始终将他置于门外。皇甫寻细长的眼眸半闭着,微微仰头默然苦笑,或天灯,或中秋,都只是花晚晴心中寂寞使然,而她也从也不愿知他的真心,“别这样看我,这并非我好心。全多亏了你外公与我爹的交情,而我实也不忍向家之后就这般委屈的进了我家的门,所以一会儿会由你舅舅接你回府,帮你准备这些事儿。”
花晚晴一惊,身子才是本能向前倾斜,但她逃脱的意图顷刻被他识察,大手用力收紧,圈着她腰仍叫她无法动弹。
“皇甫寻——”她侧首,隐忍的愤怒与委屈使得她满脸通红,他如今只是在做告知的义务,也并不由得她来选择了吧?
皇甫寻一笑置之,铁了心用别的方式来处理这段让他头疼的关系,“如你认为我这样的行为让你厌恶,或是我霸气凌人,那你还是改称我世子大人吧,你唤得也自然些。再者,你和我似也不到直唤姓名的亲密,至少你根本不是这么认为。”
“我说过,那是误会,你不听。如今就算我对你说,即便我已不耻自己的变心仍喜欢了你,你可信我?”皇甫寻的笑让花晚晴心灰意冷,她垂下头,尴尬地也笑了起来,却怎么都笑不出声。
不是她的她不该强求。能抽身时,她为何不尽早离去?对皇甫寻的幻想,让她泥足深陷,舍不得也都成了心痛的悔之不已。
她看着他,咬着唇。他如今并不愉快的笑正冲淡着她的记忆,那记忆中曾有过他毫不保留的笑容,他将那扇门关上了。
“你不会让我走?即便我不是与易名扬在一块儿?”花晚晴哽咽问,思虑许久,她目光中已失了神采。
“该知道这消息的人都已知道,你认为我会让你走么?”每次看到花晚晴沮丧的模样,皇甫寻便极难再对她说出狠心的话,又即便心底恨她不解其意,却不能坦然地伤害她。只是,皇甫寻更不知要如何说服自己,她的心此时就不在他这儿的话,那若是——他还要娶别人,要让她成为他的妾室,她会有多恨他?
他只是不想放手,因而更不得不重新戴上这坏人的面具。
“真是三日后么?”她又问。
花晚晴意外的平静让皇甫寻吃了一惊,听她话中的语气,见她不再挣扎,不骂他也不解释了,反倒才像对他死了心。
他自嘲,她的心他又何曾拥有过。
“皇甫寻。”花晚晴轻唤他的名字,垂下头,“最后一次这样叫你吧。”
胸口如窒,皇甫寻始终不答话,只紧紧地抿着唇。
“如你不是世子,如你我相遇再早些,那该多好?”
话音才落,禁闭的门外有了动静。花晚晴听得出,那是尉迟兰馨的声音,大致也猜出了她今日是为何而来。她忽然抓住皇甫寻的手,在门扉推开时又霎时放开,那片刻的光景却叫皇甫寻心中生出了千头万绪。
她冰冷的手传递了什么,竟能让他一时失神,她彻底起身,带着他从没见过的漠然的表情,乖巧地站在榻边。
对安然接受了他给予的命运的花晚晴,皇甫寻的心中却似乎得不到预期的满足,又直至他从这思绪中回过神,尉迟兰馨已笑着走至他的身旁。他发现,一旦曾有的玩笑与戏弄都成了他无法克制的关怀与在意,那女人便似在他心中扎根,如要生生拔去,他的心怕也不复存在了。
花晚晴放开了他的手,皇甫寻不由看了看,他为何生出了种种的不安呢?
“妹妹,见你还这样完好,我就安心了!”尉迟兰馨调侃着拍了怕皇甫寻的肩,故意挤眉弄眼的她是想让房中气氛更活络。她才入屋没错,但这房中“天寒地冻”的氛围她哪会嗅不出来?
花晚晴依旧冷面,向尉迟兰馨行了丫头才行的礼后便就真像外人般默默地站在角落,不搭话更不对眼。此景倒叫尉迟兰馨颇为尴尬,只觉自己出现的并不是时候。再者,皇甫寻的心思也不在她的身上,她又只得故意扯开话题,悔恨得只想把刚才那句不应景的调侃话重新吞回肚中。
“我在门外见了向大人,他怎么没进屋?”花晚晴看了她一眼,迅速垂下头,尉迟兰馨眉头一怔,忽觉得她竟有些怕跟这样的姑娘交往。
皇甫寻说:“他是侯着来接她回去的。”
房中并无下人,在尉迟兰馨入房前,她也让随行的婢女侯在屋外。但突然,她倒希望房中的人越多越好,“这,这……哎。”尉迟兰馨懊恼地叫了一声,感觉自己陷入了浆糊中,索性将怀中的信函大大方方抽出递给皇甫寻,又自个儿找了张圆凳在皇甫寻身边坐下。
场景似昨日重现,只是此时,倒比那日更让人不愉快了。
“我爹说让你看看,还让我传话,说要你办好了家里的事儿,就赶紧下聘吧。”
尉迟兰馨横了心将话说出,但从不拘小节更从不畏人言的她却不敢往花晚晴处看,像欠了她什么。“还有,哥哥说,如有可能会让爹爹和王爷一同向皇上呈上婚书,这样便也能解了金央国的念想。喂——”
尉迟兰馨闷了声,无奈地又翻了翻白眼。
皇甫寻虽已将信抓紧,但他的目光却只停在花晚晴的脸上。他似有些怅然,因花晚晴面上那份淡然及不动声色,他再无法泰然处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