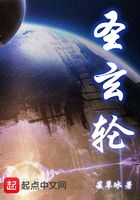越说越激动,竟无法抑制住,捂住口剧烈咳嗽起来。手掌摊开,却是一掌鲜血,如海棠花一般娇冶,鲜艳。
见状,陈大人一颗心提到嗓子眼上不去下不来。这件事非同一般,若七王真有造反之心,那得尽快报于皇上知道。
七王府在大宋根基深厚,先逝的老王爷更有一帮亲随老将的势力仍在朝中,岌岌可危,本就是皇上心腹最大患。
在帐中来回踱着步子,恍忽的心如跳跃的烛火左右摇摆,不知飘向何方。
最终,双手重重抱拳。眉宇紧紧蹙成坚定的决绝。
“韩侍卫,本官立刻派两名精骑护送你回京,禀报皇上。此事事关重大。切记,入了皇宫切莫相信除了皇上之外任何人!”
“未将明白,请大人放心。此言埋在韩尘腹中,若非将我开膛剖肚,否则谁也别想从我这里知晓!”
黑夜的风儿突然狂肆的刮起。半躺在帐内,赵闵觉得阵阵阴冷袭来。他伸手拉过一件衣服披上,不去在乎。
傍惶的心思依然游走在疑惑的边缘。
南王府,那个隐在暗处的人是谁?虽不见其人,但那蜇伏的杀气却比地狱之火更邪佞。狂猛。
半月后,当赵闵与陈大人抵达京城。望着熟悉的城墙,巍峨宫殿。心中百感交集。
踏进大开的宫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怪异的感觉像座牢笼。
“吱!”
正宫门突然紧紧合上了不留一丝丝缝隙,连阳光都被挡在了外头透不进来,将赵闵旗下的将士尽数抵挡在外。
“怎么回事?”
立刻感到不对劲。他迅速转头问陈大人,却见其火速赶向另一旁,如避虎狼一般闪远,与此同时,四面城墙之上站满弓箭手,个个箭已上弦,对准了自已。
此时,对面厉声高喊:“七王赵闵,狼子野心勾结辽贼,岂图谋朝篡位,逆天下之大不违,还不束手就擒!”
远在遥远辽国花香盈盈的南王府,一少女抚摸着手中的白鸽,取下插进脚环里的纸条,看过后,灿烂的笑容展开在她绝美的面容绽放,那么恬静,那么清纯,仿佛世界有她的地方就不会有黑暗。
“太好了,现在,你很痛苦吧?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喊!”
金雕玉琼的御书房内,宋真宗一袭龙袍威风势抵万千,只是周身被无奈压抑的灰暗比起龙袍上张牙舞爪的巨龙不及其万分之一。
书房内,另外侍着四五名老者,均是金丝大蟒袍,腰束玉帛带。头戴一品大员乌纱,面色凝重。
真宋来回踱着步子,心下焦躁不安。
“皇上明见。依老臣看,即便此事为虚,但闵王爷拥兵自重,其威望更无人可及实乃朝中一大患,为防不测,不如先收了他兵权,再做衡量!”
话音一落,迅速有站人出来厉声反驳,双目怒瞪,恨不得把那老贼的嘴巴给烧烂了。
“潘臣相!”
说话的是正一品巡府。铿锵有力。如惊雷压下。
“哼!”潘仁美冷哼,鼻孔朝天,丝毫不将对方放在眼里。
“凡事要讲证据,单凭韩尘一人所言不足为信。万一错杀好人,岂不是正中辽贼下怀,亲者痛仇者快吗?”
“好人?嗯!”应着他的话,潘仁美嗤之以鼻,扬起眉梢,神彩飞扬跋扈,带着兴灾乐祸的意味回道:“老夫也相信闵王赤胆忠心。那么!为了以表诚义,就将三军帅印上交,这份诚义才够重吧!”
漆黑的地牢,阴潮寒冷。被关在此已有半月,赵闵深知凶多吉少。牢狱之灾,他的睿气丝毫未见褪减。
他并不在乎区区一个亲王的位置。只是心中有一个模糊的意念。这件事只是一个开始,对方出手快又狠,且直捣要害,懂得打蛇看准七寸。
然而,他慢慢踱步到铁栅栏前,随着走动脚上的铁镣发出沉闷的声响。为什么心中那股强烈的不安并非来自今日牢狱之灾呢?
这时,有狱卒端着盘子走来。打开了门,态度非常恭敬,将盘子放到地上,说道:“王爷,请用膳!”
低头看了一眼,虽说比起府内膳食确是天壤之别,但就牢内的伙食来说,已是再好不过的了。比起昨天的那顿……
他微微一点头,自嘲:“想不到本王如此落迫,也有人会伸以援手!”
狱卒惨然一笑,叹息道:“王爷这么说是折煞小人了,这是小的应该做的,当年若不是靠了王妃娘娘,小人家里早就家破人亡,哪还有能吃上皇粮的今日!”
“王妃?”一时间,赵闵反应不过来。喃喃自语,突然,灵光咋现。一记了然收回眸中,他想起来了,那个被抄家灭门,送到异国他乡的……麟儿!
心!赫然疼痛不以,恍如一把布满芒刺的利刀狠狠插进来回绞到,血肉模糊。
“麟儿!麟儿……”泪水模糊了双眼,手狠狠攥紧,粘湿一片。眸底压抑的是被被叛的痛恨与了然的爱意。
‘为什么要背叛我?为什么?’
他无法释怀她的红杏出墙,更恨为什么自已爱的竟是这样的女人。
见状,对方同样黯然伤神。生怕再提起赵闵的伤心事,便离开了。之于百姓的意识里,闵王妃死于重病,并不知晓其真正原因。而皇室亦不可能将这种丑事公布,于是真相像便被这最美丽,最冠冕堂皇的借口永世湮埋,不见天日。
闵王府。
数万名御林军将整座府邸团团包围。连每日府内必用的开销都改成专人送入。一时间似乎圈成了牢笼,连一丝丝阳光也无法照进。华贵的府邸内一片灰暗,每个人整天兢兢业业,愁云惨淡。浓浓的乌云当头压着整座王府透不过气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