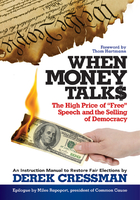大龙镇上只有两家医院,正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但不管怎样小镇的医疗条件还是相对落后,除非事出紧急,大多数居民宁愿花上一个小时跑去邻近的明远市。因此,当赵新成得知女尸生前长期在镇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时,感到非常诧异。镇上的第一家医院,年代久远、设施落后,哪个重症病人会选择这样的医院?
呼啸飞驰的警车内,赵新成和周渝信却彼此无言。在这样静默的氛围中,一个人是如坐针毡,左顾右盼着想找点话题,而另一个人则是专心开车,瞟都不瞟一眼。赵新成知道不可能指望周渝信开口说一句话,只能焦躁地按下车窗,假做欣赏路旁的风景,飒爽的凉风也压不灭蓬勃的心火,他只能没话找话:“小周,你来过这里吗?我猜你肯定没来过。”周渝信目不斜视,也没有任何动作,语气冷淡:“来过。”粗线条的赵新成一点也没察觉周渝信语气中的疏离,只是很惊讶地感叹:“你居然来过!你才23岁吧,真没想到!”
镇第一人民医院所在的位置是30年前曾经是大龙镇最繁华的街道,医院邻靠客运站,那时来往车流皆汇聚于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如今,好景不复当年,车站仍在,人流早已稀疏。沿路走来,尽是排排林立的店铺,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依稀可辨往日繁华,只是门面古旧晦暗、招牌破旧凋零、客人寥寥无几。间或掠过的学校也早已废弃,或改造成工厂发挥余热,或遍地荒芜生机不再。
“怎么这么,热闹?”对自己看到的场景,赵新成在脑海里搜了几圈才勉强找到一个词来形容。医院正在改建中,原本还算宽敞的大门只留一条勉强可供车辆通行的通道,两边堆满破碎的砖瓦,除了住院大楼其余地方均已拆除,轰隆隆的机器嘈杂地工作着。简陋的白色停车线形同虚设,也不分车种,全都乱七八糟地混在一起。短短几百米,赵新成目瞪口呆,感觉自己的下限正不断刷新,忍不住扯着嗓子吼着:“怪不得没什么人来呢,环境这么差!”不过,他的声音很快淹没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唯一的听众周渝信只出神地盯着大片废墟,拳头紧握,丝毫没有察觉自己并不算尖利的指甲已在脆弱的掌心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镇第一人民医院很少收治重症病人,因此院里的医生护士对这名特殊的病人都印象深刻。有人说,这个女人有一天突然出现在这里,孤身一人,一住就是5个月,熬过残酷冰冷的冬天,在冰雪消融的春天复苏,却没等来璀璨的夏日;也有人说,她不是一个人,有一个年轻俊朗的男人常来探望,形状亲密,也许是男朋友;还有人说,这个苍白脆弱的女人,永远都是安安静静的,就像一朵逐渐枯萎的花朵,不复往日颜色。独独没有人记得她是什么时候离去的,也许在太阳西落的黄昏,也许在寂静无声的午夜,也许在最为黑暗的凌晨。总之,当护士巡查的时候,枯萎的花朵已经彻底凋零,她走的极尽安详甚至优雅。
赵新成和周渝信两人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了她的主治医生,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高高瘦瘦的身材,干脆利落的平头,整洁有序的打扮,和看起来杂乱的医院毫不相称。不像其他医生敞着大褂,他的白色大褂从上到下一丝不苟整整齐齐地扣着扣子,天蓝色的医用口罩牢牢地遮住了口鼻,只露出微微皱起的额头和掩藏在冰冷镜片下的双眸,严肃得有些不近人情。赵新成偷偷瞟了一眼周渝信,叹了口气,真烦,又是这种“精英人士”。赵新成清咳了两声,充满笑意上前寒暄:“您好!呃”赵新成停顿了片刻,微眯着眼辨认小小的名牌:“宋医生,我是大龙警局刑警队队长赵新成,这位是我的搭档周渝信,我知道您这样的医生肯定很忙,但是我们···”宋医生一脸不耐地打断了寒暄,但冷静的语气却听不出任何情绪:“不用介绍了,直接说吧,我的时间很宝贵。”真是大爷!被打断的赵新成只能憋着火气在心里抱怨,表面上还是一脸微笑,简单说明了来意又试探着问:“她在这里呆了很久,不知道宋医生还记得这个病人吗?”赵新成既看不清楚宋医生的表情,也听不出他语气的波动,平静得一如既往:“我记得,她是我的病人,癌症晚期,病得很重。”赵新成接着问:“宋医生,要不,您给我们讲讲她吧,她是怎么死的?什么时候死的?”宋医生正打算开口,走廊里却突然喧闹了起来。
“快,让一让,让一让!”是一个紧急送往抢救的重症病人,已经被病痛抽干了精血,形销骨立,雪白的病床上更显得脸色青黑,扭曲的面部因为极度疼痛而露出挣狞痛苦的表情,像脱水的鱼一样扑哧扑哧地急促呼吸,即便圆睁着双眼也无法聚焦,只显得更为可怖。赵新成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感受过一个即将痛苦逝去的生命,他的内心很震撼。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背着手老成在在的宋医生,无动于衷地保持着冷漠的表情。赵新成有些愤怒,一个医生怎么能如此漠视生命?幸好他没有看到站在自己身后的周渝信,不然一定会脊背发凉。
病床匆匆掠过,走廊又恢复了平静。彷佛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宋医生继续回答赵新成的问题:“她是病死的,死亡时间,我不记得,我有很多病人,你们去问护士吧,我还有事。”说着转头就要走。可赵新成一直不是什么好脾气的人,也没那么好糊弄,当下就把他拦下来,本来就有些忿忿不平的他语气尖锐:“病死的?宋医生,您确定吗?可我们得到的信息不是这样呢。”说着又发出一声冷笑,猛地一拍手,语带讽刺:“哎呀!我差点忘了,您是大忙人,一个普通的病人是怎么死的,死亡时间又是什么时候,这种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您是不屑于记的,还是说根本心里有鬼!”这段话成功地惹恼了宋医生,他神色激动,好像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差点冲过去揪领子,极力控制下才仅仅是提高了声音,怒气冲冲地质问:“你说什么?你在质疑我的职业素养吗?还是说···你在怀疑我?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医生!”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氛围下,像隐形人一样的周渝信却开口了:“安乐死,您怎么看?”虽然没有说出姓名,但在场的人都知道他在问谁。而宋医生的眼神第一次动摇了,晃动的瞳孔昭示着他内心的不平静,他没有转身,却后退了一小步,随后握紧了拳头,恢复了平静:“我说过了,我是一个医生,医生的天职是救人。”
“让一个痛苦的生命得到解脱···这不算救人吗?”这句话说得太理所当然,赵新成都有点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而宋医生直接越过了赵新成,站在了周渝信的面前,几乎要脸贴着脸,然后紧紧逼视着周渝信的双眼,一字一顿地回答:“救人,是救死扶伤!”周渝信丝毫不退让,他突然变得能言善辩了起来:“这是一件好事,她会感激你的,为什么没做?为什么不做呢?”
没有大吼大叫,没有情绪失控,赵新成的心却莫名抖了抖,他吞了吞嗓子,有些讪讪地打圆场:“你们,在说什么呀?我怎么都听不懂。宋医生,我们今天已经打扰您很长时间了,您是不是还有事情要忙,呵呵,您忙去吧,别管我们了。”说着他伸手扯了扯周渝信的衣角,但这个死小子直挺挺的纹丝不动,倒是宋医生先退了一步,不过脸色很臭,嘴里哼了一声甩手走人了。谁知赵新成反而得寸进尺,又扬声喊住了他:“宋医生,之后我们要再有什么事情找您,您可一定要空出时间来!”而宋医生只稍微停顿了一下,连头也没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