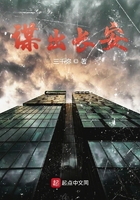被一身缁衣包裹,人越发显得形销骨立。棱角分明的脸庞有着刀斧般的印痕;镜片后有双深邃又透着点苍凉的眼睛,一副远忧不断、近虑重重的模样;而两片薄薄的嘴唇紧闭,足见其内心决绝的斗志……
望着坐在对面的林怀民,脑海里闪过龙应台的一句话:沉默的“惠能”。
林怀民听了,咧了咧嘴,露出一丝苦笑:“除了瘦,大概与惠能没有一点相似。瘦,也是长期劳累,而非常年修炼。”
四十年前,台湾地区社会依然封闭、保守。那时,舞蹈远非良家子弟愿意所为。如此环境下,决定脱下衣服,露出肌肉,大声喊出“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的口号,是要有勇气的。
幸好,林怀民成长于一个开明家庭。儿时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墙上挂着的两张照片:歌德与贝多芬。尽管身处困难年代,每日放学归来,母亲照例送上两块饼干和一杯牛奶,然后用手摇七八转唱机,放莫扎特和贝多芬,间或也有《托斯卡》之类的歌剧。“我的价值观就建立在那个精神层面的追寻和尊敬上。”林怀民道。
而一部《红菱艳》更让林怀民痴狂。他发现人只有舞动时,才能展示不同侧面。一个才五岁半的男童,终于中了舞蹈的“毒”。
即便后来去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求学,行囊里也少不了一双舞鞋。或许是造化弄人,抵美不久,艾奥瓦大学便向他招手。从此,舞蹈与他如影相随。有人形容那时的林怀民:“走着,谈着,突然,他脱下鞋子,在大街上、人行道上凌空跃起,落地之后很美地又旋了一个转子。”
回到中国台湾后,他创立“云门舞集”。
“云门”一词源自《吕氏春秋》:“黄帝时,大容作云门,大卷……”据说,那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只是舞姿、舞容早已无迹可寻,仅空留下这动人的名字。因此,“云门”草创时期作品大抵从古典出发,如《奇冤报》《寒食》《乌龙院》《白蛇传》等。渐渐地,林怀民竭力摆脱故事的牵绊和文字的桎梏,完全靠着舞者用身体内在能量流动,以肢体表达意绪与情感。用他的话来说:“舞蹈是一种交流,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和自己形成相互补足的关系,两个身体互相影响,然后自我消失,变成相同的一个。”
像《水月》,随着巴赫大提琴曲,舞者那空间感十足的肢体摆动,传达坚韧与柔美;《竹梦》以“晨舞”“春风”“夏喧”“秋径”“雨舞”“午夜”“冬雪”等舞段,描写修竹挺拔,常青如翠玉;《行草》则靠纯黑白铺陈中国书法之美,舞者身体运动恰似书法委婉转折的点捺顿挫,有“飘如浮云,矫若惊龙”之神采,使人想起《维摩诘经》里的句子:“是身如幻,从颠倒起。”而《红楼梦》干脆没了黛玉和宝钗,也没了贾母与刘姥姥,唯有白衣和红衣女孩,以四季更替、漫天飞舞、密如珠帘的灿烂花雨,烘托身着绿色三角裤的贾宝玉,吟咏“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时光流逝。
“云门”对舞者有着极其苛刻的标准与要求。对林怀民而言,他期待的不仅仅是动作,更是在跃身的刹那,肢体舞动所流出的生命汁液。排演《薪传》时,他把舞者带到布满石头的河滩上,或跪、或爬、或躺,让其感受石头和身体接触的苦楚,体悟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拓荒精神。而平日里温文尔雅、视舞者为家人的林怀民,一旦发现舞者懈怠,便立刻如暴君般雷霆万钧。一次,他竟失控以重拳猛砸玻璃,顿时血流如注,别人趋前为他包扎,他却执拗地用另一只手阻挡,“如果你们不懂得爱惜身体,那我也不要爱惜自己。”因此,“云门”舞者将舞蹈等同于生命。有评论称:“在舞台下,他们没有出众的仪表,没有时髦的衣服,走在芸芸众生里,谁也不会注意;在舞台上,他们却是一颗颗闪亮的星星,谈起舞蹈来比孔雀还骄傲。”
“云门”作品大都源自生活。林怀民说,他从小在稻田遍布的台湾南部长大,收割后,农夫会将金黄色的稻谷撒在地上晒干,孩子们常去那儿玩耍,稻谷的金黄色因而深植脑海。十四岁那年,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的小说《悉达多》里印度苦行僧与百姓于恒河边膜拜的情景深深打动了他。一次菩提伽耶之旅触发了他的灵感。于是,我们看到,一位求道者自始至终伫立舞台,任由金黄色稻谷倾泻而下,穿着白衣衫的舞者手持缀有铃铛的手杖,漫步于蜿蜒如河的稻谷。舞蹈所蕴含的能量让人如置身恒河,波涛起伏,充满对生命的虔敬。《流浪之歌》用浪迹天涯的疲惫洗去罪恶,进行一次心灵的朝圣。
“云门”已至不惑,林怀民仍在忙碌,仍在奔波。玛莎·格兰姆说过:“不是我选择了舞蹈,而是舞蹈选择了我。”我问林怀民,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否可成为恩师这句话的最佳注解,他沉默了一会儿,仰起头,注视远方,“时间如同一条幻想的河流,穿越生命的分分秒秒。每个人一旦找到命定的角色,便不想逃,也逃不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