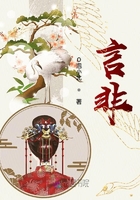“姑娘不饿吗?”
朗月回过神,将盘子接过,“谢过公子。”
拿起一块核桃酥放入嘴里,酥香脆口,真好吃。
少年微微一笑,“姑娘家中可是有病人?”
朗月将糕点咽下,眼眉低垂,伤怀道:“我爹爹染了瘟疫,正等着我拿药回去呢。”
念起爹爹,她鼻子又是一酸,声音也微许哽咽。
“姑娘若是不嫌弃,可将剩下三包药一齐拿去。”
朗月面露欣喜之色,“真的吗?”
少年安然颔首,“自是可以。”
“多谢公子!”,朗月忙跪在地上,连连磕头。
少年将她扶起,轻声道:“几包药而已,不成谢意。”
朗月目微红,谢道:“这几包药,于小女却是救命之恩,他日再相见,定当以救命之恩来还。”
少年未再多言,只道:“往后有缘,再见也必是乐事,如今已过了夜,不知姑娘家住何处,在下好送姑娘一程。”
朗月记得自己昏倒时还是黄昏,这会子却已是醒晨,已经过了一日,是该尽快回家了。
朗月不再客气,更顾不得什么礼节,道:“小女家住南山,若是公子方便,将我送到南山脚下便可。”
“南山!那里离渭城挺远的,不过在下正好要去那见一位友人,倒也可以送姑娘一程。”。
说完少年将车帘拉开,对着马车外正在烧火的二人道:“去南山。”
“是!”手下两人接令,迅速将火扑灭,驾着马车,吆鞭而去。
朗月脸皮子薄,一路未敢多语,少年也不是个话多之人,所以直到分别,她也没问出少年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个王爷,却不知是哪个王爷。
也罢,若日后再见,定要十倍的还上恩。
山路崎岖,甚是难走,朗月顶着日头一步步回到熟悉的山村。
盛世时,这个时辰大家都会去忙农活,现今旱灾没地可种,可还是有人来村外的井中打水,猎户们也会早早起来查看昨夜布置的陷阱。
可如今她人都已经跨过界碑了,仍旧一人未见,莫不是村子里有什么集会,族长将大家伙都叫了去。
思来覆去都得不到称心的答案,直到她看见一群人将他们家小茅屋包的严严实实时,才知道出事了。
朗月上前扒开人群,被拉开的人先是一愣,后而大叫起来,“不好,这家的瘟儿回来了。”
听到有人叫喊,众人瞬间慌乱一片,每个人都像躲脏东西一样躲着朗月,生怕挨着她一下,就连平日对她极好的刘家夫妇也捂着口鼻躲瘟神似地躲着她。
朗月心中一阵冷笑,不过也好,省的她费劲挤过去。
“阿娘!爹爹!”朗月对着屋子喊道。
“阿娘,爹爹...”
“孩子,别喊了。”老族长拄着拐杖,步态龙钟地朝她走来,因常年弯腰劳作,背已经驼了下去。
“阿娘!”朗月不听,跑到厨房将门打开,却没有阿娘的身影。
老族长叹气道:“孩子,别找了,你娘被人带走了。”
朗月又走到老族长跟前,“带走了?谁带走的?”
老族长道:“我也不知道,当时天朦朦亮,我眼神不大好,只瞧见他脸上有条狰狞的疤,对了!他还留下一句话,说是你回来了就先在屋里等着,他会来找你。”
“族长,那我爹呢?”
老族长连连叹惜:“孩子,节哀吧。”
朗月却像是听不懂,摇头直笑:“族长你说什么呢,我爹爹还好好的,节哀作甚,你看!”
她将手里的药拿给族长看:“你瞧,这是我下山找来的药,还是药圣开的呢,可灵了,爹爹只要把它吃了,一准能好。”,她的笑天真到叫外人心疼。
老族长实在不忍心,可事实不容置否:“孩子,你爹真的死了,我亲眼看到他系了一根白绫,吊死在那房梁上。”
手中药包掉落,朗月瘫坐在地上嚎啕大哭,她终究是个孩子,不过十岁,理解不了生离死别,也忍受不了生离死别,只晓得她没了爹,没了将她捧在手心上的爹。
“族长,我看这家媳妇都被人带走了,男人又死于瘟疫,要不然我们直接把这房烧了,省的去抬那死人沾染一身晦气。”张泼妇扭着她臃肿的身子来到族长跟前言语道。
这番话却将朗月惹毛,她破口大骂:“你个丑八怪,休要碰我爹爹一下!”
“你个小贱货,再说一遍。”张泼妇瞪着眼刚想狠狠扇她一巴掌,又怕染上瘟疫,只好愤愤作罢。
她咬着牙,扬起一脸横肉嚣张道:“老娘不仅要将你那个染了一身瘟疫的死老爹烧掉,还要把你关到黑屋锁起来。”
“你给我闭嘴!”老族长厉声呵斥,气的胡须直抖。
张泼妇这样欺软怕硬的家伙,自是乖乖闭了嘴。
“族长,张泼妇说的没错,这瘟疫传的猛,若是不将尸体烧掉,咱们整个村怕是不保啊。”
“是啊,村长。”
“.....”
一人应和,其余人也纷纷叫和。
朗月将泪擦干,站起,将肉眼所见的一切可丢之物尽抛向那群人,“滚开!你们都给我滚开!谁也不许烧我家。”
“呦呦呦,小小年纪这么大的戾气,跟她娘一样,当初我就说那女人会给这家带来霉运,朗子就不该带那女人回家,长得漂亮又怎样,还不是个祸害精。”
“丑八怪,闭嘴!,你不就是嫌我爹当初娶了我娘没娶你吗,你也不照镜子看看,就你那副丑模样,除了你那怂包丈夫谁人敢娶你。”朗月满心愤恨,面对她只想将最恶毒的话说出。
人群中传来几声耻笑,张泼妇再也忍不下去,气势汹汹挥掌就要朝朗月脸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