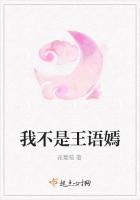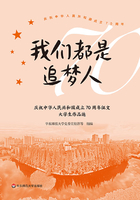这是一家家庭旅馆,典型的藏式两层小楼。昏黄的灯光下,出来一个妇人把我们迎进了楼下的大厅。温暖的房间里有电视,中间照例是个牛粪炉子,上面的大锅里热腾腾地煮着酥油茶。厅里坐着本地人、内地旅客和几个外国人,在聊天或发呆。
我们被安置在二楼一间五个床位的房间里,他们这会儿生意很好,只有这一个房间了。次丹是司机不要钱,我和小奇合住,一个床位50元。
10点半我们早早就睡了。本打算用自己的睡袋,一看床铺都挺干净,而且一点都不冷,就用了店里的被子和毛毯。原来下来1000米,就会有那么大的差别。
一夜温暖,没有了一直刮着的BC大风!
这里海拔4130米,是个小盆地。
早上快10点了才起。
一夜的狗吠,太有意思了,不是一只狗,是全乡的狗几乎都没停地叫了一整夜,真明白了什么叫“一狗吠影,群狗吠声”了。迷迷糊糊中我还很佩服这些狗怎么会精力那么旺盛,这么个叫法,它们的嗓子怎么就不痛呢?
随着天渐渐亮,狗儿们不叫了,门前大路上的各种车——汽车、摩托、马车又忙了起来。不过,这是很温暖的一夜。
起床后,比我早起的小奇很像那么回事儿地带我参观了一圈:这里是冷水桶,这里是刷牙的地方,这里是厕所……显然这儿的厕所比大本营的好很多,在室内,地面上的三个洞,很深,可以望到一楼连通室外的地面,每天夜里都往里洒草木灰,所以很干净,而且没什么异味,实在是个好方法。
服务的女孩告诉我们可以搬到对面一间,在厕所隔壁,是个双人间,窗外有山还有条河,而且房间向东,早起看得到太阳,很安静。我和小奇马上答应了,因为昨晚住的那间又是狗吠声又是车马声,的确够吵的。
早餐在旁边一家“天府小吃”吃的,粥、包子、煎鸡蛋,这家显然以做馒头见长,不断地有人来拿馒头。
我们住的斑巴家庭旅馆,就在这个乡的三岔路口上,仅有的几家川菜馆也在这个路口附近。“扎西”就是吉祥的意思,“宗”就是汇集的意思,这是个吉祥汇集的地方,西藏很多这样的路口村庄都会叫扎西宗[10]。村里的小街不过50米长,以一个三岔路口为中心,三条路:一个方向是拉萨;一个方向去珠峰;一个方向去往嘎玛沟[11],著名的风景区,徒步的好地方。
斑巴旅馆的老板叫次仁顿珠,按他老婆的话说,他从早到晚什么活也不干,就是一直在喝酒,但他们夫妇俩为人乐善好施,性格豪爽,老板当选了人大代表,经常帮助周围的人们向上反映问题。听说今年上级让他去北京人民大会堂开会,他说他不去,理由是北京没有糌粑吃,没有青稞酒喝。
老板的确能喝酒,从早到晚都晕晕的,笑眯眯的,喝了睡,睡醒了喝。
老板娘,36岁,胖胖的,很干净,很健谈,也很能干,和我们聊天时手里也在不停地干活。她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大女儿挺漂亮的,就在这个店里和她一起忙乎,21岁尚未嫁人。老板娘说将来想让这个女儿把店经营下去,想给她找个老实、心好,能帮着料理店的男人。还有两个男孩在上中学,所以这会儿店里还有小儿子和小女儿。
斑巴旅馆是次仁夫妇白手起家做到今天的,因为他们是当地致富的带头人,得到不少政府的荣誉。日喀则旅游局奖励了5万元给他们,他们商量着把这5万元周济给了乡里其他的穷人。据说拉萨电视台曾有一个春节晚会的小品,是根据他们拾金不昧的故事改编的,大意是说一个外国的珠峰领队丢了装护照和现金的包,被他们捡着,归还了。老板娘说起来时,说不是自己劳动赚来的钱,他们不想要。
老板娘说话表情丰富,经常会哈哈地笑——真觉得她的幸福感远远大于我们。
斑巴旅馆有65个床位,总是迎来送往着世界各地的人,老板娘对她的店有许多理想,她想让它更加的舒适,藏式的味道更加纯粹,还要在外面加盖一间洗澡的房子,
总之,作为这一带的第一家旅店,经营了那么多年,她非常知道各国的游客们需要的是什么。不论来了什么客人,奉上的甜茶都是免费的,还有中间那个大牛粪炉,以及老板和老板娘的热情,让你首先体会到的就是无尽的温暖。满屋的奖状也是他们的骄傲。
一会儿,门口来了辆吉普,下来一行藏人官员,也进来喝茶,说是珠峰自
然保护管理局的领导。过了一会儿又进来几个背包徒步的老外,再一会儿又是几个牦牛工。总之,来的都是客,什么人都接待。大堂里其乐融融,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以各自的方式围炉而坐,享受着同样的时光。有的喝茶,有的喝酒,有的聊天,有的写日记,有的蜷在一角睡觉、看书,还有的干脆就在发呆。时间就这么过去,只有墙上那个会说话的钟,每隔一小时报一次时,唆唆地说上一通,你会才意识到:哦,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今天阴天,队友们从山上发来短信说,从昨天到现在,大本营降了一天的雪,已经20厘米了,我们这里却要舒服很多。
喜欢让自己蜷缩在这么个地方,西藏的,很深、很远的一个小乡村的小客栈,谁也不认识谁地一起享受着如此温柔的时光。
到中午时次丹罗布说这里有一家川菜馆的炖鸡好吃,但过去一问全乡到处都没鸡卖。后来老板娘不知从哪里搞来一只本地土鸡,终于让我们吃上了炖鸡。
川菜馆的老板娘说在这儿都七年了,孩子在家乡。她忽然问我想不想吃鱼,我们当然是眼睛一亮,问她哪儿有。她说如果我们要吃,就让她老公下午骑摩托沿河下到一小时远的地方给我们钓去,但因为藏人不吃鱼,如果他被抓住会挨打的。结果我们很感激地答应她晚上再来她的馆子吃饭。
这里河的上游就是冰川,高山冷水的鱼,叫雪鱼,那肯定是味道鲜美的。
怀着对鱼的期待,我们又回到旅馆大厅围着炉子继续自己的下午时光。没想到队长和其加开个大卡车到了!
我们喜出望外!原来他俩不放心,专门来看我们。想想他俩开着辆卡车来到这里,多不容易,跑了两个多小时,卡车边上的护栏都颠掉了。
其实就在今天上午,营地里其他人还发短信告诉我,罗塞尔正在我们营地和队长喝一大瓶红酒,按他俩的话说,这样的坏天气就是用来喝酒的,没想到下午队长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
想想也真是很佩服罗塞尔这些人,竟然就这么在珠峰干了25年,现年55岁的他还在担心退休之后珠峰的事。
既然队长到了,我们就从对面川菜馆叫了两个菜,又从这家店里要了啤酒。看我们在这儿吃住都好,队长建议说我索性再多住一天,彻底养养再上去。吃完饭队长让我们带着他到小乡镇上转了转,说大队人马从ABC下来修整的时候,也可以考虑在这里。只是温泉离这儿有近一小时的车程,不知条件怎么样?能让大家洗个澡就好了。
不过队长总认为我是装病,也许我的确有些畏难情绪。这个温柔的小乡村,总是让我很想念阿里的时光,我要是知道养病得那么久,还不如先去阿里转一圈呢。
被我这么一说,队长又反过来安慰了我一通,像个外公似的再三叮咛,一大堆“这那、那这”的,然后吃了他的菜,喝了啤酒,就带着其加告别我们,回大本营去了。
送走了队长、其加,看着他们摇摇摆摆的大车消失在村头拐弯处。我们又开始期盼晚餐的鱼了,可老板娘的老公还没回来。
晚上9点,鱼终于到了。我们先去了厨房,看到那大盆中有六、七条鱼。按我们的要求清炖,果真味道鲜美,还带点甜味,太棒了!
我们还答应她明天接着来吃剩下的那几条鱼。
回到旅馆,又接到队长的短信,叮嘱我要记得做雾化。正好这会儿也有电了,我就和小奇一起整好了雾化器,套上面罩开始云雾缭绕的雾化过程。
这下可把客厅里的几帮子人给奇怪坏了,纷纷远看近观地研究起我在干嘛。因为电压的原因,我一做雾化,他们就看不成电视,于是干脆围观我,一个个倒也饶有兴趣。没想到我做个雾化,还能给别人带来那么大的欢乐。
老板的女儿在给一大帮刚从珠峰下来的牦牛工煮面片汤,这是他们的传统美食,九个人,一大锅,每人两碗。其中一个牦牛工显然喝醉了,这里人喝醉是常有的事。
我们11点多睡的,一天又过去了。
早晨是被阳光晒醒的,东窗的太阳很温暖。不临街的这间房,少了很多的嘈杂,也没有狗吠,我一夜睡得极好。
早餐照例在那殷勤的四川老板娘的店里吃的,她给摊了鸡蛋饼,还有白粥、鸡蛋。
我们商量着午饭在旅店里吃次藏餐,晚餐再来吃她的鱼,她很高兴。
早餐后,我们照例出去溜达,可是这么小的地方,一溜达就出了村子,进了农田,老是有小孩围着我们,次丹给他们买来了一些泡泡糖和圆珠笔。
春耕开始了,农田在灌溉。
我们发现这里特有的一种柳树正在发芽,芽儿很粗壮,还有喜鹊。又看到废弃的水磨房,穿着单薄的小孩趴在地上喝河沟里混浊的黄泥水,让我想到我们苹果基金会的助医工程,据说这一带的条件还算是好的。
充其量也就走了一个多小时,竟然觉得累了。唉,队长说的没错,我是真的病了,但也有心理原因。觉得在这儿多舒服,真不愿上山去了。
接到山上的电话,说今天风小,但下雪,我们这里却阳光明媚,两处才相隔50公里的距离。
回到旅店大堂继续写我的日记。各色人等来来去去,而我坐在一个有阳光的角落里,倚着一大堆棉被。
不知过了多久,厨房里飘出香味,我们的午餐又开始了。典型的藏餐:小白菜炒牛肉、西红柿炒牛肉、青椒炒鸡蛋、菠菜蛋汤。和我们的做法很不一样,味道重,肉块硬,但很香。配上米饭柔软的口感,我吃了一大碗,食欲大增,又加了半碗。
午饭后,我们又出去走。这次我们朝着拉萨的方向,沿着河床走,也很有意思。远远地看到一个人躺在水渠边上,我们过去和他聊天。是一个喇嘛,52岁,从庙里请假回来帮农8天,以前有妻有儿。这会儿他在看水渠、晒太阳,就那么四仰八叉地直接躺在土地上,那叫一个放松啊,令人羡慕。
接着又是一下午大堂的时光,太阳从东到了西。厅堂里的客人换了无数拨,今天老外多,有上山去的,也有刚从山上下来的。进来的人吃蛋炒饭的居多。邻边小学校的几个老师也来吃了蛋炒饭,边吃还边揪了一个小男生训话,说什么听不懂,总之可以看到小男生吓死了,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包烟交给老师。不一会儿又来了个小男生,两个人一起怯生生地似乎在坦白什么罪行。老师则严肃得像警察。大概意思是这两个小孩不好好学习,成绩不好,还抽烟。
过了一会儿又接了一个宝哥的电话,聊了很长时间,他说柿子林现在可美了,贝贝学习很好,但调皮的多多又把大腿根的韧带拉伤了,五一他们哪儿也不去了。唉,都是因为我不在家,否则肯定不会让他们在假期闲着的。
陈章良又来了个电话,他们要来了,问我山上的气候。接着老板娘又哈哈笑着进来了,她换了一身粉红色的衬衣,一身藏装,说要搭车去拉萨,去着手她店面的装饰改造计划,采购藏毯饰品,说完她哈哈笑着出发了。真羡慕她的心态,她的快乐是发自肺腑的。
我又出去在农田里转了一圈,赶上孩子们放学,次丹罗布发完了泡泡糖和圆珠笔。
傍晚的乡野农田像凡·高的画。
晚饭又去那家四川饭馆,老板娘给我们准备的鱼留在一个大脸盆里,我们依然在唯一的一张大桌旁坐下。不一会儿来了一帮广东游客,次丹罗布马上和我们说,是不是把大桌让给他们,我一开始还真没反应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