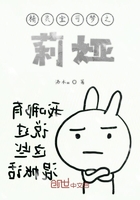青鸾的头垂在了郎佩的腿上,郎佩眼睁睁地看着怀中的女子没了心跳。
明明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却倾刻间香消玉殒,温热慢慢散去,她的身体愈来愈凉。
这个女子,曾经拥有世上最灿烂光滑的羽毛,初见她时,她还是天帝的御前织女,在殿下与瑶姌长公主的订婚宴上,她不顾众仙眼光,亲自为璧人呈上一件五彩霞衣。
当瑶姌长公主心花怒放地伸手去接之际,她却高傲地捻起一丝六丁真火将霞衣烧成了灰烬,险些伤了公主,天宫里的其他仙娥都在传,那件霞衣是她拔掉身上最美丽的羽毛织就而成成的。
她顾不得长公主那似要吃人的眼神亲手将灰烬撒落在百里弈的手心之上,一字一句道:“从来只见新人笑,有谁闻得旧人哭,青鸾以此五彩霞衣为祭,悼念逝去的故人阿漓,一愿驸马爷与阿漓的恩怨两相清,再相逢,只道是路人;二愿驸马与公主花好月圆人长健,岁岁平安,三愿佳人成双,沧海桑田莫相负,世世缘不忘。”
订婚宴上这一突发的小插曲,令天帝震怒,第二日青鸾的官衔便从高贵的御前织女降至司鹿侍,专门料理天庭仙鹿的起居饮食,这职位甚是卑微,说白了,司鹿侍就是为仙鹿喂吃喂喝打扫屎尿的杂役。
正所谓祸福相依,青鸾此举引起了百里弈的注意,百里弈以玄跻山缺少一位女管事为由,向天帝请了旨,讨了青鸾作郎佩的副手。
百里弈静静地伫于黑夜之中,默默地看着没了气息的青鸾,脑海中忽现浮现阿漓那张被火烧伤支离破碎的脸,大概连他自己亦料不到,当年,他竟会对此生唯一深爱的女子下狠手!即便当时他恨她入骨,心底深处却舍不得伤她分毫!
然而,有个缥缈的声音一直在耳边萦绕,“玲珑赤狐的处子心可医你母妃的性命,她既自裁,何不物尽其用?……”
他的双手犹如不受自己的心脏控制一般,慢慢地伸向她的胸膛……
的的确确是他亲手取了至爱之人的心脏!自责,犹如一条艳丽的毒蛇,一点一滴地啃噬着他的心脏,眼前萦绕起淡薄的雾气,空里流烟中他似看到阿漓那张熟悉而寂寞的脸……”
“阿漓……”他轻轻唤她的名字,握住她清凉的素手。淡雅的脸庞忽然变得惊恐,她拼命地甩开他的手,仿佛怕他怕到了极点。
“阿漓,我不会再伤害你,原谅我。”。
“又来,第二次了,你有完没完了,别碰我,杀人不见血的大魔头!”
宛筝的泪水莫名其妙地倘了下来,她不晓得自己为何为哭,只觉得青鸾自尽的场景异常熟悉,仿佛她也曾用利刃自裁过,无尽的悲伤似暗夜将她包围,下一刻江寒翁突然从身后冲出来,冷不丁地给了百里弈一拳,百里弈这才如梦初醒放开她。
“百里弈,收起你那副假惺惺的面孔,不要再演戏,你若如此长情,大可寻遍千山万水,找到阿漓的一丝魂魄,令她往生,又何必在此浪费光阴?宛筝不会是下一个阿漓。”
江寒翁将他推搡至一旁,转而握着宛筝的手,像握住天下珍贵的至宝,他拉着她径直走到昏厥不醒的承尧面前,示意小花将承尧带上。
几人打算离开,百里弈淡淡扫了承尧一眼;“你们现下离开,恐有不妥,看他气色,乃魂魄离体的面相,若我没猜错,你师伯的魂魄此刻正游离在弹虚之境,若他的魂魄不能归体,肉身很快便会腐烂,玄跻山无嗔泉水可助他肉身不腐。”
“你先安顿一下这女子的后事罢,毕竟你们相识一场。”
宛筝下意识地瞧了青鸾一眼,把目光放到百里弈的脸上,她试图从他脸上寻到一丝悲伤,然而除了一惯的清凉,他的脸上连半丝温情都没有,素来听闻鲛人是冷血动物,果真如此!
宛筝原以为,青鸾姑娘对百里弈这般上心,面对如此貌美的女弟子香消玉殒,百里弈这当师父的即便不伤心得痛哭流涕,亦能象征性地掉几滴眼泪罢,可看如今这情形,借此敛几颗鲛人泪作盘缠的小算盘算是落空了。没捞到一丁点儿好处,反倒弄得自己的心拔凉拔凉的。
百里弈把跌坐在地上的郎佩拽起来,凉薄地命令道:“青鸾本已天庭代罪之身,如今畏罪自戕罪加一等,你且把她的真身敛了,送去太上老君那里作药引,毕竟是天生地养的神鸟,骨骼定是上好的药材,噢,对了,别忘了替我写一道罪己书呈予天帝。”
几人闻言皆一惊,宛筝的心猛地沉了下来,头皮开始发麻,这神仙……当真无七情六欲绝情得很!若让他当了自己个的师父,凭自己这不长记性爱闯祸的脾性,不知在他手底下还能活几天?
郎佩不可置信地瞪着百里弈,顾不得心痛,支支吾吾地反驳道:“这未免也太……绝情了罢?要不,先向天帝禀明这情况,看天帝如何处置,可好?”
“日后寻着品性纯良的女子,我定为你指一门上等的婚事,今日之事,我有自己的考量,你且照办!”
郎佩欲再说些什么,只是主人那眼神颇具冷冽,令他再也不敢多言半句。
“若是想保住承尧君的仙身,便随我一同回玄跻山吧。”
“奇怪,你师伯的魂魄何时进的弹虚境?”宛筝不解。
“这要请教百里弈,我对那琴不甚了解。”
“纵使我五弟未能在母胎凝成人形,却是如凡人一般有三魂七魄的,弹虚琴便是他那魂魄的容器,相当于他的肉身,世人皆不知,他的几味魂魄便是弹虚境的入口。”
“你怎以不早说!”宛筝扼腕喟然一声叹,狠狠地用目光剜了他一眼,似又怕他记仇,忙低头装作眼睛不舒服,用手指去揉。
“许是承尧嫌你啰嗦,才偷不声不响地进了禅虚境。”百里弈的唇角上扬,现出月牙儿的弧度,自从阿漓死去,他便再也没有像今天这般舒畅地微笑过了,今天不知何缘由,前所未有的温暖一阵接一阵地从脚心涌上胸膛,这种清晰的悸动像极了昔日拥抱阿漓的感觉,妙不可言。
“那青鸾鸟何时附了承尧的身?”
“一开始青鸾便隐去身形藏在了屋里,不然我与朗佩的谈话她岂能听见,后来她见我答应要为承尧君抚琴,便生出了诓我入禅虚境的心思,事情都结束了,不提了。我们出发吧,小狐狸,江寒翁即能当你师父,那么我也可以。”
他的心情似乎比刚才好了许多,步履看起来轻松了几分,江寒翁知晓弹虚琴在他手中,不能放任师伯仙身腐坏,无奈之下,只得协同宛筝跟了上去,并悄悄解了禁锢她的法术。
而郎佩不忘将一只没了气息的青鸟揣到了胸前,即便赶路,依然不时地抚摸一下,宛筝见此情景,抑郁的心情突然好了几分,朗佩胸大无比的这个样子,让她忆起了六哥初遇六嫂时的场景。
那时,她和六哥奉阿母之命去给族里一位长辈贺寿,偌大的宾客桌上就她和六嫂是女狐。
“你也是狐狸吗?怎么胸膛鼓鼓的和我们的不大一样?”
“公子,我是女狐,当然与你不一样。”
“可是我七妹也是女狐呀,你的胸比她的大好多,那个……你家是不是很穷呀?你是不是了偷了席上的肉团子揣在怀里?嗯,你不必羞愧,偷鸡摸狗的行当我和小七亦做过不少,相逢即是缘,今日我便将小七出门必带神器借与你用。
看!我阿母给小七缝制的长袜,崭新着哩,小七每次用它当布兜盛赃物,要不,把你藏的肉团子拿出来装在这里面?”……
“你笑什么?”江寒翁好奇地追问,宛筝便笑呵呵地将六哥与六嫂的趣闻讲给众人听,还不忘添油加醋描述一番。
“我六嫂拒不承认偷了肉团子,偏偏当时我六哥年少无知,一心认死理,两人竟因此事在席上扛了起来,气得我六哥竟当着众人的面撕了六嫂的上衣让众人验证,我六嫂直接给了我六哥一记耳光,然后哭哭啼啼地逃走了,从此我六哥便博了个花花公子的美名。”
小花听得稀里糊涂,未觉得有什么好笑之处,而江寒翁和百里弈二人的耳根子皆似染了霞色,绯红一片。静了半晌,百里弈清清冷冷地看了她一眼:“同男子讲这样的笑话,很失礼,到了玄跻山,不许再给灵兽讲这些。”
还未行拜师之礼、下拜师贴,他就给她定规矩,未免太欺负人了罢。宛筝气结,嘴角一歪,荡起了坏笑。
“我不给灵兽讲,那给江寒翁师父讲可以罢,来来来江寒翁师父,你且附耳过来。”
她抓着江寒翁的胳膊,不由分说将他绑至身旁。
百里弈绷着一张冷冰冰的脸瞪她,眸子似染了银白的寒霜,忌妒的锋芒一闪而过,他的脸上随即扬起温熙的笑,声音却清清凉凉:“日后若再同旁人讲这样的笑话……”
宛筝得意地以为自己的激将法即成功,哼,他不让她讲,她偏要讲,难不成他还能将自己千刀万剐了不成?最好一次就能将他惹怒,令他一气之下将她退回狐狸洞!省得她再绞尽脑汁盘算着如何整他。
“别忘了叫上我。”
?
他的回答令她大失所望,他的笑亦……让她有些不自在,愣了片刻,她才恍过神来,貌似他又开始了调戏她,呵!人不可貌相果真不假,看他衣袂胜雪,一副仙骨道风的样子,原和他六哥一样,是个色迷迷的贱种,只不过,与他不同的是,她六哥懂得怜香惜玉,而他绝情地很……哼!
要问摧花辣手哪家强,定是玄跻山那臭山长,杀人放火最在行,抽筋剥骨炼皮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