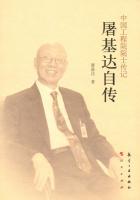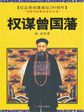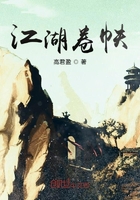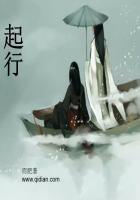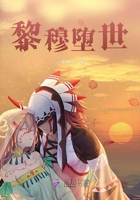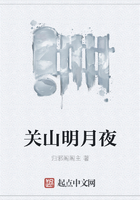四“以情求道,是以忧耳”
无数的因素推动着人的感觉、思维和行动。谁能说清,在现实给定性的向度上,具体的、个别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尽管曼殊抱定了坚心事佛之志,遁入空门,但“以情求道”注定他成不了得道的高僧……
广东蒲涧寺。
怀着逗子樱山村情殇后的深哀巨痛,曼殊悄然离开日本,绝意在此出家。
掌寺的长老正在禅房闭目诵经,他抬起眼皮瞅了一眼面前的这个面容忧戚的少年,沉缓地问道:
“你愿皈依莲座,永赞三宝否?”
“是,弟子愿随我师,参证禅理,坚心事佛!”曼殊跪拜于地,垂首作答。
“你小小年纪,缘何徒兴事佛之念哪?”长老显然对曼殊的发愿有所怀疑。
“大师,弟子自幼历经苦劫,有难言之恫。我师慈悲,至祈能收纳弟子,化被佛光,脱离茫茫苦海。”
“噢?”长老双目微启,又仔细打量了曼殊一眼,旋又闭上。
“请问,你是何方人氏哪?”
“香山人氏。”
“姓名。”
“贱名苏戬,乳名三郎。”
“父母安在否?”
“弟子自幼失怙,形同孤儿,畸零一身,托踪于茫茫天地,父母于我何有哉?”
“岂有此理!佛门弟子虽弃家修行,断却尘缘,然一点毛发体肤究为父母所赐,而你居然口出此言!这佛门本为清静之地,岂容尔等忘恩负义之辈扰乱清规?待我唤徒儿们将你赶出山门!”
闻听此言,曼殊脸色大变,“扑通”一声跪在长老座前,颤声道:“请大师容弟子细细道来!”
接着,曼殊便一字一泪地诉说了自己幼年的悲惨遭际,听得长老也有些动容了,说话的语气也平缓下来。
“你读过书吗?”
见长老怒颜稍霁,曼殊便用手撩起衣襟,擦了擦眼泪,如实地答道:
“弟子7岁在沥溪老家入乡塾,习国学。13岁随姑母去上海,拜西班牙罗弼•庄湘博士学英文,15岁去日本入大同学校就读,故弟子稍通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对梵文也略知一二。”
“噢?”长老微微颔首,又对曼殊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其实,长老一开始就看出眼前这个少年绝非凡俗之人;但他眉宇间透出的那种惨伤忧愤之气,又使长老暗暗忧叹,他深知,眼前这个尘缘未断、魔障未除的少年,不过是由愤世而离世,这是无法潜心修行的。更令长老担心的,是这个孩子那副忧深痛巨的神情,说不定是个情种胚子;这对灭情弃智的出家人来说,可是最要不得的。于是,他本着慈悲的情怀,告诫说:
“佛门乃清静无为之地,岂能收六根未净之人。你如此年纪,尚未谙世事,若仅凭一时之念,便隐遁空门,恐怕太过轻率吧?”
但曼殊此次已抱定了坚心事佛的决心,他声泪俱下地向不愿为其剃度的长老祈求道:
“大方家请勿吝此区区一席地,容我潦倒残生。不然,我将刎座前矣!”说到这里,曼殊的声调哽咽酸嘶,那刚刚揩干的眼泪又汩汩流下。
此时,长老的鼻头发酸,心底涌出一种莫名的悲悯之情,他说道:
“山门清静,你又无保人作中,本不当收容。念你身世畸零,不无可悯。可你知否,人世之荣华富贵固如云烟过眼,然亦足为六根未断者牵累。你既决意皈依空门,自当遵守寺规。从今而后,你能断尽一切欲念痴情早证佛果否?”
曼殊听罢,立即跪拜于地,俯首答道:
“弟子誓愿坚心事佛,了断尘缘,永为灵山护法。自今日起,弟子即开始闭关,以示皈依之诚!”
“善哉!我佛慈悲,本师决意收你为徒。”
长老的话刚一落音,曼殊便“咚咚咚”地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哭号道:
“我佛慈悲,我师慈悲,感谢我师不弃之恩!”
“且慢!”长老的声音透出几分威严,“你既入空门,自当与凡身断绝。本师赐尔法名曼殊,尔记住否?”
“感谢我师为赐法名,弟子已铭记于心!”
长老微微颔首,然后猛然喝道:
“知事们,准备法衣、度牒、净水、香火,为新度师弟曼殊,剃——度!”
……
自此,蒲涧寺又多了一个小沙弥。
然则,曼殊毕竟不同于那些心如止水的僧侣。一日,一位云游的和尚见曼殊心绪不宁,神色忧戚,遂问道:“披剃以来,奚为多忧生之叹耶?”
曼殊答道:“今虽出家,以情求道,是以忧耳。”
既然是“以情求道”,曼殊便注定成不了得道的高僧。皮相地看,他很沉静,少言寡语,但他的心思却似天上的浮云,常常飘动、变幻,又如穿过棱镜的光线一样光怪陆离。他的神经是异常敏感的,所以他的欢愉、愁闷、爱憎乃至对人生的感受力、领悟力,都超过常人数倍。
大概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失恋而在内心激起的轩然大波已稍稍平复;也可能是他那喜欢新奇、追求刺激的心,无法恒久地固定于一点;或者从根本上说,是无数的复杂因素推动着人的感觉、思维和行动。谁能说清一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他悄然离开了蒲涧寺,返回横滨。
在横滨大同学校毕业前夕,19岁的曼殊又考入早稻田大学高等预科中国留学生部。在此求学期间,由于曼殊在经济上仍依靠天性吝啬的表兄林紫垣的微薄供给(每月仅补助10元生活费),故只能寄居在牛込区夏本町的一间最简陋的学生公寓里,以白饭为食,甚至为省火油费,夜晚竟不燃灯。“同寓者诘之,则应曰:‘余之课本,日间已熟读,燃灯奚为?’”
然而,物质上的贫困能捆缚住心灵的自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