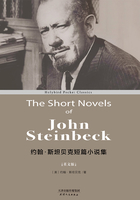烟雨阁一年一度的花魁争夺赛,怎么能少了爱凑热闹的太子爷。
这位太子爷是高兴了,澜石和向天却苦不堪言。
一个想看女色却看不了,一个不喜女色,却要陪着,两人心中都是愤慨。
只有魏埋满面春风得意,看着他们轻声道:“想换主子?”
“不敢。”两人立马一本正经的回道,不敢露出半点不满。
魏埋大笑,径直出了客栈。
向天跟在后面,敢怒不敢言。
澜石一想到魏埋那如沐春风的脸,心情就格外不好。
烟雨阁
老鸨在门口招待着各路来客。
要说平常烟雨阁就是宾客满堂,今日确是以前的近两倍,桌子椅子也要比以往多的多,不分阶级,各路人士都可进来一睹花魁之风采。
宾客分为四等,
一等即为二楼雅坐厢房,可以清晰的看到台上的所有,安静观赏,是观看花魁赛的最佳位置。烟雨阁内是镂空的天井房,内里设有阁楼两座,仅仅只有两间雅间,左右两阁楼一边一间,隔窗相望,相隔甚远,看不清楚。价格二百两一间,惊为天人,非一般人能负担的起。
二等即为台前观看,离舞台很近,也是观看的好位置,但要六人拼桌观赏,且仅有十桌,二等座仅能坐六十人,一百两一人,价格依旧如此不要脸。
三等则是在二等座后面,接近大门的位置,一人一张椅子,没有桌子,从二等座一直摆到快到门外,足足摆了三百多张椅子,场面惊人,因为三等座已经座无虚席。五十两一人也不是小数目。
四等则是三楼走廊,离舞台又远又高,仅仅只需二十两,只能站着观看。此时被围起来的三楼供观看的走廊,竟然也是站了满满的人,怕有人拥挤不慎跌落,四等座不在出售了。
不必说,太子爷自然是坐在了二楼的雅间了。
此时魏埋正一手品着酒,一边盯着楼下忙忙碌碌的人,心情颇好。
这几日没有暗卫,倒是轻松自在。
“公子,虽是没有发现刺客,但也不要掉以轻心。这里人多眼杂,只怕就隐于之间。”向天正色到。
“嗯。”魏埋随口应到,不以为然。
向天语塞,退出房间。
再度瞥向楼下,一抹白影隐于台后的帘布,怎么是个男人?
照说宾客是不能去到后院的,收回目光,看向大门,老鸨不在了。
阁内后院。
“申公子呀,你这找东西也要看时候啊,今天花魁赛,老身无暇顾及你的,真要找东西等明日再来吧。”
“花妈妈,你不知,红裳可爱的紧,与我约定偷取对方一物藏匿起来,谁先找到便答应对方一个要求,我猜我的东西定在红裳房内,我去找她便是,不会耽误。”申远说。
花妈妈正是老鸨。
“不行不行,红裳的舞蹈是第一个上台,此刻正在梳妆打扮,马上就要开始了。你这会过去,误了时间就不好了。我给你安排个位置,你等他们比完赛再去寻吧!”
申远只好应下,那东西对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样也好,有劳花妈妈费心了。”
昨日红裳给他下了迷药,但精通药理的申远随身携带各种歪门邪道和效果清奇的药物,并未着了红裳的道,给红裳下了梦春花,自己才好不容易逃了出来,到了客栈却发现去烟雨阁前与接头人取的行头画像不见了,心中暗想定是取解药时不慎把画像给弄掉了。
只好等今日前来寻,但一早过来,各个女妓都忙着准备节目,无暇顾及他,就连红裳的人影都没见到,等了一天,想着直接去后院寻人,不想这花魁赛却要开始了。
耽搁的这时间,四个座席均已满席。但这位贵客老鸨又不能怠慢,要说申远可是每天都来,一来就点头牌红裳,红裳身价一次也要个七十两,这都连着来了好几次,可是让她赚了个翻。
这也不能怪申远,他虽然不是很喜欢红裳,但她比较安静,所以只点她,却不想惹来了大麻烦。
“花妈妈,无需管我了,花魁赛比完我再来吧。”申远拱手作别。
“那可不能,花妈妈我今日就破格,不收你钱,让你坐一等雅间!”老鸨说完拉着申远往阁内走。
等下看了红裳的舞,让你欲罢不能,说不定几千两赎了她都说不定呢,摇钱树在此,怎能让他溜了,老鸨心里算计着,脸上笑容诡狭。
“我知道这雅间仅有两间,而且赛前两日便已有人定去了。哪还有雅间?”申远疑惑,难不成让我进别人雅间不成。
“是的呀。一间可是当今大斯的坨鑫王,他间内有六七人,我们不便打搅。令一间是一个阔绰的公子哥和一个闷葫芦,两人着实是孤单了点。我见他们温文尔雅,礼貌有加,和你一般都是彬彬有礼之人,定会答应的。”老鸨说完已经到了楼梯口。
申远觉得不妥,收回被老鸨拉着的手,拒绝道:“这样行不通,人家掷百两观赛,定是图个清净,我这般贸然打扰,实在不妥。”
“有何不妥,这会已经没有地方可以让你待着了,难不成你要跟她们一起上台不成?”老鸨责怪的说,又拉上申远的手。
申远依旧推脱,可老鸨的力气却大的出奇,他怎么挣都挣不开
到了门外,见到的人令申远震愕当场。
门外站着的不就是那红衣男子身后的黑衣男子吗。
老鸨见申远惊讶的表情,不以为然道:“不必惊讶,他确实长的不错,但里面那人长的更好看。”
申远连忙摆手挣脱:“花妈妈,还是算了,我等会再来,不用麻烦了。”
说完转身就要跑,他可不想见到里面那红衣男子,可还没踏出去,又被老鸨拉住了后襟。
“你这脑子怎么回事,平时的风流哪去了。今天可是一年才有一次的花魁赛,你这么喜欢红裳,还不看看她今晚的表现再走?”
申远被说的一句也答不上来,敢情他看起来就是个风流的公子哥?看来这几日在烟雨阁学的效果还不错。
老鸨拉着申远,一刻也不松开,对着门外的向天说道:“向公子,奴家有事与魏公子商议,您能否通融下。”
向天瞥了一眼老鸨又瞥了一眼申远,申远歪过头,避开向天的眼光。
“我家公子喜静,不便打扰。”淡淡的口语疏远拒绝的意思非常明显。
老鸨是什么人,经营几十年年烟雨阁的人,最不怕的就是交涉,怎么可能被这点小事屈服。
申远心中却大寒,因为听完老鸨说的话,只想挣脱老鸨的手,挖个地洞钻进去。
“魏公子,还请您通融开个门哪。您第一次来我这烟雨阁,想必不知道我们这一等雅间还有一特殊惯例,陪酒聊天哪。您一个人饮酒多没意思,知道您喜静,我这不,依着你的性子,给你找了个安静的人来陪您喝酒哩!”老鸨大喊道。
向天眼神伶俐的看向老鸨,觉她图谋不轨,这等无稽之谈也说得出口,就是陪酒也该是个女的,叫一男的过来是什么意思?
老鸨才不怕他,一双眼暧昧的盯着向天,向天撇开头,冷声道“公子怎能与这等俗人同座饮酒,还不快滚!”
申远心中腹诽,说的好像我特别想进去一样。
“向天,不得无礼,既然是雅间惯例,也别冤枉了这几百两银子,让他进来罢了。”不瘟不火的声音从雅间传出。
“公子,这样有失身份。”向天依旧挡在门口,不让半分。
“什么时候我说的话也需经你同意了。”依旧不瘟不火,语气却强烈。
老鸨眉毛微挑,对向天抛了个媚眼,看着向天让出门,趾高气扬的推开门从向天身边进了去。
“魏公子,人已带到,老身便不打扰了”说完关门退下了。
申远暗自尴尬,却不显露。
尽量保持坦荡的微笑和翩翩气度。
他折扇于胸前,走至桌前后,拱手对魏埋作揖。
“魏兄,初次见面,在下申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