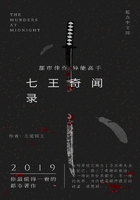“哦呀,吃汽车的丹珠么,年轻时候给畜牧局开车的丹珠嘛,哈哈,他那个死了的老婆一直骂他是个倒霉鬼丹珠。现在嘛,他是我的邻居丹珠。”
唵,嘛,呢,叭,嘧,吽。老阿妈在她耳边一遍遍念着六字真言。长途班车飞速奔驰。稀薄的空气令她困倦不堪。她不断地跌入浅浅的睡眠,每次被汽车颠醒,都会发现自己头靠在老阿妈的肩膀上。老阿妈的羊皮袍子散发着酥油、风干牛肉和藏香的味道。为了让她睡好,老阿妈一动不动。
她想:也许这就是他一直在路上寻找的温情。
你的朋友边巴茨仁是个丢失了母语而只能用汉语写作的诗人。他天性快乐、率真,才华横溢而又嗜酒如命。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诗人一样,爱做英雄梦,渴望漫游、冒险,恨不得追随一八七○年代的法国诗人兰波去非洲贩卖军火。噢,白色猎手,你马不停蹄地奔波,穿越了惊慌的草原……他朗诵着兰波的诗句,手舞足蹈,像个戴着人的面具的黑天使。同时,他又是个藏密金刚乘的奥义修持者,参禅,诵经,打坐,在大法会中受灌顶被加持,去遥远的寺院朝圣。他的身上总是洋溢着一
股慈悲的威慑力,可以慑服众多桀骜不驯的灵魂,然后劝导那些双手罪恶的人归依佛教,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让曾经操刀握枪的手持起酥油灯和印度香。
“嗨,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写诗吗?”有一天,他对你说,“我写诗是为了修行。”
冬天过去以后,封冻公路的积雪开始融化。“想不想去拉萨?”边巴茨仁问道。“当然想啦。”你说。
于是,边巴茨仁在兰州批发了五大卡车解放鞋。“我们会赚上一大笔钱的。”他说,“这笔钱唦,可以让我们在拉萨舒舒坦坦地请那些朋友喝个酒。”
你们的车队驶上通往拉萨的青藏公路。记得当时,你和他喝着一瓶白酒,唱着歌子,在驾驶室里活蹦乱跳。车过格尔木,大片的油菜花如落满霞光供一群波西米亚人裸体做爱的海子,而远处的雪峰被阳光照亮,如画室中裸女微微颤动的乳房。公路向着远方延伸。你开始唱起扎巴多吉改编的新疆维吾尔民歌。《流浪汉》原名“Sikenashka”,每一个维吾尔人都会唱。在固定的旋律中,歌者即兴编出新的歌词。在新疆,你会听到维吾尔人经常整夜整夜不停地唱着家喻户晓的《流浪汉》之歌。
我是一个嘛流浪汉呀,全国各地我都走遍我是一个嘛流浪汉呀,一生一世我走不完骑上了马儿者去西藏,坐上班车我去拉萨嘿,塞凯哪什卡,塞凯哪什卡坐上了班车我去拉萨樱桃好吃嘛树难栽,姑娘好看我口难开刺玫好看嘛手难摘,姑娘好看我挂不过来好心的姑娘看上了我,我没有工作害怕养不活嘿,塞凯哪什卡,塞凯哪什卡我没有工作害怕养不活
姑娘姑娘我爱你,弹着吉他我想着你姑娘姑娘我爱你,请个画家我画下你把你画在那吉他上,抱着吉他我抱你嘿,塞凯哪什卡,塞凯哪什卡抱着吉他我拥抱你
人说拉萨的酸奶子好,姑娘的小嘴更香甜人说拉萨的绿松石好,姑娘看起来更养眼。拉萨的小伙子爱嫉妒,我只好带着姑娘往内地跑嘿,塞凯哪什卡,塞凯哪什卡我只好带着姑娘往内地跑一到拉萨,边巴茨仁就带着你到处找朋友。你们扑向各个酒馆,和街头混混、迪厅舞女、流浪汉、黑帮老大猜拳行令称兄道弟。整整三个月,你俩没有一天是清醒的。酒场子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罗布林卡—太阳岛—雪新村—西藏大学—朵森格路。朋友换了一拨又一拨,屁股底下的羊毛毡换了一块又一块,婆娘们端上来的酥油茶换了一碗又一碗。哎呀,舒坦得很呐!等你和边巴茨仁酒醒以后,去找那五个卡车
司机,没想到那五个家伙卖光了解放鞋卷钱跑了。没钱回家,你们两人滞留在拉萨,又和朋友们连喝了三个月烂酒。觉仁波,直到你俩吐了血,你俩才发觉再这样下去非喝死在拉萨不可。于是,你俩以五瓶白酒的代价,搭上了一位甘肃酒鬼的运货卡车,在夜色中悄悄离开了拉萨。
一周后,你们在路上看到一个疯汉似的男人在招手。他瘦骨嶙峋,头发蓬乱,衣衫褴褛。如果说他不像疯子,那至少像个逃犯。你把他拉进驾驶室,看见他布满血丝的眼睛简直在喷火。边巴茨仁把白酒递给他。他咕嘟嘟灌了一口白酒,喘了口气说:
“大哥,俺是个艺术家。”一听他就是个东北人。卡车正在吃力地翻越唐古拉山口。“俺是个行为艺术家。”他说。哦嚯,牛逼极了,行为艺术家!“给我们表演一下唦。”边巴茨仁说,“我们还以为你们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哩,没想到还有行为艺术家。让我们也开开眼界唦,喏呗?”“哎呀大哥,看在你这瓶白酒的分上,俺可不想忽悠你,俺今天要搞一个伟大的行为艺术。”他脱光了衣服,冲司机喊道:“大哥,停车!停车!”
司机瞪着醉沉沉的眼睛,乐呵呵地看着行为艺术家,一踏脚刹。行为艺术家跳下卡车,开始裸奔。山风凛冽,突然而至的暴雨夹着雪粒从唐古拉山口涌了过来。卡车司机哈哈大笑着,一踩油门,开足马力,轰的一声,卡车开过了唐古拉山口。卡车顺坡疾驶,把行为艺术家远远地抛在后面。他在暴雨中裸奔,发出动物一样狂呼乱叫的声音,以为你们会把他丢在这不见人烟的鬼地方。你们哈哈大笑,在转弯的地方停下来等他。他气喘吁吁地跑来,一头栽到草地上。当晚,他就病倒了。你和边巴茨仁以及司机都感到过意不去。“可是俺不在乎死亡。”行为艺术家睁开他那双燃火的眼睛看着你们,用先知般的口吻说,“人活着毫无意义。年过三十岁的那天,俺就对自己说哩,俺已经活够了。俺经常梦想着伟大的死亡,像斯巴达战士,或者像一个革命者。这却是个庸俗的时代。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对不?这却是个流氓的时代。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对不?英雄只能像俺一样,长年漂泊在路上,梦想着死亡。
如果有一天,死神来到俺身边,俺会对他说,俺不需要床,俺需要道路和远方。俺死后,俺的坟墓将建筑在路上,那些南来北往的风就是俺的墓志铭。”长途班车重又上路了。车窗外,碧绿草原上突兀的雪峰闪耀着银光,像直插蓝天的利剑,像执命赴死的战士,要把天堂之门洞穿,再把天梯搭建,然后让厌世者在孤独峰顶手抓一缕流浪的云彩进入天堂。雪峰下的湖泊——星露海——像翡翠一样,绿而忧伤;像智者的眼睛一样,清澈而明亮。山坡上的狼毒草开花了,火焰般的花朵如野兽在金黄色的桦树叶和绿色的草丛中飞蹿。班车穿越峡谷。铅色云朵在山顶堆积,风雪瞬时凄迷,海拔上升,盘旋的公路几乎垂直,喘息的汽车在砾石中跳荡着,缓缓前行。路边巨大的岩石上用红色颜料写着四个大字:小心飞石,或者画一个大大的惊叹号,让人感觉到每个石头都会捂着嘴巴睁大眼睛发出惊讶的喊叫。大卡车从对面鸣着响号,轰隆隆压过来。班车开到悬崖边上给对方让路。她探头出去,看见悬崖下一片云霭。风雪如此凄迷。她担心,如果她稍微挪动一下屁股,班车的重心可能就会偏移,可能就会从这悬崖上滚落下去,一直掉进峡谷。
车到雀儿山顶的垭口。风雪正凄迷。经幡猎猎响。你把手中的“隆达”撒向空中,同时高叫着:“哦嚯嚯……啦嗦嗦……”接着,汽车向山下冲去。宛转,盘旋。裸露的山石,针叶林,灌木丛,鹰和秃鹫,野兔,山鹬,一一掠过。风雪渐次稀薄,海拔下降,温度升高。一家形容愁苦的人在路边用木头潦草地搭建出一个窝棚,窝棚前面的石头上写着:洗车。江永才让的新汽车现在满身尘土,蓬头垢面,像极了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扎西尼玛蹲在路边喝酒。江永才让对你说:“走吧,我们去洗个温泉浴。”
你跟着江永才让绕过窝棚边的几块巨石,跳下公路,只见两个温泉冒着热气。江永才让脱光了衣服,他的皮肤很白,他的生殖器还留着包皮。这无忧无虑的童男子跳进温泉,快活地洗起来。你也赶快脱光了衣服,跳进了温泉。温热的泉水从脚踝、小腿、大腿、胯骨、小腹、胸膛一寸寸地漫上来,渗透了肌肤和毛孔。阳光照耀着你们,不时有云朵从头顶飘过,带来一阵凉风,吹得你直打哆嗦。松树林密密匝匝地覆盖了山坡,各种鸟儿在树林里鸣唱。林中的山涧潺湲流淌,发出水击岩石的訇然声响。这是梭罗①笔下印第安人生活的国度,这是纯粹吐蕃特人的国度——用印第安人或吐蕃特人的生活方式,植物的方式,自然的方式,让人性复归,唤醒,解放,让心灵自由,把眉头的乌云驱除,忘记烦恼、忧愁和恐惧。可是你知道,人们天天在侮辱着大地,哪有资格谈论自然和天国。如果你不能成为先知,如果你不去召唤,那些愚昧昏暗①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美国作家、思想家,其主要著作《瓦尔登湖》(Walden)是他在瓦尔登湖边的林中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生活和思想记录。
的灵魂怎能获得解脱和拯救?别充当穷人的先知,而是要勤奋,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瓦尔登湖边的梭罗隐士如是说。此刻,你和江永才让多么像两个穷人的先知,站在阳光下,赤身裸体,肌肤闪烁着水珠的光芒,面朝山麓上茂密的树林和奔逐的鸟兽,沉思着,想像着,祈祷着。让那些困厄于都市的囚徒获得解放吧,他们的一生从来就没有亲近过伟大的自然和信仰,他们的心灵蒙覆着厚厚的尘埃,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如果真有一位天使降临,他们也绝对不会相信。
顺着河流的方向,雀儿山下,公路两边是壁立万仞的山峰。顺着河流的方向,便是德格,你此次旅行的终点,你人生的第二故乡。一个人,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验灵魂的强度和载力。一想到将要在这里居住并生活整整一年,你的心情便不由自主地激动起来。这是游牧族的生活,大隐士的生活。如果寒山①有灵,他必会引你为知己。他会穿越千年的时光从唐朝到来,和你对酒悠游,吟风弄月。你们会在秋天飘摇的树叶上写下千年流传的诗歌,你们会把诗稿付之一炬,让纯粹的火焰成为诗歌的读者。吾家好隐沦,居处绝嚣尘。践草成三径,瞻云作四邻。助歌声有鸟,问法语无人。今日娑婆树,几年为一春。寒山当年如是说。
德格县城到了。河岸边的山坡上赭红色的木头房子鳞次栉比。她漫步街头。色曲河在新兴的水泥建筑下哗哗作响,向着远方奔去。简陋的店铺。肮脏的牧民。长发上缠着红色英雄结的男子腰里插着银柄长刀。牧人的妻女头裹绿松石和红珊瑚,佩金带银。西装革履的小官吏走起路
①寒山,乃唐代长安人,出生于官宦人家,多次投考不第,被迫出家,三十岁后隐居于浙东天台山,享年一百多岁。寒山诗作在二十世纪受到了中国及西方众多读者和研究者的关注。
来又土又神气。狭长的街道上塞满了蔬菜小贩、屠夫、马匹、卡车、拖拉机……网吧里玩游戏的僧侣进进出出。桌球室里好勇斗狠的少年随时准备打架斗殴。发廊里涂脂抹粉的妓女穿着廉价皮裙倚在门框边嗑瓜子。兽皮贩子的粗手抚摸着一张豹皮。珠宝商把手伸进彼此的袖筒里掐着指头讨价还价。幼儿园的儿童学唱着走调的国歌。文工团的男女演员打情骂俏争风吃醋。更庆寺①佛学院的百名僧侣在山坡下的草地上辩经。围绕印经院转经的群众被一场暴雨驱散。雨来得很猛。顷刻之间,街道上变得空无一人。她躲在首饰店的屋檐下,看着五只放生的绵羊四处游荡。一个疯子,像来自天堂的预言者,在雨中呼喊:末日来临,光欲熄灭。
等那只觅食的乌鸦从树林里飞到垃圾堆上开始觅食的时候,雨停了。一个穿着旧式军绿色警服腮帮子上翘着两撇小胡子的老酒鬼,哼着歌儿从酒馆里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酒鬼丹珠!”调皮捣蛋的孩子们跟在他身后,使劲起哄,“嗨,酒鬼丹珠,你的手枪丢了,当不成警察了。”
他转过身想要追打那帮小孩,不小心一个趔趄,栽躺在街上。孩子们嘻嘻哈哈地一哄而散。他挣扎着想要站起来,却发现没有一丝力气,索性就躺在大街上指着那群孩子叫骂起来:
“哎,没奶吃的羊羔子,老子我当警察的时候,一枪子儿就能崩掉你那根尕鸡巴。老子我,我手枪没丢,我藏起来了,我就是为了把你那尕鸡巴一枪子儿崩掉才藏起来的。唔,我藏哪儿了?我藏在鱼肚子里了。哼,局长开除我,我不怕,我把手枪藏在鱼肚子里了。我一枪就崩掉他的个尕鸡巴……”
①更庆寺:四川康区藏传佛教萨迦派主寺,位于德格县更庆镇。更庆,藏语意为“宏大”。“啊,你这个造孽的人,都喝成这个样子了,还腰里别个死老鼠,
冒充枪手哩么。”老阿妈感叹了一句,急急忙忙从屋檐下钻出来,跑到老酒鬼跟前。
“哎唷,扎西青措,我的尕母马,你回来了嘛?”老酒鬼醉眼蒙胧地瞅着老阿妈说。
她和老阿妈搀扶着酒鬼丹珠,来到一处山坡下。老阿妈的家是一座在公路边依山而建的二层小木楼。她家的对面,紧靠着色曲河,也是一座二层小木楼。小木楼的阳台上摆着一盆石榴树,一个老人坐在躺椅上,一边拨弄着阳台边的四个方向盘,一边晒着太阳。
“吃汽车的丹珠,吃汽车的丹珠,”老阿妈冲那位老人喊道,“这个姑娘来找你。”
“扎西青措,你别骗人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