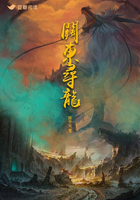后半夜,我被冻醒了,从窗口望出去,镀了一层乳白色月光的街道、屋顶、远处小尖顶的教堂,就像童话世界一样虚幻。我走到安娜的床前。她捧着那本翻开一半的暗红色封面的《圣经》,蜷身侧睡着。漫爬的月光映射下,她的脸如婴儿般恬静,眼角还有浅浅的泪痕。我俯身看着她,心底里忧伤而又疼痛,还有种不知所来的幸福感。我的目光落到了她敞开的睡衣下露出的半个乳房上,突然像被火灼了一下似的。我把唇轻轻地落了上去,她抱着《圣经》的手松开了,《圣经》啪嗒一声落到了床下。她咕哝了一句什么,又侧身向里睡着了。
我想起了那些难以启齿的梦,觉得自己真是荒唐无比、罪恶无比。为了让发烫的身体冷却下来,我掀开被子躺着,让窗口涌进的月光和冷风使我平静下来。这一夜终于在不安与内疚中过去了。早上起来,安娜看到我那张被痛苦扭得变形了的脸,心疼得叫了起来:“你看看你,都冻成什么样子了啊!是不是昨夜梦见赫伯特了一夜没睡?”
我更加无地自容。我催着安娜离开,今夜就不要陪我了,我能照顾好自己。说真的,我是怕身体里的那个恶魔吞噬我,也吞噬了她。我的提议遭到了安娜的坚决反对,她说她已经失去了一个弟弟,再也不能对我撒手不管。我无助地哭泣起来。她把我的头搂在怀里安慰我,她的气息让我晕眩。这一夜我一直听着安娜那边的动静。她翻书的声音,她的叹息。吹熄烛光后,她渐渐弥漫开来的呼吸,又让我抑制不住冲动。我憎恨自己,使劲拧着脸,疼痛也不能浇熄我的冲动。迷迷糊糊中,我想像着赫伯特的灵魂正在屋内逡巡着,正冷冷地看着我。夜里起了风,雨突然下大了。我哆嗦着身子起来关窗,一转身,看到安娜不知何时已经起来,站到了我身后。我突然紧紧抱住了她。
她怜惜地让我躺在她的床上,轻抚我发烫的脸。她以为这样能让我尽快从伤痛中走出来。看到她坐在床边冷得哆嗦,我让她也钻进来。她犹豫了一下,先伸进来一只脚。我一把扯过被子,把她整个身子都盖起来。直到这一刻,她还是我的姐姐。当我的手隔着棉布睡衣握住她的乳房,她才惊惧而愤怒地喊了一声,像坐在一块烙铁上一般跳了起来。我闭起眼睛,等待着她疾风骤雨般的责骂,等待着她甩下来一个耳光或者朝我吐唾沫。可是没有。她拿过床头的《圣经》,飞快地翻到有折角的那一页,写着阿麦农占有他妹妹的那一页,问是不是我折的。我承认我这么做是为了让她看到。
她低低地叹息了一声。我听到了她身体里堤坝坍塌的轰鸣声。“傻弟弟,这不是你可以做的。”无边无际的潮湿裹住了我,我如同陷身于夏天的沼泽地,无力挣脱,又自甘沉沦。在最后沉没前,我喃喃地说,我就是死了,也还是爱你。早晨醒来,安娜已经走了。她带走了那本《圣经》,还有赫伯特的画。如果不是落在枕边的几缕她的头发和湿湿的泪痕,我真要怀疑昨夜是不是做了一个梦,一个难以启齿的梦。
这些年的浪荡行径,让我浑浑噩噩不知敬畏为何物。我只是觉得没脸再去见安娜。这些年我确是劣迹斑斑,但我从没想过要把耻辱带给她。我小心翼翼地在内心供奉着她,就像供奉一尊女神。我希望自己混得有出息,出人头地,而不是像父亲为我安排的,成为一个呢绒商人、杂货店伙计或者下三烂的水手。我做梦都想着带给她更多的荣耀,却没想到对她犯下了连上帝都不会原谅的罪孽。
是赫伯特的死,让我们在悲伤中相互取暖。尔后,魔鬼的引诱让我越过身体的边境线,失足滑下了万劫不复的悬崖。我这是在推诿责任吗?赫伯特已经死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在北极滑落的冰川吞没他身体前的一瞬。那张冻得像青石一般的脸,不再是他,而是死亡通过他的躯体呈现的一个形象。他当然不会再来指责我。压弯我们的总是自身灵魂的重量。
我一刻也不能在伦敦待下去了,那些雾蒙蒙的街角、房子、走过的路,勾
起的全是耻辱的回忆。我的余生怕是再也走不出这一夜带给我的耻辱了。我发誓不再见安娜,不再打扰她,我在内心请求她的原谅。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我。我不知道我是谁,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要远远地离开。对生活我已不再有什么期待,我相信自己会像曾经卑微地生活过的那样走向死亡。一个念头越来越强大,直至整个地充塞在我心里:去中国!去找我的母亲。只有找到了她,我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是多余的。
我来到威斯敏斯特区老皇后街的那幢老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写着大清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一个门房再三盘问之后,把我领到了金登干面前。当年,那个被我称作父亲的男人带我们来英国,寄养在戴维森太太家,是他一手操办的。我希望从他这里打听到一些母亲的线索。
我已好长时间没有见过金登干了。一见面,他就拖着那条瘸腿上来热情地拥抱了我。他显得老多了,比我矮了整整一头。他一边问我安娜和赫伯特怎样了,是不是一切都好,一边又数落我们在职业选择上不应该违背父亲的意愿,致使回到伦敦后再也收不到北京一个子儿的接济。
“去印度做一个殖民地文官,或者士兵,有什么不好?就算哪儿也不去,在这里开一家小杂货铺子,也比你这样子要强得多……”我不客气地打断他的絮叨,告诉他,安娜嫁人了,赫伯特死了,我决定离
开英国,去中国找我母亲。
“去中国?”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这事我要征询你父亲的意见。”
“他已经把我们的舌头压制了二十多年,他打算要压制一辈子吗?”我气愤地叫了起来,“我有权自行决定去这世上的任何一个地方,他管不着。”
“可是,你母亲在你出生的那年就已经死了呀。”
“不!这只不过是你的上司总税务司大人骗人的鬼话,我与她有心灵感应,我能感觉到,她还活着。你见过我母亲年轻的时候吗?”
“我没见过,但我见过她和你父亲的合影,她是个迷人的东方女性。那年你们三个到英国来的时候,我是听你父亲说的,你们的母亲在上海因产后出血去世了。”
我冷笑道:“他当然巴不得我母亲早一点死,他好早一点迎娶新娘。”
“你就这么恨他?”
“是的,我恨他。”
“你这么说或许有你的道理,但你也应该知道,他一直操心着你们三个的生活、教育、职业,替你们找抚养家庭,送你们去读书。我在这里经管着他的几个账户,其中的Z账户,就是专门为你们设立,开支你们的生活和教育费用的。从法律意义上说,他完全可以不管你们几个非婚生的子女,但他把你们带到了英国,托人照管你们,让你们受教育,他是我见过的最有责任心的绅士。”
“见他鬼的绅士吧!这样的绅士我现在只想狠狠踢他的裤裆。”我恶狠狠的语气让金登干吃惊不小,这让我于心不忍。他是个好人。“我来是想请您告诉我,去了中国我怎样才能找到母亲。您是我父亲多年的亲信,应该会告诉我一些有用的线索吧。”
金登干说:“我很高兴你已经长大成人,对事物有了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好多事我也不会再瞒你。如果你有兴趣,我给你说说我在你父亲领导下在海关工作的经历,也好让你更全面地了解他。”
“好吧,好吧,我听着。”
金登干说:“我是1860年跟着李泰国去中国的,那时李泰国是大清海关的总税务司。他回国度假期间,受清政府委托在欧洲购买了一支小舰队。我厌倦了在财政部做一个小职员,向往去外面的世界闯荡,就跟着这支小舰队去了中国。我和你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那时你父亲是江海关税务司,李泰国赴欧期间代理总税务司职务。由于李泰国性格上的缺陷,他过于自以为是,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再加上中国人看穿了他想把舰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野心,中国方面拒绝接收这些舰艇。李泰国失去信任,丢了总税务司的官,你父亲接替了他。小舰队遣散回国途经上海,你父亲又找我谈了一次话,他希望我继续为海关做事。在伦敦帮助李泰国处理出售遣返舰艇时,我被钢锭压伤了一条腿。后来伤腿痊愈,却成了一个瘸子。在我养伤期间,你父亲没有按照海关常规减少工资,还是全数发给我,这让我又不安又感激。于是1866年春天他回国度假时,我跑前跑后服侍得特别殷勤。没错,你们三个就是在那时候来到英国的,我帮他联系了戴维森先生一家把你们寄养了过去。因为你父亲如此器重我,这年9月他结束度假返回中国时,我也随同前往了。
“是的,那年秋天他去中国时还带上了新婚妻子,对此我不便作任何评判。到了北京,我被任命为总税务司署稽核账目税务司。你父亲任命我这个重要的职位,足见他对我的信任。为了尽快掌握中文以便与中国人打交道,你父亲还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朋友丁韪良牧师学习中文。几年后我回国结婚,同时为你父亲的一桩官司奔走。官司拖了几年终于胜诉了。你父亲好几次催促我返回中国,但我妻子艾伦不喜欢去中国,再说我们已有了好几个孩子,于是我就留下了。海关在伦敦的代理机构一直是一名商人做代理人,你父亲一直有意改组这个机构,于公于私,我都希望这个机构由我来掌握。到了1874年,正式成立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时,我就被任命为办事处主任了。我的公开任务是为帝国海关采购各种物资和用品,招考雇员,还有一个更机密的任务是搜集和传递情报,当然我还担负着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为我的主人——也就是你父亲购买衣物、书籍、食品,经管财产,经营证券投资。是的,我不仅仅是一个海关雇员,还是一个情报官,是他在欧洲的耳目,一个忠诚的仆人和管家。我们约
定,除了紧急事情电报联络,每周五,我必须写信给他汇报此间的消息。他回信吩咐我做这做那,谈北京政坛的消息,向我倾诉烦恼。这样的通信,二十来年我们从未间断。这么多年来,他一家子在北京的一应物件差不多都是我寄去的,香皂、芥末、球形蓝颜料、胡椒、无核小葡萄干、木莓果酱、草莓酱、橘子酱、黑皮鞋油、香草香精、柠檬香精、苦杏仁香精、腌鲱鱼、荷兰防风草、艾伯奈色夹心饼干、扫烟囱用具、骑马装、礼服、靴子、帽子和手套,等等,我还为他寄过香槟酒、乐谱、流行小说、小提琴、竖笛、兔子、鸽子和珍珠鸡,我寄去的乐器,差不多可以装备一个交响乐团了。我差一点就把伦敦的百货公司搬到北京了……”
金登干津津乐道于这些对东方世界而言的舶来品,有些跑题了。看出我的不耐烦,他又把话题扯了回去:
“我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办公室里总是宾客满堂,既有汇报工作的下属,也有各国的来访者,帝国政坛的要员。他的会客计划总是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他的生活却是孤独的。他会定期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阅读从伦敦寄来的一些流行小说,他还托我买过好多把小提琴,他一直是个不错的小提琴手,偶尔也参加一些业余的戏剧表演。这几年我还听说他在北京搞了一支铜管乐队。这完全是一个绅士高雅的兴趣和爱好。而且我认为,他不断扩大在社交上的影响力,说到底还是为了他的海关。除此之外,好像再没有别的能吸引他。他从不参加俱乐部活动,也从来不是竞技活动和其他一些项目的爱好者。一些从北京回来的人,偶尔也会说起总税务司的绯闻,说他有无数宠友,但事实证明那都是无根的传说,是对他名誉的恶意中伤。
“他谨慎圆通,又不锋芒毕露,一旦认准的事,他就不会回头。每次走进他的办公室,即便是老资格的税务司也会感到不安,甚至害怕。他锋利的目光,他斯巴达式的朴素生活方式,他钟表一般严谨的思路,都会让你感到压力。就我来说,宁愿给他写长篇书信,也不愿面对他那炯炯的目光。但办公室之外,他又是个多么令人喜爱的人,慷慨大方,像一个艺术家一样感情丰富。你很难想像,他最大的快乐不是别的,竟然是为他的朋友和下属的孩子们准备生日礼物!当他像一个圣诞老人一样出现在孩子们的生日宴会上为他们派送礼物时,他是多么的快乐!那些孩子是多么喜欢他。就连我的孩子们,见过他一面后也都迷上了他。
“所有事实表明,他是个有着巨大能量的人,顽强、机灵、有商业才能,勤勉,廉洁。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经常工作到深夜,事无巨细,必躬亲焉,决不容忍自己的雇员有任何废话。据说北京的外国人圈子里流传着赫德先生是这样的一种性格:刻苦、谨慎,含蓄得甚至有些内向,并且从小就不喜欢体育运动。他们开玩笑说,这几乎就是一个十九世纪中国士大夫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