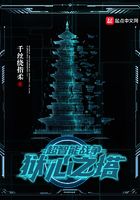黑夜里陈千岁凭着那双异于常人的双眼,看见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出现在眼前。满脸横肉,油光满面,五官被挤得几乎看不见了,嘴唇上涂满了粉紫色的口红。这正是被神志不清的陈千岁无意一推,推得个身首分离的毗蓝婆。
她的头飘飘悠悠的悬浮在空中。此时正与回头的陈千岁撞了个满眼。她的双眼无神,晶体混浊,倒真像是被陈千岁掐死的那两只司晨天鸡的眼睛。正是如此,陈千岁只觉双腿发软,身上一丝力气也没了,喉咙里不自觉的发出“赫赫”得气流滑动的声音,双眼死死的盯着毗蓝婆的脸。是她在哭吗,是她把我引过来要报仇吗?陈千岁不错眼珠的看着她。她却没有任何动作,脑袋上下摆动一会,慢悠悠的向着右侧走廊飘去。这时陈千岁的才看明白。毗蓝婆根本没有身子,只有一个头漂浮在空中。
赶紧跑吧!陈千岁心里脑子里就只有这一个想法。赶紧跑。可是腿实在不听使唤,扶着楼梯慢慢的向下蹭。刚下去没几个台阶,就听见一楼传来脚步声,还有两个男人在低声私语,像是什么事情谈不拢似的,在一楼争持了起来。有人来了!陈千岁差点没哭出来,这哪是人啊,就是天神下凡。他想喊两声救命,但是喉咙好像抽筋了,根本就发不出声音。便只能咬着牙一步一步的向下蹭。好在听脚步声,两人也从楼梯上二楼了。
听脚步声是离陈千岁越来越近,不知怎么,忽然又停了下来,只听其中一个男人说道:“老陈,一会儿上去了我可什么话都没有啊。”另一个男人脚步一顿,有些愠怒,压低了声音说道:“你怎么又反悔了,什么叫做一句话没有,刚才不是说的好好的。”刚才没哭出来的陈千岁此时终于哭了出来,妈妈,我想我的妈妈。
悔恨的泪水流满了陈千岁的脸颊,来的不是别人,正是陈掌门和李堂主。陈千岁听出二人的声音,真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闲着没事自己作死,跑到这龙潭虎穴来。楼上有冤魂索命,楼下有杀人不眨眼的死敌。这一小段楼梯,是上也不得,下也不得。这可怎么办。此时楼上又传来了一个女人悉悉索索的说话声,离得远,陈千岁听不大真切,楼下的陈掌门和李堂主的谈话,陈千岁却听得清清楚楚。李堂主有些心虚,嗫嗫道:“我我我没料到她也来了,好家伙,我腿都软了,现在合计地好好地,就怕一会儿一害怕什么该说的不该说的就都秃噜出来了”。陈掌门显然是急了,压低的声音藏不住的怒火:“你他妈糟蹋女人的时候,怎么不软呢你,废物点心!我告诉你,一会儿给我把持住了,那小子的事你要是说出去,咱两个都得死,而且死的很难看”。说完,两人又开始向上走。陈千岁无法,只能硬着头皮又返了回去,就在手电光照到二楼的那一刹那,陈千岁闪身进了右手边的那一间屋子。
屋子里很黑,唯一能将月亮透进来的窗户用几块木板封住,只有几缕惨淡的月光从木板与木板之间的缝隙里挤了进来。陈千岁倚在墙角,大气也不敢喘的听着外面的动静。
两人来到二楼拿着手电左右照了照,李堂主干咳了两声,陈千岁耳朵里那女人悉悉索索的说话声便消失了,一会儿,传来一个苍老的女人声音,有点像公交车上叫人让座的老大妈。“这边来”。陈掌门和李堂主对视一眼,向着走廊尽头的房间走去。
陈千岁终于是松了一口气,浑身无力的倚在墙角,屋里很黑,但陈千岁能看到,就在他转过头的一刹那,猛然间发觉这屋子里并不只有他一个人!
“青衣奶奶。”陈掌门和李堂主两人恭敬地叫道。房间里背对着他们坐着一个身着碎花棉袄的身影,不用细看便知道是商场里老年人精品专区新年特供——牡丹花开,大富大贵喜庆棉袄。头上一头花白的头发很精致的在后面挽成一个老式发髻,上面簪了一朵百花一朵红花。此时正低着头不知道在干什么。陈掌门和李堂主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叫了声青衣奶奶。“把手电关了吧,怪费电的”。说完指了指墙上,手电照去,墙上有一个开关,原先应该是白色的,此时上面挂满了一层厚厚的污垢,看的直叫人恶心。“吧嗒”一声,屋顶一颗小小的黄色灯泡闪了两闪,亮起了昏黄色的光。这时陈掌门和李堂主才看清楚,屋里堆着一些不知从那里捡来的破烂,一张烂桌子上放着几个酒瓶子和脏的叫人恶心得碗筷。房间另一侧的地上有衣服铺盖卷,铺盖卷上本应该是流浪汉的位置,此时却躺着一个男人,约么四十岁上下的样子,体格精壮,衣着虽不名贵,倒也干净利落。紧闭双眼,不知是死是活。青衣奶奶坐在椅子上端坐在房间正中。
陈掌门看了李堂主一眼,像是警告他不要多说话。“青衣奶奶,不世僧与饕餮女具是被烧死在车厢上,车厢里其他人的尸体也烧得一干二净,已经有人去打理了”。“无敌刀的下落问出来了吗。”青衣奶奶问道,陈掌门摇摇头,反应过来她是背对着自己看不见,忙开口道:“没有。”“废物!”青衣奶奶厉声喝道。“简直是废物,当初告诉你们不要轻举妄动,等我赶来,偏偏不听。不世僧几个死也就死了,不值什么,只是饕餮女一死,这无敌刀的下落便再也无人知晓了,愚蠢,愚蠢呐!”说着便痛心疾首的捶着自己大腿。“青衣奶奶别着急,弟子听到饕餮女无意中提起过无寿道长,或许他知道些个中隐情呢。”陈掌门说道,说完一杵李堂主,“哦对对,我也想起来了,像是听饕餮女说起过一嘴”。“哦,那个老不死的杂毛会知道。”青衣奶奶像是来了兴趣,“说说怎么回事。”陈掌门将火车上的事情连删带减,半真半假的说了出来,将陈千岁的存在完全抹去,更将此次行动失败的原因全部推到了不世僧的头上。
陈千岁紧紧地贴着墙角站着,随着时间推移,心跳慢慢的恢复正常,刚刚进来的时候,差点没背过气去。他发觉这间屋子里并不只有他一个人。准确的说算上他是有三个半人,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小男孩和一颗头颅。这个女人和小孩他不认识,但这颗人头陈千岁还是很熟悉的,正是在火车上,被他一掌拍飞,刚刚又漂浮在空中将陈千岁吓得半死的毗蓝婆的人头,此时正在屋子的正中央,和陈千岁眼对眼,来了个心灵与心灵上的交流。陈千岁这一天经历的太多了,此时的场景让他很快的镇定了下来。因为紧靠在墙角的陈千岁清楚地看到那个女人和小孩也是各自占据一个墙角,身体紧紧地贴着墙壁,好似很忌惮陈千岁的到来。
陈千岁此时的境地很是微妙。
他和一个女人,一个小孩,一颗人头各占一角,奇妙的组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格局。三人一头都不停的打量着对方,或是惊惧,或是好奇,或是着急。但都都没有一个敢出声,也没有一个敢动一下。
他的眼睛看得真切,与他相对的那个墙角站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正是狗不吃的年纪,看到这么大的熊孩子,陈千岁就头疼了。此时他到没有一丝惧意,乖乖的站在那,抿着嘴,忍着笑,像是做什么游戏似的。这哪来这么个熊孩子,穿着一件宽宽大大的羽绒服,把膝盖都遮住了,眼睛上挂着一副大大的眼睛,足有啤酒瓶子那么厚,许是冻得,鼻子上还挂着两行清鼻涕,一抽一抽的。就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孩子,却叫陈千岁汗毛倒竖,脊梁骨发寒。不为别的,正是这个小孩子手上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竹竿的那头用红色塑料绳吊着一个东西,黑乎乎的,像是个不亮的的灯笼,又像是个南瓜,但陈千岁的眼不同已往,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是一颗人头!毗蓝婆的头,红色塑料绳拴着她的头发,像是一条大鱼一样,被这个小孩拿在手里一挑一挑的当做玩具。陈千岁这才明白,他为何刚刚看到毗蓝婆漂的头会漂浮在空中了。
陈千岁不再看那个小孩和吊在屋子正中央的人头,一进门的墙角处站着一个女人。好似受过专业训练似的,后背倚着墙角,持枪对准陈千岁。她以为这屋子黑咕隆咚的大家都看不清呢,她手里哪有枪,两根手指并拢,唬鬼呢。
此时三人各怀心思,都不出声。陈千岁便趁此机会细细打量起面前的这个女人来。这女人像是察觉到了陈千岁在看他,更紧张了,身体紧绷的像拉满的弓弦,稍微一碰就断。其实陈千岁没有恶意,他不停的打量这个女人,属实是因为她漂亮。理由就是这么粗俗而直白,因为漂亮。美好的东西谁不想多看上两眼。齐耳的短发向后梳成一个小辫,零零散散的碎发,随意地荡在耳边,正是这几缕碎发,越发显得她的脖颈细长白嫩,身上衣着简单利落,虽是冬装,丝毫没有臃肿的感觉,配上一双马靴,倒真有些英姿飒爽的感觉。陈千岁知道女人看不见他,目光有些直白,唇角也向上微微挑起。“小哥哥,你为什么看着这个姐姐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