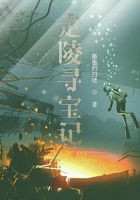建康城。
桓道芝的马车缓缓驶入城门。云秀抱着熟睡的孩子坐在车上,脸上都是悲苦哀怨的神色。桓道芝脱下了铠甲,换上一身帅气的男装,白了她一眼,真不知道刘裕喜欢这女子哪一点。走了一路,哭了一路,离了丈夫,活不了吗?
桓道芝到底出身高贵,涵养很好,心里那么想,话说得却漂亮,“嫂夫人,不要伤感了,现在进建康了,马上就到谯王府了。平西将军会照顾你的。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以后要自己坚强些。”
云秀道谢,还是很哀怨,“多谢小姐相助。”
“嫂夫人,恕我多言,刘兄把你们母子托付给平西将军,你就在谯王府上好好住一阵,不要总想回句章或是京口,否则,你既是让平西将军为难,也让刘兄无法安心作战,战场上,最忌分心。”
云秀听着,担心刘裕,眼里又满是泪水,她扭过头去把眼泪擦了。
桓道芝说,“另外,不要对别人说,是我送你来的。我不想让人知道行踪。”
“好。”云秀答应了。一路上总见桓道芝与随从密谈,沿途又不断有人来找她,帮她换马换车,车上装满了财物,看来是有什么大事。
随从在车外说,“小姐,谯王府快到了,转过街口就是。”
桓道芝便命马车停下,对云秀说:“嫂夫人,我答应刘兄送你到谯王府,现在到了,你自去吧,恕我不能再送了。”
“好,这一路上多谢照顾。”云秀道了谢,背上包袱,抱起孩子下车。
桓道芝便带人走了。
云秀转过街角,果然见一座庄严宏大的府邸,大门紧闭,门上挂着匾额,写着“谯王府”三个字,这就是目的地了。她抱着孩子,朝那府门走去,还没走到台阶下,守门的几个人向云秀喝道:“站住!哪来的妇人!还敢闯王府!”
云秀向那些人深深一拜,“诸位好,我丈夫是北府军副将刘裕,有书信给平西将军。我哥哥戚大富也在贵府里当差,麻烦您帮我通禀一声,我求见平西将军。”
守门的人们看她长得漂亮,全都站起来,互相看着笑。不等众人说话,其中一个人抢先走到她面前,说道:“戚大富的妹子怎么了?一个副将的家眷,我家世子也是你相见就见的?世子不在。”他一开口,其他人就不便再说话,只好坐了下去。
“那我哥哥呢?”
“你哥哥也不在,都在城外军营呢!你出城去找吧。”
“那军营怎么走?”
“就在城南,自己去找吧!”
云秀没想到会被拒之门外,只好抱着孩子茫然无措地走了。她刚转过街角,就见刚才说话那人追了上来,“小娘子,留步呀。”
云秀回身看着他。
那人笑道:“你不知道,王府的规矩,看门的不能擅离职守。我刚刚当差也是没办法。现在我不当值了,就有空了。你不是要找世子吗?我帮你呀!”
“多谢了。”云秀向他行礼。
“小娘子,你丈夫呢?”
云秀想到刘裕,心里难过。“他在打仗。”
那人搓着手,嘿嘿地笑道:“哦,那可是凶多吉少。你说你一个女人还带着孩子,真是可怜,你那哥哥也不是疼人的。依我看,你还找什么世子呀!不如,”他笑了笑,低声说,“这条街往北,有一个小院,我在那儿落脚。你来跟我过吧。”
云秀后退几步,怒斥他:“放肆!”孩子醒了,哇的大哭,云秀抱着孩子快步走了,头也不回。
背后传来那人喊声,“爷我好心好意,想给你个活命的机会。你别不识好歹。那军营远着呢。就你这样的,路上就得被人欺负死,不信,不信你就走一圈试试!”
孩子饿了,一直哭,云秀抱着孩子在一个墙角坐下,从包袱里掏出一块干粮给孩子吃了,又去拍一户人家的门,要了一碗水,让孩子喝了,千恩万谢地还了人家的碗,然后抱着孩子继续赶路。
这条路果然不好走,人来人往,只有两三条大街上还算兴旺,地面干净,店铺都开着门,可一到偏僻的街角巷尾,就总能遇上一群群乞丐流民。云秀的包袱被人明目张胆地抢走了,她想去要回来,却见歹徒凶恶地瞪她,她害怕,忙抱着孩子跑开。又过一个街口,竟有妓院的老鸨地痞想抢她,她拔下头上的簪子,跟他们拼命,连连大叫救命,正好有些巡街的衙役路过,那些人才跑了。
云秀生怕再遇上流氓无赖,便把头发弄乱,脸上抹了好多灰土。好不容易到了城门,却是一阵滚雷,霎时下起了大雨,天气更加湿冷难耐。许多人纷纷地从城外往里跑,说是外面要发洪水,乱哄哄。云秀弓着身子,给孩子遮雨,慌忙跑进城门下避雨。幸而城墙很厚,城门像一个穹顶,聚集了不少躲雨的人。云秀向人家打听平西将军的军营有多远,怎么走。人们都说不清楚,有的说在城南十里,有的说在城北五里,有的说城南城北的大营已经撤了,将军在城外只是练兵,不是扎营。还有的人问她城西也有军营,她到底找哪个营盘。
守城的兵往外赶人,“要出就出,要进就进,别在城门内逗留!”将一些百姓又都赶进了大雨。云秀抱着孩子,赶紧又找了一个屋檐躲雨。
大雨倾盆一般下着,军营还在城外不知道哪里。
孩子刚刚这一路受了惊,又淋了雨,着了凉,难受得一个劲儿直哭,云秀的心都碎了,不找大营了,四处问人医馆。这时,雨渐渐小了,她不再等了,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弓着身子给孩子挡雨,自己冒雨深一脚浅一脚地连找了几家,大夫们看她这穷苦的样子,就不肯给孩子治病,还把她往门外赶,直说晦气。
云秀抱着孩子一边哄着,一边哭,建康城这么大,她不知道能去哪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谯王府,哪怕守门的人不给她通禀,不让她进门,她总能等到司马休之回府吧。
云秀想好了,就抱着孩子往谯王府走。她已经走了一天,连饭都没吃上一口,水都没喝一口,已经很疲惫。但她没有办法停下来,只能拖着疲惫的身躯,往谯王府去,那是她现在唯一的希望。
冷不丁有个饥民追着她走,那人已经饿了几天,眼眶深陷,面如菜色,手伸出来就像骷髅骨架,有气无力地对她说:“你这孩子病了,没药给他吃,他活不了。不如大人吃了他,还能得条命。你下不了手,我帮你。咱们一起吃。”说着,就要抢她的孩子。
“滚开!”
云秀吓得发疯似的大叫,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用手和腿拼命地踢打那人。那人终是饿得虚脱,挨了云秀几脚,摔在地上。
云秀抱起孩子就跑,那人挣扎着爬起来,在后面紧追。云秀抱着孩子逃命,大喊“救命”。那人始终跟着,就像无常索命似的紧追不放。云秀边跑边回头看,跑出街口,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
她被那人反推了一把,抱着孩子摔倒,后面那饥民跟上来,一把抓住孩子就要抱走,云秀使出全身力气,死死地拽住自己的孩子,大喊:“放手!放手!救命啊!”
正抢夺间,几个人围了上来,那饥民一看,见都是当兵的,犹豫了片刻,撒了手,一溜烟跑了。
云秀坐在地上,抱着孩子放声大哭。
当兵的人赶跑了饥民,回头呵斥她:“快让开,你挡了我家将军的路。”
云秀回头看时,见身后是一辆油壁车,青色车身,朱红的车轮,挂着油皮灯笼,写着“平西”,刚才正在行进途中,被那饥民和云秀截停了。
云秀燃起了一线希望,抱着孩子从地上爬起来,问:“请问,是平西将军吗?”
当兵的人便是休之的随从,横着佩刀把她推开,招手让车辆继续前行。
云秀拼命地往大车旁边挤,向车内大声哭喊:“平西将军!司马使君!我是京口刘裕的妻子,我是戚云秀,将军救我!”
马车停了下来,车窗帘子掀起,车里的人果然是司马休之。
戚大富在马车后面的随从队伍里,听到云秀的叫声,把在他前面的人往两边一扒拉,三两步跑了过来,边跑边叫云秀的名字,同时把自己身上的斗笠蓑衣解下,披在云秀身上。见妹妹和外甥这副可怜的模样,戚大富心疼得直掉眼泪。
司马休之没想到云秀会在此时此地出现,又是这般可怜,他愣了片刻,忙让戚大富扶云秀抱孩子上了自己的马车,戚大富本不敢上车,可妹妹也不便一个人在休之车上,便也大着胆子坐上车来,好在休之并不怪罪。云秀来不及说别的,先求休之救救孩子。休之一摸孩子额头,见他已经发烧,一面命人立刻去找大夫,一面命车夫快马加鞭,赶紧回府。
戚大富着急地问:“秀儿,你怎么来建康了?刘裕呢?”
“他在句章打仗,有十多万贼众从海上登陆,把句章围住了,他怕我们有危险,便托人把我们送到建康,说平西将军会收留我们的。我现在都不知道他怎么样了。”云秀哭着说,越哭越伤心。
休之看她这样,也觉得心中恻然,问:“你既然来找我,为何不在府中等着?”
云秀委屈地哭着说:“我去了,府上的人让我出城去找你。”
戚大富骂了一句。
休之不再说什么。
戚大富又愤愤说道:“那刘裕托的人,也不靠谱呀!送人都没送到地方,什么东西!”
云秀想到桓道芝不想暴露行踪,便含混说道:“人家也有急事。”
“谁啊?我认不认识?等我见了刘裕,好好说说这人。”戚大富不依不饶。
“是刘裕的朋友,我也不太相熟的。”云秀说道。
一会儿,到了王府,守门人见是休之的马车,忙把府门打开,跪在两边恭候他下车进府。休之带云秀下车,命人把守门的一干人都拉下去重责四十大板,然后把云秀接进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