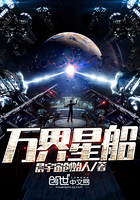一
群山叠峦,十月深秋,层林五色,美不胜收。
红的是枫树,绿的是松树,黄的是柞树,白的是桦树,加上落叶次生林黑褐色的树干参差其中,又有红日、蓝天和白云衬托,真是色彩斑斓,风景如画!
这里是小兴安岭张广才岭的延绵地带,再往东南,就是完达山脉了,山地、丘陵、平川相互交错是这一区域地貌的明显特征。一条一级高速公路G401国道像一条巨龙盘旋、弯曲、延伸着,它不仅是贯穿于此地的交通干线,而且也是欧亚大陆架在我国境内的重要一段。
此时,一辆黑色奥迪A6L小轿车正在大车、小车中飞快奔驰。这车由西北方向的省城而来,往东南边陲的冠东矿区而去。车内后排右侧坐着国家总局派驻省城的煤矿安全监察局局长辛家,左侧坐着纪检监察室主任林冬,办公室主任王帆坐在驾驶员“黑章”的旁边。
“开慢点!”王主任压低声音悄悄对“黑章”说。
王帆之所以用这句话反复提醒“黑章”,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来是最近全国和全省都在严肃认真地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月活动,高速路上安设了多处电子眼,车辆超速将被拍照,不仅要罚款、通报,还要在媒体上曝光。要是真的违章了,罚点款倒是小事,可又通报又曝光,那真是丢不起人,谁不知道东A00055是辛局长的车呀!再就是辛局自从上了车就面无表情,双眼紧闭,一言不发,不知道他是在想什么还是睡着了,怕车速太快影响了他。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条路坡陡、弯急、车多,车速太快总不如慢点安全。安全监察局嘛!不仅要管煤矿的安全生产,首先自身也得保证安全哪!要不谁服你?
“黑章”这一路紧张得不得了。平时,辛局坐车很少有这种状况,他不是与同车的同志谈谈工作,就是就某些问题让他们谈谈意见和建议,再就是不断地接打手机,也可以说,他有许多工作的思路和决策都是在旅途过程中萌发、动议和形成的。像今天这样不吱声、不睁眼、不接打一个电话的情况还真没见到过。
“黑章”今年29岁,给辛局开车已经六七年了,小伙子为人忠厚、老实、稳当,驾驶技术好。他最大的特点是不多说一句话,有人想从他嘴里抠出点辛局的情况来,那是枉费心机。由于他长得黑,所以,辛局和全局的人都管他叫“黑章”。这话说起来,还有段故事。每当单位的同志把他介绍给外人时,人家就会问:是姓弓长张啊,还是立早章啊?“黑章”想也不想立即回答说:“不清楚,反正大家都管我叫‘黑章’。”弄得大家一阵大笑。
“黑章”今天的脸可不仅仅是黑了,而是紧张得黑里透红。每当王主任提醒他开慢点,他就全身冒一次热汗。后来他又一想,算了吧,紧张啥,司机的任务就是保证领导安全、准时、顺利地到达目的地,别的事都和咱无关。想到这,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车也开得更稳了。
其实,辛局一直没有睡。两个多小时,他一直在深深思考着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那份重要批示和如何落实好总局纪检组组长的电话指示精神。辛局是今天中午才从北京回到省城的。他在总局开了两天汇报会,内容是通报全国小煤矿关井压产的进展情况,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阶段性部署,并提出了三点刚性要求:即列入关井名单的一个也不能漏;届时应该关井的一天也不能拖;国务院关井的六条标准一条也不能差。会议期间,他与一同参加会议的省政府主管工业的牛副省长进行了几次沟通,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部门和地方政府两个角度,就全省关井压产的现状、问题和工作规划很快形成了共识。两人甚至在今天上午共同返回省城的飞机上,还商定下午三点就召集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开个紧急会议,以便尽快把国家总局的这次会议精神落实下去。可是,计划不如变化快,辛局和陪同他前去开会的王主任下了飞机后,本打算到局里把这两天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处理一下,顺便看看局里还有什么事情。可是,刚坐上接他的汽车还没来得及打开手机,司机“黑章”的电话就响了,说纪检组林冬有重要事情向辛局汇报。
二
辛局走进办公室还没坐定,林冬就把一份重要批件递了上来。
总局局长在一封举报信上做了如下批示:“拟请安兴组长牵头速查清此事原委。今年的关井压产已到收尾阶段,如果存在如此严重问题,必须严肃处理。可否让辛家同志组织调查,并将结果告知我。”接下来就是状告的内容了,信写得很长,但归纳起来大体是四个问题:贺新煤矿不具备安全生产的基本条件,不仅拒不执行国家和省、市安全监管部门的停产指令,而且至今还在照常生产;该矿超层越界,井下做了很多隐蔽工程;该矿8月20日发生一起死亡3人的重大恶性事故,不仅隐瞒不报,而且偷偷地把尸体掩埋了;该矿与冠东矿业集团原主要领导有关,该领导不仅有明股,也有暗股。此信署名是郑心,留下了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座机,一个是手机。批示的时间是今天上午9点,怪不得昨天晚上在北京散会后,总局局长在见到辛家时没有提及此事。
林冬对辛局说:“安书记还交办了两件事,一是请您看一下这个批示,再就是他在办公室等您,请您给他回个电话。”听到林冬这句话,辛局边看批示,边毫不犹豫地拿起了办公桌上的座机话筒。
安书记即总局局长批示中提到的安兴,是中纪委驻总局纪检组组长。由于他曾在包括冠东在内的几个矿务局任过多年的党委书记,又在全行业德高望重,因此,无论他调到哪个部门,走上哪个岗位,担任哪个职务,大家都一直称呼他为安书记。别人叫着顺口,他也觉得亲近。
这电话一通就是半个多小时……
刚放下电话,铃声就响了,听筒里传来了牛副省长那响脆的声音:“辛家呀!你跟谁在聊啊?是不是又惹老婆生气了?哈哈哈哈……”玩笑过后,辛家把他看过批示,与安书记通电话,又请示了省长和省委书记等事,详尽地做了表述。
“看来,咱们的计划又泡汤了,辛家,你立即动身吧,省纪委梁副书记明天早晨就到,我安排一下紧随其后。我看咱们把各产煤地市的主管领导集中到冠东去,在那儿贯彻国家的会议精神,也借此把冠东的关井压产推动一下,你看怎么样?”牛副省长这么客气,辛局能说不行吗!放下电话,辛局抬头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数码万年历电子钟:2006年10月27日11时55分。
他一边整理桌上的文件,一边对站在左右的王帆和林冬说:“咱仨半个小时吃饭,半个小时收拾东西,告诉‘黑章’,下午一点出发去冠东。”
王、林二人对了一下目光,尽管他俩对刚才的一切看得、听得都很清楚,但还是感到有些突然和惊讶:“这就走?”
“对,这就走!”辛局头也没抬。
“我俩也去?”王、刘几乎是同时说。
“废话!”辛局继续在批办文件。
“我说辛局,关井压产是各级政府的事,咱这个安全监察部门去管合适吗,这不是自家的坟茔地没哭过来,又去哭乱葬岗子吗?”王帆的俏皮嗑儿多,这在全局都出名。
“咱去查人家矿业集团领导违纪违规,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不太爱吱声的林冬也突然冒出了这么一句话。
“得,得,得,有完没完?咱们三个是你大(辛局瞧了瞧林冬)?你大(又看了看王帆)?还是我大?”
“看论啥呗?”林冬嘟囔着。
“论啥?这个时候论啥?还能论同学,论哥们,论朋友,当然是论官呀!”辛局一本正经地说。
“那还用问!”王帆接了一句。
“这不就得了,别在那儿没事瞎叽咕,走!去餐厅。”他们每天午间都在省局吃自助工作餐。
三
其实,王、林二人讲的,也正是辛局心里想的。
辛局确实很为难。难就难在总局下属已成立了6年的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在各产煤省、市、自治区下设的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分辖区组建的监察分局,是一个垂直管理机构,人、财、物均由国家局直属领导和管理,对其机构、人员、职能、责任,国务院办公厅的两个文件专门做了明确、具体的规定。而国有和地方大中型煤炭企业下放管理后,企业的党、政、工,人、财、物,产、供、销,均分别由所在地的省、市和自治区党委、政府及主管部门管理。煤矿安全监察机构主要是对各类煤矿在安全生产的监察上、特殊工种和人员的培训上,各类事故的调查处理上履行自己的五项职责,依法行政,严格监察,同时对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进行检查指导并提出意见建议。而对于关井压产,国务院、总局和有关部门的文件、领导讲话,甚至是媒体每次提及都明确提出由各级政府负责。自己这次去冠东调查此事,怎么摆正角色,怎么开展工作,怎么表明态度呢?再说了,自从煤矿企业管理体制改革之后,煤监机构的纪检监察工作除了抓好系统内部的党风廉政和班子队伍建设,就是调查事故,其他的事情也不在自己的职责范围之内,对此,林冬说的完全在理。这就是辛局一路上面无表情的原因之一。
辛局确实心里很烦。他倒不是因为这封上告信心烦,而是他对信中所告的这个煤矿的大事小情是再清楚不过了,根本不用调查。因为这次上北京开会之前,他作为省政府关井压产调查组负责冠东地区的组长,在冠东整整工作了两周,刚刚离开。他心里十分清楚,尽管上告信告了好几件事,可实质问题就是说这个井口必须关闭。只要把贺新煤矿列入关井名单,一切矛盾就会迎刃而解。辛家之所以能果断地做出这样的推论,是因为在上次他来调查关井压产期间,有几个小井曾公开叫号:只要贺新煤矿关闭,我们就全部关井,如果把贺新煤矿留下,只关我们,那根本没门儿!辛局也一直弄不明白,按国务院下发的“小井关闭九条规定”衡量,一个小井只要违反其中一条就得关闭,而贺新煤矿是九条违反了八条。对此,管辖这个井口的江东监察分局已经三次提出关闭井口的建议书,分局的张青局长也多次向自己做过汇报,省局也向省有关部门几次表明了建议关井的态度,可为什么就是落实不了?和尚头顶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光调查不落实顶个屁用!真不知道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这是他一直双眼紧闭的原因之二。
辛局确实感到很累。虽然在省城当官,可是不管是干企业,抓管理,还是搞监察,只要是和煤矿搭上边,那就是苦,就是累,就是活遭罪。自打调到省局四年来,无论是当处长、副局长还是局长,他每年下基层都在二百天左右。有一次,王帆给他算了一下工作记录,最多的一年在基层待了二百零四天,最少的一年是一百九十七天。也就是说除了开会、学习和大假,几乎2/3的时间工作生活在产煤地、市、县和各类煤炭企业中。就拿今天走的这条路来说吧,他每个月都不知道要来回穿梭多少次。他记得最清楚的是2001年6月,为陪国家总局和省里的领导检查、组织小煤矿整顿验收和调查处理几起重特大事故,他一个月就跑了五趟。许多老伙计都跟他开玩笑:“辛局长,您这工作跟您这名字应验了,真是辛家,辛家——辛苦到家了,来冠东跟通勤差不多了。”本来回省城了,可第二天又因为公务非来冠东不可。前几天见到的人又问了:“辛局,还没走哪,差不多来了二十天了吧?”弄得他哭笑不得。
这不,今天快中午才下飞机,连家也没回,下午又出发了,连老婆也不知道他已经从北京回来又去往冠东。他寻思着到了冠东再打个电话,连报平安都有了,还能省一次电话费。为此,他特意嘱咐王帆:“我把手机关了,心静一会儿,你把手机开着,不是你认为非我接的电话一律应付回去。”王帆这个老道的办公室主任,自然心知肚明,立即把手机调到静音状态,不管电话怎么震动,他一看就能分辨出轻重缓急,对那些没用的电话,他连接都不接。怪不得“黑章”两个多小时,一直没听到辛局接打电话。
还让辛局感到沉重的是,煤矿安全的责任真是重于泰山。虽然矿井下黑乱脏臭,设备傻大黑粗,煤炭生产看起来是个粗拉活,但是煤矿安全来不得半点的粗心大意,必须细之又细,慎之又慎,严之又严,否则“一失足成千古恨”。回想起这几年全省发生的两起死亡人数都在百人以上的特别重大恶性事故,不就是责任跑粗、管理跑粗、操作跑粗造成的恶果吗?因此,这几年,他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总是坚持在常年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极力从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和社会监督等方面,探索出一条符合区域实际和实现煤矿安全生产的新招法。殊不知,这种正常的工作往往总被今天这样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务所打断,真是砍了头的竹子——节外生枝。这也是他一直一言不发的原因之三。
可是,让辛局感到欣慰的,倒是总局纪检组安书记和省政府牛副省长的一番话。“辛家呀,你今天辛苦辛苦,打打前站,做做准备,我今天下午有个必须参加的党组会,明天晚上就到。从你的角度,有些话也不好讲,到时候该说的话我去说。我当调查组组长,你和省纪委的梁副书记当副组长,放心大胆地干,有什么问题我兜底儿。”安书记的话让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牛副省长也说:“辛老弟呀,这本来是我的事,结果让你受累了,我下午安排一下工作,明天中午就到。我跟纪委老梁说了,你俩先拿出个意见来,到时候我去冲锋陷阵,绝不往里装你们。但你是专家,你得出点儿好主意,三人同行老弟受苦嘛!哈哈哈哈……”
想到这里,辛局沉重的心情总算透进了一丝光亮,顿时轻松了许多。
四
车子颠簸了几下。
辛家不自觉地睁开双眼向窗外一瞥,也巧,正好扫到了高速路旁一闪而过的一块绿色路标:距冠东180公里。凭着对此处地容地貌的了解,他知道快要走出张广才岭的东南麓了。这一带地势险要,怪峰突兀,山崖陡峭,路狭窄,坡度大,急弯多,是司机师傅们尤其是在冬季驾车时最为打怵的一段,但这里山峻、树高、林密,也是风光最美的一段。当年,作家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所描写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在这一带围剿国民党残匪的故事。特别是家喻户晓的侦察英雄杨子荣乔装扮匪,深入虎穴,活捉座山雕的精彩章节,就发生在离此不远的老爷岭上。想到此,他禁不住触景生情,竟轻声哼起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那段脍炙人口的西皮唱腔:“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捡重担挑在肩……越是艰险越向前……”他哼的是有板有眼,京韵京味。最后那几句“立下愚公移山志,能破万重困难关,一颗红心似火焰,化作利剑斩凶顽”,他竟字正腔圆,节奏准确,一气呵成地唱到了位。
“弟兄们,怎么样?”辛局一反常态,满脸微笑地问。
“好!”“好,好!”车里的另外三人虽然没能齐口同声,但都表达了各自赞许的心情。
从哲学的观点讲,精神状态是意志品质和信念决心的外在直观反映。这一点对大学本科毕业的哲学系高才生王帆来说,那是最简单不过了。他十分清楚,此时的辛家,对这次去冠东调查,肯定是思路明达,胸有成竹了!
从推理的角度看,树立信念能够坚定信心,进而才能下定决心。林冬这个学数学的大学毕业生,一直善于用逻辑思维去观察人,去处理事,去干工作。他也十分清楚,此时的辛家对这次去冠东调查,不,准确地说应该是关井压产,肯定是胜券在握,誓在必夺,因为这项工作任务已经迫在眉睫,时不我待了。
辛局的情绪变了,对大伙儿的称呼改了,车内的气氛也顿时活跃了起来。
“辛局,从省城出发时,你既不让通知冠东市委、市政府,又不让告诉冠东矿业集团,还不许我安排吃饭和住宿的地方,这‘三不政策’我实在是领会不透意图,难道今晚局长大人和我们这几个拎包的要住露天地儿?”王帆看了看表,已经下午三点半了,五点左右就应该到达目的地了。办公室主任的职责,让他实在忍不住问了起来。但是,言辞和腔调充满了玩笑味。
“王主任,都说你这主任能力、水平,尤其是头脑反应是全国、全省‘煤’字系统最棒的,通过今天这事,我怎么没看出来呀!当办公室主任的,凡事都得至少提出个一、二、三来,供领导选择和决策吧!你问我,我问谁呀?你是我的主任,还是我是你的主任呢?”辛局的话已经完全不是上级对下级布置工作的味道了,而是哥们兄弟间的一种调侃。
接着,他冲着林冬问:“你说呢?”
“我说个啥?我就知道官大、嘴大、口气大,金口玉牙,说啥是啥。”林冬和王帆是同一级别的处级干部,当然要结成统一战线去对付正厅级的辛局了。
“平时你小子蔫了巴叽的,可到了节骨眼儿上是说话有劲,不用上粪!”辛局开始“骂人”了。
“哈哈哈……”三人一同大笑,“黑章”也“嘿、嘿、嘿”地咧着嘴角捡了个乐儿。
五
辛家、林冬和王帆,这三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不单单是同事,而且同龄,是同学,还是同乡,所以感情、友情和亲情在他们三个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都是冠东人,只是一个家在农村,一个家在市区,一个家在煤矿;他们初中、高中又都在同一个班级,在省重点校冠东市二中同窗了六年;他们还都以优异成绩分别考上了国家重点大学,辛家被中国矿业大学录取,主修采矿专业,林冬则以他们三人中最好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数学系,王帆在吉林大学哲学系深造了四年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毕业后,他们按照事先约定都回到冠东矿务局工作;再后来,三人又先后调到省城的煤矿安全监察局成为同事;特别是今天,三人又同车前往老家冠东共同处理一件大事,不,应该说是四个人,“黑章”也是冠东人哪!是辛局把他调到,不,应该说是带到省城的。
他们三人的关系,无疑也招来了局内外一些人的非议,甚至连“黑章”也刮上了边儿。其实,他们三人好归好,但从来都是事归事,尤其在工作中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有的时候摔门、拍桌子、砸杯子,弄得很多人都得来“劝架”。可事情过后,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半天一天,就又恢复原来的模样了。局里的人都说:“嗨!他们之间的事,谁也弄不明白!”
为了他们三人的关系问题,辛局在今年七月份的领导班子谈心会上,对党组成员讲了一番令人十分感动的话。他说:“俗话说,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至于我和王帆、林冬的关系,我这个局长以党组书记,不!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向党组汇报,我们三人或者是三人当中任何两人之间没有任何一点不正常的政治、经济和其他关系。”辛局的语气十分自信而坚定。
他接着说:“只是除了同事之外,又增加了点同岁、同学和同乡的缘分。有人说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好,这是事实。但是,除了谈话投机缘,脾气对撇子,互相能交心外,大家说,他俩沾着我什么光了?处级干部不是我提的,现在的岗位不是我调的,房子不是我给的……”党组成员和列席谈心会的各处室主要领导干部都在洗耳恭听,只是王帆和林冬没有在场,他们分别正在两个地、市搞关井压产的摸底调查。
“倒是没少跟着我吃苦、受累、遭罪!没少跟着我背黑锅!”辛局心里有些内疚。
“远的不说,就说今年总局部署的大打瓦斯治理和关井压产两个攻坚战吧,牛副省长非常客气地跟我商量,说请我局再抽调两个处级干部,参加省政府的三个关井压产调查组。按理说,副省长说请,那是客气!这件事本来咱们局尤其是我就责无旁贷。那么两个处级干部抽谁呀?按常理说,应该是监察一处、二处处长,因为他们对情况熟,又是他们分内的活儿。”辛局喝了一口茶。
“可是,我坚持派王帆和林冬二位去。为什么,就是因为有人说我们的关系好。关井压产这个得罪人、矛盾大、活难干的差事,就得让这俩人替我去堵枪眼,谁让我们的‘关系好’呢?当时,班子其他成员并不同意我的意见,可我就是坚持。”辛局有些激动了。
“结果怎么样呢?我是坚持了意见,可把他俩害得不浅。他们一人一组,一个在南片,一个在北片。俩人都被委任为省政府关井压产工作组的副组长,可真干起活来那可不是副组长了,是组长!为啥呀,因为这两个组的组长都是省里的厅局长,一位公务缠身压根儿就没去,一位去了一天就参加省里会议离开了,临走还给王帆下达了和毛主席一样的重要指示:‘你办事,我放心。’”会议室里哄堂大笑。
“怎么办?干吧!他俩明明白白地知道,不干,我能饶得了他们吗!结果他俩是起五更,爬半夜,详细摸底调查,协调有关部门,进行资料汇总,经常忙得通宵达旦。王帆两个月没回一趟省城,林冬一天晚上下雨路滑,乘坐的汽车撞到了路边大树上,差点把小命丢了,腿到现在还瘸着。”辛局有点心疼。
“最难办的是最后拟定关井压产的建议名单了。他俩分别向我汇报,那纯粹是个程序!我虽然是局长,可是究竟哪个矿井该关不该关,我知道个啥?但是,我知道他俩谁也不会胡来。于是,我说,你俩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办对了,成绩是你们的,办错了,问题是我的。结果他俩干得都比我这个局长强。今年全省计划关闭70个小煤矿,他俩各负责的一片20个,不但建议名单落实了,而且有的已经关闭到位了。唯有我负责的冠东地区,对33个井是光调查摸底了一遍,目前连建议名单都没定夺。”说到这里,辛局和与会的全体人员都不禁对王、林二位的工作从心里感到佩服。
“最可气的是,市里有个别人跟小矿主说关井名单跟市里没关系,都是省调查组圈定的,还说是煤矿安全监察局带队的人说了算。真是胡说八道!”辛局拿起桌上的文件重重摔了一下。
“弄得小矿主都冲我们来,给王帆、林冬打电话,恐吓、谩骂,甚至扬言要杀他们全家。”
辛局愤怒地说:“这件事不算完,等我腾出手来弄清楚了,我不弄他个人仰马翻,这个局长我就不干了!”大家还从来没有见过平时说话总是和气、干脆的辛局今天发这么大的火!
“再有一点,就是有的同志对我有意见,但这不要紧,找时间咱们谈谈嘛!说我批评谁谁谁,是王、林二人上我这里来告的状,这是哪来的事儿?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保证,王、林二人从没说过全局任何人一句坏话,反而是一谈起某某,他们总是说这个人的优点。我也当着大家的面说清楚,刘国明……”他叫着监察二处处长的名字。
“上次要处分你的事,你老对他们俩耿耿于怀,认为是他俩上领导这儿说你的坏话,今天我告诉你,后来之所以没处分你,才正是由于他俩多次说了好话。”
六
说到这儿,大家心里都清楚。去年,在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安全监察工作中,二处的两名监察员发现冠东一个小井有一个十几米的上山独头没采取任何的安全措施,不仅瓦斯超限,而且没有正常供风,也没有进行密闭。所以与负责这个辖区煤矿安全监察的江东分局一起,依照煤矿安全监察的有关条例和规定,立即下达了停产整顿指令并给予了经济处罚。可是,井口虽然交了罚款,但是没有停产。更为严重的是,作为煤矿安全监察部门没有对这一重大隐患跟踪问效。结果仅仅过了三天,这个井口的两个工人误入此处导致窒息死亡。这真把辛局气坏了,作为监察部门出了这样的漏洞,真是丢人!现眼!失职!他提议非处分刘国明不可。
一看局长真的动了肝火,王帆、林冬三番五次轮着班地劝辛局:“这事不能全怪国明,咱们把文书下了,把款罚了,国明还三次给矿主、市里和咱们下面的分局分别打电话。市里的监察部门还把该井的提升绞车锁上了,分局的人又天天去盯着,也确实没有生产,谁知道矿主后半夜又私自把锁打开偷着干上了。咱们这个部门总不能派人24小时蹲在井口吧!咱省局60来人,分局20来人,要是那么干,全省近千个小煤矿,咱就是不吃、不喝、不睡觉,也看不过来呀!”
“再说了,咱这个机构虽然成立5年了,但是有些监察的路子、程序和方式毕竟还是处在一个摸索、总结和完善的阶段。您说,有谁愿意出事故啊!”辛局一开始态度还比较坚决,可架不住他俩反复做工作,而且又说得头头是道,也就慢慢地消气了。后来,只是把刘国明叫来,狠狠地批了一顿。
一看辛局提起了这件事,刘国明的脸涨得通红,连忙摆着手说:“没……没有,不信你问问他们。”他用手指着身边的几个与会者。大家看着刘国明这尴尬神情,都禁不住哧哧地笑了起来。
辛局又饱含深情地说:“组织调我到局里工作后,我总感到能与所有的同志在一起共事是一种缘分,缘分哪!”辛局加重了语气。
“大家都是我的兄弟姐妹,都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而承担共同的责任,这个目标就是搞好煤矿安全监察,保证全省的煤矿平安。我是局长,用大家的话说就是‘一把手’,那么作为我,能去整副手?整处长?整部下?我要真整,得整比我大的官,把他们中间的谁整掉,我再往上爬一爬,我整大家干什么?难道把你们谁整掉了,放着局长‘一把手’不当,我去干你们的活儿?”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我是有时候批评人,但那都是为了工作,我这个人既不记恨人,也不会对谁有成见,都是就事论事,说完就拉倒。咱们都共事多年了,难道对我这一点,大家还没品透!”
辛局讲完了,会场静得好像掉根针都得掷地有声。霎时,会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种热烈的场面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辛局和大家都清楚,局里领导班子成员们的心拧得更紧了。
七
辛局看了看手表,又与左右班子成员耳语了几句,决定把原定下午研究工作的会议提到上午来开。辛局清楚地知道,趁着大家的情绪正高,如果因势利导,一定会把工作研究得更好。
会议议定了三条,一是由辛局挂帅,和王帆、林冬一起继续参加省政府的关井压产调查工作组,把今年的关井压产任务全部落实到位;二是由一名副局长牵头,抽调监察一处、二处的同志,推进瓦斯治理的攻坚战;三是由一名副局长带队,兵分五路,与各监察分局一起,全方位地进行为期两个月的重点监察,目标是下半年坚决杜绝一次死亡三人的重大事故,全年百万吨死亡率一定创出全省历史同期最好水平,为地方煤矿的安全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很快,有关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就传到了王帆和林冬的耳朵里,尤其是跟他俩描述辛局讲话的人学得绘声绘色,把他俩感动得差点没掉下泪来。确实,他们三人一起这么多年,无论是私下交往还是公开场合,辛局还从来没有对他俩这样评价过。
后来,在一次三人见面的时候,王帆和林冬你一言我一语,跟辛家推心置腹地说了一番话:“老同学呀!啥也别说了,也别胡思乱想了,嘴长在人家的脸上,说啥人家自己说了算。没给咱造别的谣就不错了,不就说咱们关系好吗?总比坏强吧!”
“咱们能对得起共产党员这个名,对得起组织任命的这个官,对得起国家给开的工资钱,给国家、社会和百姓干点实事就行了。”
……
慢慢地,三人都陷入了沉默与思考,虽然没再说话,但他们已经心照不宣,形成了思想认识上的共识。
所以,这次来冠东之前,在辛局办公室说的那些话,他俩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说也白说。全局只有他俩跟辛局是关井压产调查组成员,辛局来冠东,他俩还想躲清静?
八
车子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然后径直开向东南。太阳刚刚落山,时间将近五点,车子距冠东还有十五公里。车没有向冠东市里开去,而是继续直奔路标指向还有十公里的平阳。
“咱这是去哪儿呀?”林冬迷惑地问了一句。
辛局笑吟吟地望着窗外那再也熟悉不过的山山水水和一草一木,并不搭话。
其实,从辛局说出了“三不政策”,王帆就知道了今晚他想去哪儿。因此,在省城还没出发的时候,他已经做出了安排,但没有对林冬说,万一领导的想法再有变化呢?
“到时候就知道了!”王帆边笑边说,又顺手拨通了手机:“老爹吗?再有二十分钟准到!”
“噢!”林冬也笑了起来,他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