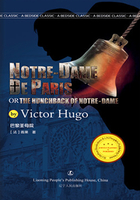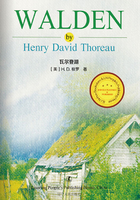1984年离我远了,这中间隔了十七年,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代人的成长……我不知道该怎样回忆这代人的成长,站在风尘的1984年的街头,他们会看见一些什么呢?也许他们走着,每天在这上学、放学的路上,脚下踢着一颗石籽,人有些无聊。黄书包斜挎在肩上,在屁股的另一侧颠簸着,里面发出铅笔盒撞击书本的声音。
他们是中学生了,才十二、三岁吧。课业一下子沉重了许多,新添了英语,历史,地理,植物……他们知道“叶绿素”、北回归线等新名词。“rose”是玫瑰花,如果用作人名,就叫罗斯。真是有趣得很。
这是被寄予厚望的一代。他们身处的时代是那样的热火朝天,风尘仆仆,许多人搭着时代的列车往前赶,汗渍淋漓的……整个八十年代就像夏日的农贸市场,充满了各种奇怪的、不相干的尖叫声。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走走停停,心存很多幻想,可有时也是茫然的。他们不知为什么来到这里,来找什么。也许是来看热闹的吧?有的就空手而归了,也有的呢,顺手捞到了一点小便宜。
这是物质主义盛行的年代,也是理想主义的年代。青年人开始寻根了,热衷于追溯人的源头,他们会问出“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样的傻问题。整个一代青年是迷惘的,空有很多体力,可是浪费了。
而这一代的少年呢,正在安静地成长。时代的好处,他们还来不及体会。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活泼向上的年代,每天都在生长,正如“日新月异”。可是这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成长里没什么新鲜事,啃着手指头,一天又一天,就这么迷迷糊糊地长大了。
我在这里记述的就是这些,几个人物,一些事件,某个场景……也许太平淡了,缺少冲突和戏剧性。可是成长,怎会有戏剧性呢?它是如此无聊,枯燥,只不过一年年地挨下去,熬到头了,就尽了。
从念初中开始,我母亲就向我灌输考大学的愿望。她常常在我耳边聒噪着,我虽嫌烦,可是认真地听着,点着头,做的仍是不相干的事。我喜读课外书,从学校图书馆借的,一次只能借三本,看完了,还了再借。图书馆在教研楼的底层,隔壁是期刊阅览室,再隔壁的一个小套间里住着一个鳏夫,图书管理员,姓吴,我们都叫他吴老师。
这吴老师是吴江人,也有人说他是上海人。操着一口拗口的普通话,五十多岁,个子不高,黄瘦脸,戴着眼镜。总之,是有点南方人特质的,不是秀朗干净,玉树临风,而是有点那个。我说不上是哪个,也不是阴沉,更说不上龌龊,只是让人想起潮湿的梅雨季和青苔,亦或是很多天没洗澡,身上粘遢遢的,可是忍受着,一天天懒洋洋地拖下去,似乎也坏不到哪儿去。
他人倒真不坏,很安静,喜欢散步。我们常常看见他穿着泛白的灰中山装,风纪扣扣得很严实;夏天他穿白府绸衬衫,里面的白背心隐约可现……他朝我们走过来了,背着手,慢慢地踱步。他走在校园的某条林荫道上,这是下午时分,课外活动开始了。许多高年级的男生骑着自行车在校园里游荡,摇着铃,从他身边闪一下身,把车笼头弄得像蛇一样蜿蜒曲折。
也有的男生叉腿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曲着膝,鞋掌几乎擦着路面。他们一手搭着书包,一手放在嘴唇边,吹出尖厉的口哨。偶尔他们也会回头看一眼,他们看见什么了吗?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
就在这喧闹的氛围里,吴老师向我们走来了。他微笑着,看上去很平和,他一向是平和的。看见相熟的女生,总是停下来打个招呼,说一会话。他心情很好,叫人小丫头。如果凑手的话,他甚至会摸摸你的头,轻轻地拍你一下。
他是个长者,一个地道的绅士。然而他也是异性。那些低年级的小姑娘们,才十二、三岁吧,刚升入中学,还不谙世事。她们喜欢和他搭讪,东家长西家短,告诉他很多事情。她们总是嘻嘻哈哈的,她们想以嘻嘻哈哈来掩饰些什么,来掩饰什么呢?她们自己也不知道。
到了她们这个年纪,是极敏感害羞的,有很多繁杂的心事,一点点小动作都能明察秋毫。什么也别想瞒过她们。她们笑道,吴老师……侧了一下身体,躲过了,吴老师的那只手便在半空中停下了。
总之,她们还是喜欢他的,他不算讨厌,知道适可而止。他能准确地叫出许多女生的名字,初一(4)班的李小玲,初二(3)班的蔡红……她们感到很吃惊,连班主任都未必记住她们的名字,可是他记住了。她们觉得欣喜。
况且,他那儿还有大白兔奶糖,正宗的上海货,是他从南方买回来的。他分给她们糖吃,她们也未必想吃这块糖,可是好意难却,吃就吃了罢。那时她们在集糖纸,就像集邮,集火柴商标一样,她们把五颜六色的玻璃糖纸夹在一个硬壳笔记本里,真是好看呀,尤其在阳光底下,翻一页就是一幅图案,黄的是向日葵,蓝的是大海,绿的是草原,还有白绵羊,穿泡泡裙的小女孩……就像小时候玩过的万花筒,摇一摇,那里头的世界就出来了。
单为这个原因,她们也愿意去他那儿坐坐,说一会话,顺便淘两张糖纸。
慢慢地,在我们女生当中,开始流传着吴老师的种种谣言。有人说他作风不好,他很早就离了婚,在男女关系上一向不清白。你想呵,他一个外乡人,凭什么在此蛰居多年?他是犯过错误的,据说被贬谪此地,他无儿无女,无依无靠。他甚至没有朋友,成天跟一拨小女生厮混,他什么意思?!为什么高年级的女生不愿理他,她们是过来人,早知道他不是个东西,他也就骗骗我们罢了。
还有人说他色迷迷的,他那双眼睛呀,啧啧……她们不再说下去了,在阳光底下,她们的脸色呈现出成人的灰白,那是一张张成熟而世故的脸,也是幼稚的脸,也是未来的良家妇女的脸。
很多年后,我还在想着这拨女孩子,包括我自己在内,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了这样?才十二、三岁,一切的天真烂漫全是浮面的,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心智早已熟透,慢慢地变质,发出苹果的腐香来。这些未来的小女人呵,长大以后会是何等形状,委实不敢想像。
关于吴老师的“色”,我并不能确定,可是我也加入了讲他坏话的行列。我只烦他腻腻歪歪的,可是下雨天,跑去向他借雨伞也是有的。一个冬日的晌午,天很冷,我吃完了饭(因为家离得远,中午我在学校吃饭),倚在阅览室门口的廊柱上晒太阳。这时吴老师从隔壁走过来了,他说,来家里坐坐吧。
我走进他的家里,很谨慎地搬来椅子坐在外间的门口,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女孩子走进这屋里,也像我一样搬来板凳坐在门口。我们说了一会话。他拿出果盒让我吃糖,我不吃,推让着。他把糖剥开,差不多要送过来了,我站起来,感觉他在碰我的手肘。
很多年后,我也不能确定他是否碰过我,他怀有怎样的心思,我只是疑窦丛生。对我来说他是一个谜,谜底尚待揭露,而很多年前的我,只不过从谜面上轻轻滑过了,我侧一下身,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我对他说,我要走了。非常镇静地说着这句话,像一个历经世事的女人,给足了别人面子,也为自己找了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