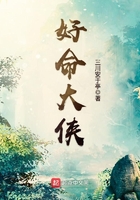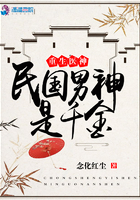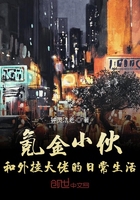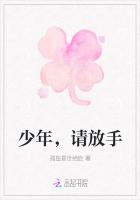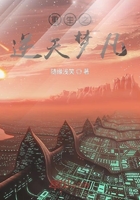在黄家村村口的一间土地庙里,黄念书和李翠翠席地相对而坐。黄念书在地上写了密密麻麻一大片字,李翠翠拿着树枝在土地上临摹着。少年认真看一本书,少女一边抄字一边偶尔偷偷看一眼少年,见少年看的太入神,便不忍心打断他。终于等到少年偶然放下书的空挡,少女忙问道:“念书啊,这几个字怎么读。”少年耐心的为其指点出来之后,少女说道:“今天乡试出成绩,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啊。我都替你着急。”少年淡然一笑,说道:“反正也考完了,已成定势,再着急也没用啊。”翠翠看着黄念书问道:“你若是乡试过了,是不是就要去京城考试了,之后是不是就不回来了?”黄念书答道:“乡试只是咱们县的考试,乡试过了以后郡县会向京城推送前几名参与省试……”翠翠打断他道:“你说这些俺都不懂,你就说是不是很久都不回来了。”黄念书看着少女,微微叹了口气,说道:“似乎是的,从乡试到殿试就要小半年,之后还要在国子监和翰林院深造几年,几年之后位列何职还是未知,估计五年之内是不会告假还乡的。不过我若是得空,就会回来看看的,毕竟我爷爷不能跟我进京,我还是不放心他的。”翠翠仰头看着少年,认真说道:“你不在的时候,我会替你照顾爷爷的。”黄念书受宠若惊,赶忙说道:“这我何德何能啊,不用的。再说你也要嫁人,你也不一定就在咱们村了啊。”翠翠抬头看着他,欲言又止,突然门口传来急促的喊叫声,二人一同转头向外看去。“黄念书!黄念书!给老子出来!你乡试中了!你乡试中了!”二人起身向庙门口走去,只见王小六挥舞着一大张纸,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翠翠忙迎上去扶住他,问道:“怎么了怎么了?念书中啦?”王小六弯着腰使劲喘着粗气,手一扬把纸递了上去。黄念书接过,只见最上方写着:洪武三十七年丰谷县乡试榜。黄念书的名字赫然位列榜首。黄念书深吸了一口气,把大榜全部展开,向下看去,实则一个也看不下去,心脏砰砰跳个不停,手脚发软,脑袋有些晕眩。王小六和翠翠不敢打扰他,只能让他一直保持一个姿势站了许久。不多时又有两个人走过来,正是于秀才和黄念书的爷爷黄国邦。原来于秀才和王小六去乡里领了大榜之后,见黄念书位列榜首,王小六直接一把把大榜抢过来,飞也似地跑到黄念书家,但只有黄国邦在家,王小六便直接来到他们常去的土地庙,这才找到二人。而于秀才从乡里回来之后,便去了黄家与黄国邦长谈了以后的安排,二人这才赶到。见到黄念书在此,黄国邦走过去拍了拍孙子的肩膀,黄念书如梦初醒,看着黄国邦说道:“爷爷,我考上了。”黄国邦满脸都笑出了褶子,无比欣慰地看着孙子,说道:“好,不愧是我的孙子,考上了,还是第一名。接下来你就专心学习,日子一到你就进京。”黄念书定了定心神,环视了一圈,只见黄国邦、于秀才、王六郎、李翠翠都在看着自己,点点头说道:“好。”于秀才接过黄榜,差王小六给人送回去,接着对黄念书说道:“从今天起,你就吃住在我家,我给你讲经书时策。你爷爷会把你的铺盖送来。你在我这学五天,随后就进京。”黄念书一愣,能预想到接下来的日子该是泡在诗书里了。
昏暗的油灯影下,黄念书埋头于史书典籍之中,于秀才就在一边从厚厚一摞旧书里翻找着。终于于秀才抬起了头,翻出了一本破破烂烂的书卷,放在黄念书面前,哑着嗓子说道:“这是我当年科考的时候,在京城买的一本《时务策》,里面都是最容易考的题,你再把它看完。”黄念书揉了揉酸涩的双眼,哀求道:“这都看了一整天了,歇一歇吧,先生你的嗓子都讲哑了。”于秀才叹了口子,爱怜的看着黄念书说道:“也罢,是我太心急了,歇一歇罢。”黄念书放下笔,拨弄了一下油灯灯芯,揉了揉酸涩的脖子和腰。于秀才泡了两杯茶水,递给黄念书一杯,坐在黄念书对面。二人沉默不语,于秀才率先开口说道:“出了咱们乡,你就是羁旅之人了。外面不比咱们北凉,尤其是京城,你要处处谨慎些。莫要得罪了人,也莫要受欺负。”黄念书答道:“好的,弟子知道了。”于秀才又说道:“出门之后,吃饭喝水都要花钱,花销还不小。我当年凑出了十几两银子,那也紧紧巴巴。不过这次你不用担心,你爷爷做几十年驿卒,给你攒了不少兵饷,我也会让乡亲们凑一些。到时候你不用太省,足够你用了。若是有人贩卖考题,信都不要信,九成九是假的。就算是真的,也不是咱们能买得起的。不过若是有人卖历年的题库,你便可以挑便宜的买一些。京城北华街有咱们北凉的驿馆,凡是入京的北凉仕子都可以凭户籍文牒入住,每天中午一顿饭,要6文钱。你到时候去那里投宿就可以。若是在驿馆里遇到老一些的人,就可以跟他们提我的名字,他们应该还记得我。”黄念书好奇问道:“先生,您教了我们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您的名讳?”于秀才落寞说道:“我本姓于名签。我的先生给我取了字,但落榜以后,自知愧对于先生,就把字隐去了,不提也罢,只需对他们说我叫于签,是那个省试不利的落魄的书生就好。”于秀才喝了一口茶水,又嘱咐道:“皇宫旁有一条燕子街,看着不起眼,可里面住的都是朝中大员。你开考之前,先自己写几篇文章,什么都好,无论诗词还是时策。多誊写几份,揣在身上。一大早就去燕子街街口等着,看到穿官服的出来就赶紧把文章递上去,态度千万谦卑些,一旦有人收下了你的文章,对你是大有裨益,你可千万记得。”黄念书说道:“好,我记下了。”于秀才看着灯芯里的焰火,双眼失神,自言自语地吟诵道:“十年前事已悠哉,旋被钟声早暮催。明月似师生又没,白云如客去还来……”黄念书接道:“烟笼瑞阁僧经静,风打虚窗佛幌开。惟有南边山色在,重重依旧上高台。”于秀才点点头,继续说道:“孩子啊,你可别嫌为师唠叨。我当年命运使然没考上,好不容易名下教出了你,你若能参加殿试,为师至死也瞑目了。我知道你能留在朝廷。你乡试过了,是秀才,就会去京城参加国子监的省试,这时候就是举人了,举人才可以做国子监的学徒,或是去六部做个九品的副使,若是省试名列前茅,或是被朝中大员举荐,就可以参加殿试,到时候皇上亲自出题。殿试无论名次如何,都可以做上六品以上的主事了。在你做官之后,这些话就再也不会有人对你说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十年苦读,一朝科考,一生攀爬,谋得高位。做官到底为的是什么?为自己的名誉?光宗耀祖?衣锦还乡?还是唯唯诺诺一生,死后在史书上留个文正的谥号?亦或者是买官弄爵,玩弄权势?层层剥削,赚个盆满钵满?要我说,都不是!念书你记住,无论你以后做得了多大的官,都要记得,你做官不为自己,不为上司,不为皇上。你为的是天下千千万的百姓!王朝强盛却也兴衰更替,皇恩浩荡照样有昏君佞臣。我也不管你如何在官场里摸爬滚打,我只要你不愧对良心,不愧对天地,不愧对于生你养你的北凉,不愧对百姓,就够了。若是你也随波逐流,作奸犯科,我于秀才本事不大,但我把你的名牌挂在学堂外面,受乡里人唾骂!”黄念书吓得一顿,赶忙起身躬身行礼道:“学生谨遵先生教诲!”
黄家村前,聚齐了一大群男女老少。今天是黄念书进京的日子。由于路途遥远,所以要提前出发,在路上就要耽误十多天。黄念书背着硕大的包裹,里面衣食笔墨皆有。黄国邦破例牵出驿站军马私用,只为送孙子一程。黄国邦李翠翠正给黄念书再检查一遍包裹,生怕落下什么。突然人群中钻出杨木匠,手里抱着一个木头箱子,箱子外皮用粗布包住,箱上面还支出一块雨棚。杨木匠抱着木箱走过来,对黄国邦说道:“来,俺给念书做了个书箱子,结实还能装东西,把书啥的都装进吧。”又见李翠翠的娘提着一个包裹过来,直接把包裹装进箱子,说道:“这是俺给念书做得新铺盖,用的都是我家小子成亲剩下的新布料。”又见烧火的大娘捧着一个冒气地布包过来,把布包也放进箱子,说道:“这是俺蒸的馍馍,念书路上吃啊。”又见村中铁匠握着一杆毛笔递给黄念书,黄念书接过来发现入手沉甸甸地,铁匠憨厚说道:“这是俺打的,你拔一下笔尾巴就有一把铁钎子,带刃的,路上有山贼小偷,给你防身用,小心点,别把自己扎到。”不断有村民往箱子里装东西,箱子完全装满,盖子勉强能盖上。最后于秀才递给黄念书一个沉甸甸地钱袋,看着黄念书说道:“这是大家凑的二十三两零六文钱,路上吃喝坐车用。走吧,天黑之前能到郡城。”黄念书眼睛火辣辣的疼,两行热泪流下。扑通一声跪在众人面前,磕头行大礼,一却句话也说不出来。众人赶忙过来搀扶,说道:“哎呦,大状元的礼我们可受不起,快起来,别跟我们客气。”黄国邦一把拽起孙子,对他大声说道:“乡亲们对你的礼不用你还,你只要记得,做官之后莫要忘本,莫要忘了你是黄家村人就好,你做得到吗!”黄念书哽咽着,认真说道:“做得到,我黄念书绝不忘本。”黄国邦扶他翻身上马,在人们目送之中,黄国邦为孙子牵马,黄念书坐在马上背着满载乡亲们寄托的书箱,一老一小消失在丰谷县黄家村的乡路中。
少年今朝科考去,不知他载何时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