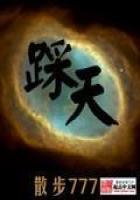过了年,便忙春事,眼看告一段落,龙少枢召沈冲天单独议事,问道:“家中一切还安稳吧。”
沈冲天知道哥哥所指,恭敬回答:“哥哥放心,惜宝不是那般不省事的,当晚就已经知道自己错了。如今在家中日日自省,剩下就是读书写字,颐养心性,不敢有违。”
龙少枢点点头:“孩子,是个好孩子,就是心思忒敏感些,像你当年一样。本来嘛,血气方刚年纪,刚从战场归来,又有战功傍身,也是心浮气躁的,关上他一阵,定定心气也好。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契氏不比寻常人家,也是目中无人习惯了!呵,谁料这次,刀刃抵在了牛角尖上,也给他一个教训。”
沈冲天揣测国主心思,不紧不慢道:“如今战事结束,边境上暂时没有动静,即使有一些小纷乱,我相信那些将领,不致让哥哥忧心。我归来快半年,当初听哥哥的话,休养身心,如今早就返本复原,不该再躲懒。今后若是朝中之事需要我尽力的,哥哥也莫要嫌弃弟弟身体不方便,年纪大,做不好。”
龙少枢笑道:“在我面前说‘年纪大’?你是借机嘲讽我吧,你啊!算了,说正事。这里就你我兄弟两个,说吧。”
沈冲天语气严肃地一一道来:“这颗种子是创国之初种下的,历经三四朝,早就盘根错节,各省各部皆有,表面看遮天蔽日,其实底下更加细密复杂,错综庞大,牵一发而动全身。若动静太小,不着痛痒,倒显得做事局促,没魄力,不如不做。若是想着不留后患,势必要深挖,难免带出好土好泥,根系尽,泥土亦空,白白留下原地一个深坑,到时恐怕朝野上下俱空,人人自危。臣弟担心此举于国基有碍,可置之任之,不闻不问,在如今更加广袤的国土之下,任由深根自腐于泥下,撼动国基,才是真正不负责任之举。老树成妖,倒不如拔除干净,重新栽种新苗,岂不更好!臣弟以为,依现在局势,动,则打草惊蛇,不如不动。暗底下广撒网,布下诱饵,等待最佳时机,一朝收网,一个都逃不脱。就是需要较长的时日,耐心静气,方可保万无一失。”
龙少枢故意皱眉:“絮絮叨叨半天,你在说什么?”
沈冲天立时回敬:“藏头露尾半天,哥哥又想听什么?”
龙少枢憋不住,忽而“哈哈哈”,放声大笑:“就喜欢你这样的,说话不吃力。你不知道,朝中好多人,要朕费心费力解释半天,才明白朕的心意;还要费心费力再解释半天,才明白朕如此心意之下,他们应该做什么。你深知我脾气,喜欢那等痛快豪爽,绝不拖泥带水的,深剜就深剜,没有点壮士断腕之气,焉能镇得住!我这样做,还有个自私的想法在里头。你、我,包括老六,对这些人还有些威慑之力,却一年老似一年,在你我之后,咱们的孩儿们能不能管得住这些人,我心里一直打鼓。你说的对,不栽树,无以遮阴;可树长得太大,遮天蔽日了,根腐了,就该伐!砍斫几根枝桠,没意思,经过一冬一春,又能再长,索性连根拔起。依你的估算,一齐收网,需要多久?”
沈冲天回答:“至多一到二年。”
龙少枢长叹一声:“傻弟弟啊,朝中事,不比军中,急不得!这些世家,可不是个个都像契氏那个熊孩子一般浅显懵懂,否则怎么能屹立百年不倒。他们不但彼此联络有亲,对外也是敞开胸襟,广纳门生,而且对于许多新贵,他们远比朝廷更懂得笼络人心。这还不算,他们所有人背后其实还盘踞一条大蛇,不撬动他,所有辛苦都是白费,岂止是撼动国基,还能撼动朕的龙椅呢!”
沈冲天忙问:“谁?”
龙少枢缓慢吐出几个字:“长公主府!”
沈冲天忽然有些泄气:“为何偏偏是他!”
龙少枢冷笑:“太上皇识人的本事也是一等一的,给最喜爱的女儿选驸马,自然更是千挑万选。莫说家世、性情、心机、聪慧,就是鼻子短一厘,眼睛小二分,哪里略次一点都入不了他老人家的眼,结果就给咱们留下这么一个太过聪明的麻烦。这还是在太上皇一朝,到朕这里,呵,朕的亲姐姐、姐夫,多好的一棵遮阴大树!现在回想,你不纳妃,也挺好,免去这些乱七八糟的事。”
沈冲天思索一番,犹豫道:“姐姐的病,时好时不好。眼看春风起,又是个犯病根的时月,如果一直难见起色,这边动作就要加快,一二年都用不了!”
龙少枢当即大惊:“放肆!那是我亲姐姐,你敢算计到她身上!”
沈冲天黯然:“唉!哥哥何苦来,那也是我亲姐姐,自小对我最好的亲姐姐!”
龙少枢闻言,静默一时,叹息道:“罢了,罢了!过来吧,以指代笔,把你的主意写在朕左掌上,朕也将想法写在你左掌上。比对一下咱两个心中所想,折中吧。”
沈冲天缓步上前,龙少枢左手抓住弟弟右手,摊开左掌放在他指尖下。沈冲天也摊开左掌递到哥哥面前。两人右手食指几乎同时在对方掌心起落,以同样的笔顺,写下相同的字。
龙少枢叹息着收回手掌,看沈冲天还是维持着刚才的姿势一动不动,关切地问:“在想什么?”
沈冲天回答:“其实哥哥早洞悉一切……”
龙少枢心知弟弟言语所指,不动声色地叮嘱道:“朕只有一句话交代,既知姐姐最疼爱你,别伤她,别的……”他挥挥手:“下去吧,你知道该做什么。”
沈冲天走到殿门,忽然听到身后一声:“弟弟回来。”
龙少枢起身走下来,站在沈冲天面前,忽然深深一揖。沈冲天听到衣袍响动的声音,伸手触到哥哥环抱的双臂,再向上探竟是俯下的半身,忙吓得跪在地上。
龙少枢扶起弟弟,情真意切道:“做哥哥的只希望弟弟明白一件事,弟弟与哥哥,其实是相互成全,唇齿相依。朝堂虽大,哥哥却无可依托之人,此举成败,只在你一身。哥哥在此先行谢过了!”
沈冲天终于吐出心中疑虑:“哥哥就不怕我……”
龙少枢道:“你是我弟弟,我了解。你有心机,却无野心。作为帝王,或是觊觎帝位的人,你从来不合格。”
从皇宫出来,沈冲天去了少桠姐姐的长公主府,自他出征,已经几年没见姐姐,确实想念姐姐了。
龙少桠在屋中,刚听到下人报:“齐王到”,话音未落地,就见沈冲天大踏步,轻巧利落地来到面前,言语轻快道:“外面大太阳晒得身上好暖,姐姐为何还憋在屋子里,也不出去除除霉!”
龙少桠不免笑道:“是幼弟来了,脚下小心些!怎么还是像个小孩子,走路蹦蹦跳跳的,也不想想自己什么年纪,该稳重些了。”
沈冲天轻声哄着姐姐:“什么年纪?八十岁,在姐姐面前也是弟弟!姐姐不知道,刚在陛下面前我可稳重了,端着架势,被哥哥拘了半天。好不容易到姐姐这里,快让我放松放松吧!来人,帮我脱了朝服,我要好好陪陪姐姐!”
龙少桠笑笑,只得顺从着:“好!既这样,你就陪我到花园里散散步,听你的话,我也除除身上的霉!”
姐弟两个在花园中慢慢踱步,龙少桠扭头端详着弟弟,不无惋惜道:“几年下来,白发又增好些,我的幼弟也老了,都是被陛下使唤来使唤去,生生累得!去岁秋,好容易盼着你班师回朝,却有一大堆后事等你处理,似我这等无事的,想见齐王都排不上号!眼见告一段落,又听说你在军中四年累坏身子,陛下让你在府里好好休养,无事不许别人打扰。我就又盼着新年,谁知临近年关,我却一病两三月,陛下为你庆功,摆好大的筵席,我也不能去。终于见到你,快让我好好看看,这接二连三的事,可委屈你了。”
沈冲天疑惑:“姐姐都知道?”
龙少桠点头:“你姐姐只是老了,不是傻了。大宴之上,你的义子和契氏的孩子大打出手,别说皇宫,都城中都传遍了,讲得那叫一个热闹!如今可平息了?”
沈冲天无奈:“真是‘好事不出门’!劳姐姐记挂担心,都是小孩子家,本就心性不稳,又借点酒气,第二日就没事了!宝儿一向都挺好,也是契氏那小子出言不逊,指桑骂槐的,惜宝为了维护我才动的手。”
龙少桠柔声劝解道:“不是我说你。我知道你身边子女少,惜墨那又成年,离你渐远,你的一腔父爱无处倾诉,全倾倒在这个义子身上。可这孩子毕竟不是你的骨血,又是中原人,到天狼时已经八岁,养不熟的!需要小心提防!”
沈冲天不爱听:“我也不是姨母的骨血,也是中原人!”
龙少桠仍旧和颜悦色:“你不一样,当年你到天狼时才满月,诸事不知,心性未定,吃着天狼的奶水长大,你就是天狼人!我这样说,是希望你分得清何为远近!契氏也好,其他几姓世家也好,那都是跟着老皇爷、跟着先皇过来的人,里面那些在或不在的长辈,都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为陛下打江山,他们为老皇爷、为先皇打江山,你们才是一类人!千万不要因为这些小事,就疏远他们,记恨他们。”
沈冲天听着话音不对,心中提防着问道:“姐姐今日何来此一说?”
龙少桠道:“我是担心啊!我天狼自创国一来,一直以稳妥为上。陛下不甘心只做个守成帝王,贪图一时所谓的‘宏图大业’。若只是惦记着外面的国土,倒还罢了,如今外境到手,四围安稳,也该松口气。结果陛下又盯上几大世家,长此以往,必将搅乱朝堂!你在他身边,要时时劝导才是,只有你的话,他还听得进去些。你自幼一向沉稳持重,如今可倒好,陛下要做什么,你都依着他!我担心,先皇费尽心力维持下的天狼国败坏在你们手上!”
沈冲天立时皱眉,制止道:“姐姐慎言!这话太重了!”
龙少桠索性点明:“我说得重?!陛下哪项决意被驳,你就舌战群臣!陛下要处置哪个朝臣,你就搜集证据!陛下要打仗,你就去领兵!你们不亏是‘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可你知道,朝中对于陛下的决策,对于你的行为,是如何沸议!群臣那些不堪入耳的话,真要我转述给你听吗!两个弟弟,没一个省心的!”
沈冲天极力压制着情绪:“姐姐!虽然姐姐当年也曾助先皇料理过国事,我以为从陛下做太子辅国之时,姐姐就全身而退了。谁知这么多年过去,姐姐还不放心陛下治国之力吗?如今的天狼,是陛下的天狼,别人无从置喙!这天下,只能一个人说了算!姐姐该明白,何为君,何为臣!否则,手伸得太长,耳朵听得太多,实在不利于姐姐养病!弟弟言尽于此,望姐姐好自为之!”
从少桠的公主府出来,沈冲天才真正明白龙少枢最后两句话的意味。在宫里,兄弟两个刚说完的悄悄话,就有风声透露到公主府中,甚至比他腿脚还快,这种无孔不入的渗透,让沈冲天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