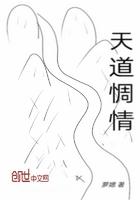她眼角眉梢都是淡淡的笑,叫人看着也有些开心。
陆明骄斟茶的手不停,放下杯子,给她娘一个眼风让打了霜的茄子似的月夫人坐下,见院门关上,这才淡笑:
“祖母又礼拜了哪处仙山的哪位道长?”
人都散了,坐下来她才有空去慢慢理顺脑中的繁杂。
她醒时只觉得有一股力道在狠狠地拽她,硬生生把她拽出壳子,留下一堆东西不曾带走。
醒的突然无措毫无防备。
迷迷糊糊里,只知道好像是自己受了伤所以才晕厥不醒良久。
可具体是谁伤的,想不起来。一去想便眼前昏暗头痛。
她只知道,这会自己应当是同那狗贼楚定澜在莽草山上打仗,怎地这会又在府里了?
莫非……
陆明骄想到了什么,身心都一沉,不过这时候却无法去顾虑那些事,将祖母应付过了才要紧。
她每每想到上一世祖母的惨死,心中便如千刀万剐。
是以这一世,陆明骄早早劝说祖母去外头修养。
老太太同寻常老人家一般,年纪大了便喜欢礼佛参道,陆明骄也由着她。
她在府里困了后半生,余生总该过得舒服些。
陆明骄从心事中回过神,面上还是从前一贯的淡然,与祖母谈笑。
老太太虽这几年也时常不得见这孙子,却也算是看着他长大,对于陆明骄的心绪变化,虽摸不完全,却也是有些数。何况她本就是个阅历颇深的老人家,看过的人无数。
不过对于这,她却并不会问破。
老太太,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往往都懂得什么叫深晦。
她于是淡淡一笑,似乎对孙子的问候相当高兴:
“是那玄真观里的一位小师傅,道名叫做静淞。年纪轻轻,祖母瞧着,与你一般大的模样。不过却是个沉稳又宠辱不惊的。听闻也是哪个大家的公子哥,不过慧根极佳,被那掌门收作关门弟子栽培。”
她接过陆明骄递来的茶,喝一口暂缓。
月夫人一直充当个木头人,面上却有些波动。
这个婆母,虽近年都不管府中中馈在外修身养性,却是个手段雷霆的。
后院里的那些个心思,镇国公到底是个男人,不懂应付。这婆母可就不一样了,那叫一个杀人不见血,软硬兼施。
她向来是很怕这婆母的,虽说她从未体罚她,以前也只是逼着她抄书学规矩,但那张脸一摆在跟前,月夫人就是不敢动。
这天生似的威压,叫她一个自小如野草自由生长大的边疆人压抑无比。
月夫人的印象里,这婆母也是话少。同她的早死鬼相公截然相反,也不知他们一对冰块脸夫妻怎么养出陆鹤庭那么个叽歪话痨。
她不禁瞧了眼陆明骄,杏眸里都是奇异的惊恐。
陆明骄接收了母亲的目光,心里忍不住无奈发笑。
她娘,不管是上辈子还是这辈子,都一如既往地怕她祖母,怎么都改不掉。
不过母亲的意思也不奇怪,陆明骄自己也对祖母今日的异样话多有些微妙。
她瞥一眼祖母泛着浅淡笑意的脸,不着痕迹地问道:
“祖母很喜欢那道长?”
老太太放下杯子,赞许似的点点头,抬眼盯住陆明骄,目光炯炯:
“此子良善,堪为灼灼之友。”她一顿,继续:
“祖母初闻消息,前日本就要回府了。奈何路上出了差错,鎏英那时又收了伤。若非静淞下山购置药材,我这老命约摸要去了大半条。
也是他推算出今日回府吉运上佳,喜也。
这不,当真就是件喜事。”
陆明骄细细听完这一通,了然点点头。玄真观大名鼎鼎,乃是一座道家名观。
位居栖凤山中一线天,历代掌门都颇有些推算之法,通晓天文地理,更出了几位国师。
又以门风好善乐施更闻名,是当地出名的活菩萨。
她虽不参道,这样鼎盛的道馆却自然是略知一二的。
想来那位静淞道长确有本事,也秉承门风,便也忽略心中异样不大去在意。
陆明骄于是点点头,不在此事上纠结。
“我已无恙,祖母回府疲了吧?过些日子我再着人将您送回去。”
老太太两只手交叠在一起,不说什么,只是笑眯眯地点个头。
若云侍立在一边,瞧着满眼欢喜。心道那道长还真有些灵通,居然算地这样准。
祖孙俩自然地闲聊一番,老太太终于心满意足。
她这才叹口气,沉沉看向低头不语一动不动的儿媳妇,满脸的恨铁不成钢:
“你儿子才醒,你就同个乡下粗妇似的告状?哥舒月,快要二十年了,你怎的永远没有长进?”
月夫人紧紧攥住手,半晌才结结巴巴地咕哝:
“媳妇,媳妇是急了点……”
陆明骄禁不住嘴角一翘,又迅速放下了。
枝头的鹂鸟叫地欢畅,却越发衬得老太太的脸黑如锅底。
她语塞一瞬,干脆转开眼睛望天,千言万语化作一句:
“……灼灼不像你当真是万幸。”
月夫人嘴巴一闭,干脆不说话了。
她心里不是不丧气。
回回自己也懊恼,怎么总是这样性子急没脑子还天真。
她也不是看不懂他们意思的,就是……就是回回禁不住激将……
回回……被坑。
婆母骂了她五年,最后干脆眼不见为净。
月夫人虽然心里开心,但也有些觉得对不住。
她要是也能每次都玩些心思,她和灼灼从前的日子过得应当也不会那么穷酸。
将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月夫人朝着婆母认真点点头。
这句话说的当真是很对,灼灼要是像她,他们娘俩约摸早被气地跳大江了。
她一字一句认真回应:
“婆婆说的对极了!”
“……”老太太抿嘴,吃了苍蝇般地看一眼她,扶了扶额头,只觉得再看一眼就要气晕过去。
陆明骄低头喝口茶,笑意快要藏不住。
日头正正好,燕来春草冒。
一年又一度,笑满普陀树。
早更头,便是喝茶谈笑。
二夫人一路逃似的回了见梅苑,急急把两女一儿塞进了房关上门。
她叮嘱一番什么却又走了,出来只是一个人。披一寻常布斗篷,径直寻到一处藏在巷子里的客栈,敲一扇门急急询问:
“天机师傅可在?我有急事求见!”
木门咚咚,却一直无人回应。
……
陆明骄醒了的消息瞒不住,也无人去瞒。
国公爷临时有事出了府,楚定澜也不在,只留下些人看着院子。
巧的是,陆明骄醒来的档口,刘子成正巧内急去了一趟茅厕。
一通排泄回来,只看见醒了的傻子和正常人似的同一个老太太说话。
自他第一回见陆明骄,便是个傻子模样。是以这印象先入为主,怎么都挥之不去。
来的路上他也听见了,都说他醒了已经不傻了。可他还是有些觉得不对劲。
这攀上枝头真正看见了,却愣了。
刘子成嘴巴圆的能塞个拳。
好像……真是不傻了。
这说傻就傻说好就好的?怎么和那些话本子里的不大一样?
他满脑子疑惑,不过任务在身,看见她无恙便也安心了些。于是懒懒趴在大树杈上看着这位殊华公子。
他谈笑间,举手投足里好似挑不出什么错,恰当又贵气,清浅又不敷衍。
只是这偶尔之间,隐隐有股不一样的气息掺杂着。
这混合在一起,刘子成不大看得出是个什么。
不解之中他轻轻下树,写一封短信在府外用鸽子传了出去。
陆明骄醒了一事,定要尽早告知将军。
金陵的大街小巷总是传满了各式消息,其中有一个又爆了,这主要人物,又还是那国公府陆四郎。
说是那陆四郎睡梦中被家中的二房三房逼宫气得大吐一口血,居然直接气醒了。
叫一直看热闹的人家又有了谈资,送去国公府拜门贴一下子堆满。
陆明骄拜别祖母坐在自己院子里,喝下一碗药,沉沉看一眼若云,面色无波眉头却紧皱:
“我记得,我应当还在同那狗贼打仗。为何一觉醒了身在府邸?”且这身上,还有重伤,内力大失,筋脉受损。
现在的她,与寻常武者无什么质的区别,而和从前,却简直云泥之别。
陆明骄虽沉睡一段时日,自己身体的异样她再清楚不过。
她这一问其实多余。只是心中,有些不想相信。
果然,若云的眼神闪了闪,慢吞吞捡了几件主要事说与她听。
房中的瓷铃叮当,若云的句子断断续续。
陆明骄听完,一张脸已经不能用黑来形容。
这面色,是黑青里的极致,锅底中的最中间,一锅粥里的老鼠屎。
她无论如何不敢置信,楚定澜竟是围剿了莽草山,将她救回敌营护送至金陵。
陆明骄周身骤然迸出一股子的煞气。
被死敌搭救,当真是再奇妙不过的滋味。
她屏退了若云,一人靠坐着,心中阴晴不定。
重来一世,又失败了……?
上辈子陆家灭门,她十四岁,用尽全部力气假死逃脱皇城的监控,而后去了漠北起义。
那一世,本该是成功的。
右手无知无觉地捏紧,力道大的简直能将骨肉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