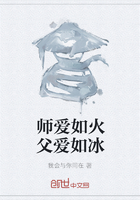话说那日胡笳在酒楼之中,偷听得一伙人夺书灭口之计,心下担忧徐府遭难,毕竟此事于己有所牵连,便欲往徐府一看,也好盘算如何应对。
胡笳从屋顶跃下,也不便往南山林而去,先市头上买一匹快马,驰到家中带了短剑同暗器,后结束行装,骑上快马,望南山林驰去。
怕惊了徐府之人,离得府上十里便歇下马来,任马儿食饱而去,自己步行至徐府墙外,照得上次依旧上了屋顶伏下。
胡笳竖耳细听,辨得人多处,房顶之上游离而去。
只见院中摆下几张案来,案上瓜果酒食一应俱全。上首一张案子前,胡笳辨的便是徐家老爷,余下四案分列两旁,胡笳瞧来一个也不识得,不过就身形衣着看来,多是江湖中人。胡笳心下稍宽,看来这徐家老爷算不得痴笨之人,此番消息泄露之后也知找来帮手助拳。
只见各人笑意浓厚,徐老爷举杯道:“此番徐家有难,多亏众位兄长挺身相助,徐某感激不尽。若非众兄在此,徐府上下尽人心惶惶,徐某代徐府上下满饮此杯,谢过众兄长侠义!”说罢举杯一饮而尽,众人举杯同饮。
左首一人道:“本自家兄弟,兄弟有难,何来袖手旁观一说?便是赴汤蹈火,我等亦在所不惜,谢字何来?百言如此言重,先罚三杯!”
众人大笑,徐百言连饮三杯下肚,道:“徐某此生有得如此仗义之兄,夫复何求,夫复何求啊!”
左首那人道:“我等来徐府多日,并不见人寻来。况愚兄已派下庄中弟子,四处打探而去,若有人意欲寻仇而来,必先来报,我等先做打算,待人上得门来,也有应对之法。百言大可宽心,今日之徐府,便是往日之徐府,一般而过。”
徐百言再谢,各自劝酒。王虎起身抱拳,道如厕而去。
霎时之间,胡笳只觉一手搭在肩头,心中大惊,亦欲起身,却发觉口不能言体不能动,内力全然提不上来,半分挣脱不得。
听得有人凑在耳边细声说道:“女娃娃莫要讲话扰了百言清净,我不伤你,你且随我来。”
胡笳心道:“你封我浑身窍穴,眨眼也不能,却来叫我莫要出声,不是羞辱我也?我自幼便习轻功,此人无声无息便至我身后,抬掌便治我动不得分毫,一生所见,除师父外并无第二人,我这等微末功夫不及万一,倘若此人要取我性命,十个胡笳也不够他杀。”
那人并不如何动作,手贴在胡笳肩头,二人便后退而去,飘然落地。并不停留,提着胡笳往林深处飞奔而去,约莫二里停下。
那人松开手,笑望向胡笳,并不言语。胡笳脱了束缚,转身便走,行不得三两步,定睛一瞧,那人却立在身前一丈。胡笳心中称奇:“此人内力雄厚,我万万不及,打是打不过的,逃也逃不掉。且听他讲出甚话来,再做打算。”
胡笳立住,道:“不知老先生拦我在此所为何事?”
那人笑道:“光天化日之下,越墙伏瓦而来,老夫心中奇怪,故来一问。不想姑娘落地便走,未解老夫心中之惑,故此一拦。”
胡笳道:“吾自幼喜动,做不得那大家闺秀,方才路过此地,见屋顶鸟儿嬉闹,心中喜爱,便想着捉了去。”
那人也不揭穿,道:“不知姑娘可捉得一二否?”
胡笳道:“此鸟甚是灵动,无奈在下手慢,不曾捉得去。若是老先生有意,自去捉来,晚辈要事在身,先行告辞。”说罢抱拳转身而去。
那人身形一晃,再拦在胡笳身前,盯着胡笳,只是笑。胡笳道:“前辈所问,晚辈已答。莫非心中另有它惑需解?”
那人道:“王某江湖厮杀一生,尚不曾对女子出手,姑娘自便。”此人正是通天棍王虎也。
胡笳一听话头不对,收起女儿心性,道:“如此是瞒不过前辈了,不过晚辈此番前来,并非做歹。早间城中听得恶人欲对徐府不利,常闻徐家乐善好施,方圆百姓皆言其善,晚辈幼年孤苦是亦受其惠,今日特来报信,望徐府早做准备,好来御敌。方才见得院中众多江湖人士,放下心来,刚欲离去,便被前辈带至此处。”
王虎心中似信非信,问道:“既善意而来,何不正入而告,要做那越墙伏瓦之举?”
胡笳道:“你道我一女儿家,非亲非故入此豪门大府,旁人得见,说出甚话来?徐家老爷食色之性,前辈心中必然有数,今日入府而去,旁人若嘴大讲出纳妾之语误了晚辈终身,前辈可赔得夫君来否?”
王虎哑然失笑,摇头道:“你这姑娘家伶牙俐齿道与我那女儿一般,此事且不提。你且说那甚人欲对徐府不利?”
胡笳道:“不曾识得,更不知姓名。瞧得那人黑袍黑履,手执黑扇,眼神阴鸷,面色苍白,话出口来甚细,女儿家一般。”
王虎点头,踱步道:“必南阳鱼休子无疑。传闻此人祖上问剑时死于徐酒歌之手,虽此人武功尚可,却多使阴暗招数。况为人阴毒,不行正事,不怪有此一行。”
王虎再问道:“此人之外,可有随行之人?”
胡笳回道:“怕有三五十之众,中有四人紧随,瞧来武艺不弱。”
王虎问道:“余下四人可识得?”
胡笳摇头,道:“不过面容打扮皆普通江湖人士,只有一人黑布蒙面,瞧来甚是奇怪,且并无兵器在手,晚辈瞧不出深浅。”
王虎思索,不得其解,猜不出此人身份,再向胡笳问道:“此行人现在何处?”
胡笳道:“距此二百里西城处,明日便来。”
王虎点头,心中了然,若是来得此人,尚且应付得去。
胡笳见王虎如此神态,想必信了,告辞转身离去,王虎再次拦下,胡笳道:“我好意递消息而来,前辈却再三拦我去路,如此便是徐府待客之道?传出去怕是遭天下人耻笑!”
王虎道:“此事尚未明朗,老夫辨不得真假。待明日事了,自放姑娘而去,今日暂且委屈一下。”
说罢,提起胡笳便走,越墙入了徐府,奔遮月房间而去。
王虎封住胡笳内力,找来府中丫鬟,吩咐道:“你且去院中唤我女儿遮月来,我在此等候。”
丫鬟得令,自去院中传话,须臾遮月便至。
遮月回得房里来,见屋中爹爹同胡笳,心中疑惑,问道:“爹爹,此人是?”
王虎解释道:“方才屋上捉得,不明来历。言前来报信,事关重大,爹爹未敢便信,不敢放任而去,别处又无处置处,现下封住其内力,你来看管,待明日事了,再做打算。”
遮月绕胡笳看了一遍,道:“此人生得面善,况又是女儿身,瞧来不似歹人。不过既然爹爹吩咐,女儿看住她便是,爹爹放心。”
王虎点头,道:“你且如此,我去同你几位叔伯商议对策。”说罢便走,去得院中叫来随行江湖朋友自回屋中商议,徐百言心中奇怪,也不便多问,自回书房再饮。
遮月见此人生得美,且又被封武功,自然毫无戒备,心中喜爱。便问道:“敢问姑娘姓名?”
胡笳此刻身不由己,见对方并无恶意,笑道:“叫我胡笳便是。不知姐姐名姓?”
遮月道:“胡姐姐唤一声遮月即可。我虽信你,可父命不可违,胡姐姐见谅则个。”
胡笳道:“无妨,待明日水落石出,自回还我自由之身。我一向山中深居,平日里说话之人也无,现下有姐姐陪着玩耍,我求之不得呢。有姐姐在此,胡笳有无武功,微末之事而已,姐姐不必挂怀。”
二人一来二去,熟络起来。遮月吩咐丫鬟置来杯盘酒食,二人兴致愈浓,屋中有酒有歌,言语合心,竟似知己一般,不亦快哉。当夜二人同榻而眠,夜半方睡。
竖日清晨,王虎天井之中摆下两案来,桌上无食有酒。一面吩咐弟子,在敌人来路等候,十里一人,出去百里。见人来时,往回递信,十里一报,依次而回。弟子得令,自去路上候着。余下弟子绕府三面而走,一方五人,防人暗中越墙。正门处留善言得体者迎客。如此吩咐停当,王虎自与众人饮酒,静待客至。
昨晚胡笳、遮月十分合意,姐妹相称,兴最浓时遮月自解穴胡笳,胡笳此刻已然自由之身,趁无人知晓,大可离去。不过胡笳一面想瞧热闹,一面怕徐府应付不得,那时再献出书来,因此与众人院中同立,不曾离去。
众人自候间,突然有人来报,对方已至百里处。不移时,又有人报来,已至九十里处。如此百里报至十里,每报一次各人心中俱是多一分紧张,只有王虎,眼神炙热,气势从一分直涨到十分。
日头正烈时,尘头起处,只见前方人马已至。迎客人上前抱拳,道:“阁下何来?”
执扇人冷面不改,道:“家中账本泛黄,今日特来算算。”
迎客人双眉微挑,问道:“新账旧账?”
执扇人眯起双眼,道:“既已泛黄,自是陈账。”
迎客人再问道:“此账可有算法。”
执扇人望向迎客人,马上微微欠身,道:“欠债者还钱,杀人者偿命!若你想平添新账,今日我一并给你记下!”
迎客人大笑,道:“吾自幼失了双亲,食百家饭而长,你道我欠下饭账几许?吾浪迹千建赌坊,你道我欠下赌账几许?我流连万间风月场所,你道我欠下情账几许?可谓债多不压身,今日阁下账本之上,只添一笔如何够耶?不若满写吾名,才不枉刀剑铸造之功。”
执扇人难得露出笑意,瞧来阴冷狐媚,不似男子,道:“既阁下有意,今日我便牢牢记下,待我行完正事,必来料理。”
迎客人全然不惧,道:“如此便好。家师早已恭候多时,请!”
执扇人下马入府而去,心下盘算道:“区区迎客之人便有如此胆识,看来徐府早已有所防备,今日之行,未必便能轻易功成。”
一众人随迎客人而入,到得院中立定,只见院中摆下两案,王虎正于案前端坐,笑意不减。王虎高言道:“来者是客,我已备下良酒,且先饮上三杯,以慰风尘。”
执扇人合拢铁扇,径直坐下,道:“往日多闻王大侠豪情万丈,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在下佩服。既然王大侠如此美意,鱼休子不便拂了去,请!”
鱼休子斟酒欲饮,身后一人阴恻恻冷笑道:“此番美意甚是好也,我等聚众而来,若在酒中下了药,毒倒了带头之人,也省去王大侠不少功夫,善也,善也!”
鱼休子低头嗅着杯中酒,道:“王大侠行事向来光明磊落,江湖中人莫不敬佩。如此下作手段,定然使不出来。你且退下,休得胡言!”
那人再欲讲话,王虎大笑出声,朗声道:“王某行走江湖一生,形正影正,讲礼者,王某以礼相待,讲力者,王某持棍一战,若是尖酸刻薄,阴阳怪气者,王某一概视如猪狗!”
那人气急,点指欲要骂出口去。王虎眯眼,面带愠色,道:“何况王某若想杀人,何须此等手段!”说罢望向那人,气势陡升。
鱼休子情知不妙,道:“慢!”
未等鱼休子有何动作,王虎伸手于案上酒杯一拂,只见那杯激射而去,那人来不及阻挡,正中眉心,登时毙命。
王虎环视众人,面色冷峻,冷哼一声,道:“区区小人,死不足惜。王某欲杀之人,何人能阻?”说罢转头望向徐百言,再道:“王某欲救之人,在座何人敢杀!”
鱼休子见王虎露这一手功夫,自知不敌,转头瞥向蒙面人,心中方定。举杯道:“洗尘之酒,如何不饮?”说罢一饮而尽。
王虎神色自若,方才杀人之事丝毫不放在心上,道:“待客之理已尽。不知阁下此行,是为讲礼,亦或是讲力来?若是讲礼,众兄弟远道而来,府上好酒好肉招待。若是讲力,王某手中镔铁大棍尚能一用。”
鱼休子脸色阴晴不定,心道:“今日我等上门而来,明眼人皆知此行非善。我还不曾发难,他倒先问起话来。此人自恃武功过人,全然不把我等放在眼里。我自然不是对手,可身后之人十招便能败我,为何听此言语也无动静?既然如此,我且先看。若能激起此二人动手,待两败俱伤之时,我再见机行事,此法最好。”便对王虎道:“为徐家先祖而来。”
王虎道:“此事倒也好办,徐家先祖已殁多年,若你有甚话讲,自去府中祠堂,牌位尚在。如若不然,自去黄泉之下寻人,或能见上一面。”徐百言心知王虎此言意在杀对方锐气,因此并不觉对家祖不敬,是以不曾言语,依旧立在一旁。
鱼休子不怒反笑,道:“既徐家先祖已殁,自不必寻他。有甚话说,自找徐家后人。既能子承父业,父债亦能子还。”
王虎见对方挑明来意,也不含糊,问道:“徐家何债于你?”
鱼休子道:“家祖当年仰慕徐氏先祖剑仙风采,不过上门问剑讨教,不料徐氏先祖出手毫不留情,杀吾先祖于剑下。敢问王大侠,此债尚能讨否?”
王虎道:“你欲何为?”
鱼休子开扇轻摇,道:“既徐氏先祖已殁多年,且在下本意并不为杀人而来,况今日王大侠在此,既你已以礼相待,我看王大侠面上,亦不能祸及其后人。现下若是交出酒歌剑谱,待我去家祖墓前祭酒烧之,一慰了家祖在天之灵,二来大家亦不致伤了和气,此事便了。”
徐百言听此言语,站出身来,怀中早已备下一物,此时取出与众人看了,道:“家传剑谱已被贼人盗了去,此字便是贼人所留。倘若为剑谱而来,众人白跑一场也。”
鱼休子冷笑连连,道:“凭此区区一张纸来,便想我等就此离去,徐老兄异想天开了也!况此事真假,我等如何辨得。徐老兄若作得假来,也未可知!你徐氏家祖不讲礼,后人也不讲礼么?”
徐百言道:“此事千真万确,百言不曾作假。如若各位不信,百言别无他法。众位自去找家祖罢!”
鱼休子脸色突变,眼中迸出杀气,道:“如此说来,徐老兄是打算不给了?好!那便血债血偿!徐酒歌,你杀我先祖,今日我便杀你后人!”
未等徐百言开口,王虎接过话头,道:“百言所言非虚,剑谱确是被人所盗。若合不得你意,要打也可,要杀也罢,一并冲王某来,王某人今日一并担着!不过凭你的功夫,在王某面前还不够看,尔等最好一齐上,否则王某施展不开手脚。”
鱼休子一掌击碎身前桌案,长身而起,怒道:“吾敬你是江湖前辈,再三忍让,你却如此咄咄逼人,全然不将我等放在眼里。徐家杀我先祖在前,今日你王虎辱我众兄弟在后,虽鱼某不才,却也要讨教几招。”
王虎推翻桌案,从弟子手中接过镔铁大棍,重重杵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石屑四溅,点指道:“一群土鸡瓦狗耳,王某一棍砸下,便能砸死一片,倘有不信者,尽管来试试。”
此时只见对面一蒙面人走上前来,嗓音嘶哑却直透人心,道:“哦?王大侠既有如此雅意,刘某便来领教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