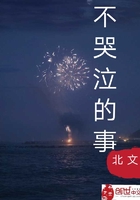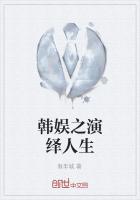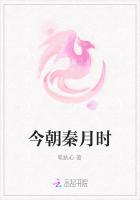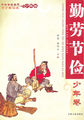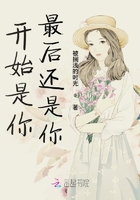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现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韦伯的知识范围和学术研究视野非常广泛,从经济、政治、法律、宗教、音乐等社会生活领域到社会科学方法论都有重要成果,对西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与卡尔·马克思、爱因斯坦一起被称为“对世界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三个德国人。”
影响世界的小人物
马克斯·韦伯无疑是个影响了世界的思想巨人,如今无论在哪个国家马克斯·韦伯,只要是研究社会学,就必然会涉及到马克斯·韦伯的著作。但在他身前,他的名声却远逊于身后,并且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甚至不为他的故乡德国人所看重。一直到60年代,由于美国一些学者的发掘,韦伯的理论才重新为人们所重视。此后,对韦伯的研究越来越多,这座庞大的思想矿山终于为人们所发现和广泛利用。
有一个事实或许可为韦伯声誉的巨大变化提供一个有趣的注脚。慕尼黑市有一个“马克斯·韦伯广场”,人们以为这理所当然是为了纪念这位社会学家的。但事实上,这个广场最初是为了纪念一位也叫马克斯·韦伯的慕尼黑市议员的。他死在思想家马克斯·韦伯之后。后来在慕尼黑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贝克教授建议将这个广场只以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命名。在参考了贝克等人的建议后,慕尼黑市政府终于做出决定,“马克斯·韦伯广场”是为了同时纪念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市议员马克斯·韦伯而命名的。
韦伯生前生活并不如意,他曾想参加政治,希望成为一个政治家,试图在选举中一展抱复。在1919年1月的国民议会选举中,法兰克福选区提名韦伯为民主党候选人,但没成功。他自己申请成为国会候选人没有得到同意。后来有人考虑让韦伯做内政部国务秘书,还有人提议让他做驻维也纳大使或者民主党委员会委员,但韦伯最终没有获得任何职位。他只是作为十三位成员之一,参加了一个非官方机构,负责就制定宪法草案问题向内政部提供咨询建议。
在学术上,他在大学教书多年,但长时期是见习讲师,正式当上教授的时间不多。他热衷于社会学,但大学要求他只讲经济学和政治学,他只好在讲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时候插入自己社会学的研究。
韦伯还患有精神分裂症,曾经一度被迫离开岗位去疗养院休息。他与家人的关系不好,和妻子常年没有性生活,与他的父亲关系更是极其恶劣,就在他父亲去世前两个月,韦伯还与他父亲大吵了一场。这场没有和解的争吵最终成为了韦伯终身的遗憾。
众神时代
韦伯是一个对现代社会提出深刻见解的哲学家。他深刻地指出,现代社会与古代社会的区别,并不仅仅是在时间先后上的不同,而是从最本质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韦伯将现代社会叫做众神时代的重新降临,所谓众神时代是指原有的统一的价值观消失了。在现代社会并不存在也不需要一个为所有人共同信仰的价值观念,但是整个社会仍然通过官僚制度和技术手段紧密地统一起来,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不再拥有共同信仰基础。在韦伯看来,传统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整个社会信仰一种统一的价值观,比如西方社会对基督教的统一信仰,中国社会对儒教的统一信仰,这被他称作一神时代。而资本主义的兴起,从根本上打破了这种共同信仰的时代基础,它不再是用一个另外的神来取代原有的神,而是彻底宣布众神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但能够同时为社会所容纳,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本质特征。
基于这一分析,韦伯提出著名的价值中立的观念。在他看来,在现代社会,各种价值观共同存在,也无法判定那一种价值观能比其他的价值观更加高明。因此,作为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应当不受到价值判断的影响,而要客观、公众的去进行研究,做到价值中立。在一次演讲中,他明确地提出教师在授课时不应当用自己的价值倾向去影响学生,教师的作用只能是告诉学生有哪些价值观念,但不应当告诉学生应当去选择哪一种价值观念。韦伯对现代社会抱有一种颇为失望的心态,在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他最后写下了这样一段为人们经久传诵的段落:
“没有人知道将来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思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也没人知道。因为完全可以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由于不需要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念,人类的生活方式越来越趋向于工具化。人越来越像一台机器一样,每日按照社会的准则去生活,但却缺乏精神上的追求和信仰。人们越来越只考虑到现实,天堂和地狱被人们视为虚妄。科学在惊人的发生着进步,经济每一天都在不断增长,但人类的精神追求却越来越来浅薄、越来越虚无,最终只剩下精神的荒漠。这种现象令韦伯感到深深的担忧,他只能抱有一种悲观的心态来面对世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