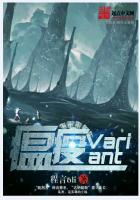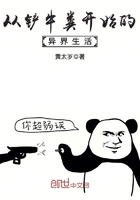表示上升和下降、上升或下降、上升和下降的无穷无尽的符号,必须归功于探索世界的高度和深度的迫切需要——人类、自然和神。人类超越了所有其他动物,超越了空间垂直维度的极限,使它对人类和上帝都一样真实:“如果我升入天堂,你就在那里;如果我在地狱里铺床,看,你就在那里。”
我若展开早晨的翅膀,住在海极。
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搀扶我”(诗篇139:8-10)。
山、塔、树和梯子都是人们上升的手段,也是上升和下降的象征。人类是一种努力到达天堂却落入地狱的动物(人属上升,人属下降),当我们使用这些符号时,我们意识到我们上升,我们下降。这方面的文化证据是象征符号的持久吸引力,圣经先知们用这些符号来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拜占庭、罗马式和哥特式建筑师在他们的设计中使用这些符号,后来教堂在他们的塔尖上展示(Patrides,“等级”)。但丁的《神曲》是表达犹太-基督教等级观念的重要作品之一,它向平面艺术家提出了挑战,要求他们描绘地狱深渊、炼狱之山和天堂的层次。在二十世纪有许多关于但丁的插图,就像之前由乔瓦尼·迪·保罗、桑德罗·波提切利、威廉·布莱克和古斯塔夫·多尔所画的一样多。这种神的等级制度也存在于古希腊,它把哈德斯描绘成神所享受的地狱,奥林匹斯山是他们的家。
和其他会动的动物一样,人类也会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很少平坦的空间和景观之中。山丘和山脉逐渐升高,土地倾斜成山谷。为了获得对土地的控制权,山顶使人们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景象,而山谷,无论多么令人愉快,都是一个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如诗篇23章“死亡阴影的山谷”)。人类建造高塔,通过挖沟渠来保护高塔,从而扩大了环境提供的高度和深度。每一种文化都有一些圣山,在那里,像摩西这样的先知会上升到上帝面前,接受律法的石板。每一种文化都有山谷,有时是被诅咒的,就像耶路撒冷城外的山谷一样,那里有肮脏的城市垃圾场托斐特,在希诺姆山谷(列王纪下23:10;以赛亚书30:33;耶利米7:31-33)。原始部落相信天上的云是神的住所,而地狱的深渊里是魔鬼。人们生活在一个中土世界,在天堂和地狱之间,在那个模糊的领域里善与恶是混合的,所以每个人都不断地面临着他们之间的选择。最引人注目的人类道德困境的这一普遍特征的一个例子是,长期以来的传统是把亚当和夏娃描绘在善恶知识树下,并把他们逐出天堂(创世纪2-3)。马萨乔和米开朗基罗分别在佛罗伦萨的布兰卡奇教堂和梵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创造了这一场景的两个伟大的例子。
一般说来,上升的程度越高越好,下降的程度越差越好。但也有一些视觉上的上升象征无法成功,因为建造巴别塔(Tower of Babel)仍然是野心勃勃的象征。占据神的位置会造成语言的混乱(创世纪11章)。希腊神话中的奥图斯和埃菲亚耳忒斯是两个巨人,他们为了到达众神的家园而把山核桃堆在一起,这也显示出狂妄自大的后果。希腊诸神惩罚西西弗斯在哈德斯的许多欺骗行为,他永远谴责西西弗斯把一块巨石滚到山上,结果巨石在到达山顶时又滚了下来。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象征主义的崛起可能只是骑着财富的车轮向上走,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衰落和毁灭。
善与恶的终极关键在于生与死。自然世界提供了光明和黑暗的象征,作为善和恶的相关字符,因为上面是光明的来源,特别是太阳,没有它就没有生命。因为黑暗只是没有光,所以很自然地认为存在本身是好的,而邪恶最终是虚无的。
存在的层次可以建立在自存的存在与一切在它之下并依赖于它的存在之间,与偶然性相对的是必要的。这一范围,包括一切对立的东西,精神的-物质的,活着的-死亡的,智慧的-野兽,都是抽象地用象徵树来表示的,并且主要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书籍中作了图解。不幸的是,最有名的书是《伟大》,《生命之链》阿瑟o洛夫乔伊著(剑桥,马塞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36年),思想史上的一部杰作,除了荷马的《金链》,对视觉艺术只字不提。链条的少数例子都来自文学作品。
生命之树以许多不同的形式散布在世界各地。挪威人描绘的世界是一棵常绿的白蜡树Yggdrasil,居住着由白蜡树和榆树进化而来的人类。神话中的生命之树是真的吗?因为所有的物种都可以被认为是树枝,而树干是从普通的树根长出来的。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指出,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尤其是在其早期章节中,使用生命之树作为指导,来解释大量观察到的亲缘关系事实。
在另外两个方面,垂直维度的符号在现代世界和中世纪一样被广泛使用,在那个时代,艺术家们受到了比我们今天更深刻的启发,去使用天堂和地狱的象征。经济上的成功是靠爬梯子获得的,而铁轨和梯级有时可与美元(美元)螺旋形的象征相比。我们仍然在视觉上代表着拥有自己的家或晋升为首席执行官的步骤。反对唯物主义的反应也采取等级形式,因为灵性被认为是超越感觉而进入知觉,从想象而进入理智。精神的提升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内在的发展,超越了计算理性,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欣赏和献身于理想。特别是,卡尔荣格的深度心理学在古代神话、神学、炼金术以及使用山、塔、树、梯子和桥的符号的艺术中找到了意义。精神自然地寻求上升,就像火星向上飞一样。令人怀疑的是,对象征主义的关注是否会发展成一种反感,即反对把所有生命都降低到死寂和单调的水平,从而剥夺我们被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称为“高峰体验”的体验。
在讨论山、塔、梯、树的意义时,我们会注意到,虽然这些符号可以在非常不同的文化中找到,但它们独特的宇宙观和道德内涵,与荣格思想主张一个基本的潜在外延的融合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许多解释器发现埃森的意义在一个原型的上升和下降:中心和世界轴,在肖像哲学的米尔恰埃利亚德。
拯救有时是下降到地球母亲的子宫,而不是上升到天父。即使在西方文化中,奥林匹斯山是宙斯和其他希腊神的家,西奈山是与以色列神立约的山,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人都认为山是好的创造物的瑕疵(尼科尔森)。
山
当以色列人在锡安山的耶路撒冷对他们的圣殿做鬼脸时,他们得到了可以唱赞美诗的机会。有15首“上升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一节至今仍被远离圣地的人和不是希伯来人后裔的人用来敬拜:“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山而来”(诗篇121:1)。这只是许多这样的表达之一。它出现在中国字的绘画中,描绘的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印度有梅鲁山,印度教徒、佛教徒和耆那教徒都认为它是世界的中心。从这个中心展开四个荷花花瓣大陆,这座山就是世界荷花的种子杯。从古希腊开始,我们就知道了一些建在海岬上的庙宇,比如雅典卫城顶上的帕台农神庙。对许多美洲原住民来说,这座山本身就是神。日本人也庆祝富士山,因为它的泉水为稻田提供水源。
正如马蒂亚斯?格伦沃尔德(Matthias Grunewald)的《伊森海姆》(Isenheim)中画板所描绘的那样,山顶是一个有着崇高愿景的地方,祭坛的装饰品。探险者们常常讲述他们欣喜若狂的经历,哈德逊斯卡德和其他三位探险者也是如此。1913年,他们第一个登上了阿拉斯加州的麦金利山。因此,我们可以对摩西带领希伯来人从埃及来到西奈山获得共同的感情。耶和华的能力表现在风暴、火和闪电中。人们必须留下来,等待先知摩西的回归。
摩西最早接受早接受来自上面的法律是在杜拉欧罗巴会堂的壁画上,来自上面的律法是在杜拉-欧罗巴会堂的壁画上,现在在叙利亚(公元三世纪)。摩西登山的形象成为拜占庭绘画的标准,尤其是因为查士丁尼皇帝在西奈山脚下建立了圣凯瑟琳修道院。意大利拉文纳的一座摩卡- ic山,呈现出一座从一层到另一层陡峭下降的高山,让我们想起美国僧人托马斯·默顿(Thomas Merton)在他的汽车传记《七层山》(the Seven Storey mountain, 1948)中使用的隐喻。
摩西上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必须留在下面的高度。在犹太和拜占庭艺术中,只有上帝之手从天上的云彩中显现出来。据说摩西在高处禁食40天40夜后,“面对面”对主说话,但在其他经文中,摩西只能看见主的背影。摩西被授予圣人的光环,在12世纪到18世纪的西方艺术中,他的额头或脸颊上有角,就像鲁道夫·冯·埃姆斯(Rudolf von Ems)的发光手稿中那样。肖像学家Ruth Mellinkoff将其解释为圣杰罗姆翻译的希伯来语“长角的脸”。我们现在同意传统的希伯来语和希腊语的解释,更正确的意思是摩西的脸容光焕发。摩西向百姓展示律法石板的时候,很少蒙着脸。
在漫长的等待中,人们变得不耐烦了,因为他们在等待耶和华的圣约,并劝诱摩西的哥哥,祭司亚伦,把珠宝熔化成一只金牛犊。这通常表现为一个偶像设置在一个柱或纪念碑平台。这一场景是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画家的最爱,也许因为尼古拉斯·普桑而广为人知。因为文字讲述了以色列的道格人围着神像唱歌跳舞,画家有机会描绘了一场狂欢。摩西是在愤怒中出现的,因为他的人民对偶像的不忠,摩西在愤怒中打碎了石板,这是摩西循环的一个标准章节。其中最有名的是伦勃朗·范·瑞恩(Rembrandt van Rijn)的《柏林国家博物馆》(Staatliche Museen)。
意大利威尼斯圣莫伊兹的祭坛可能是基督教教堂中独一无二的。石头堆起来就是为了复制一座山,父神把律法赐给先知摩西。他们都是留着胡须的族长,被天使簇拥着小号。在山脚下站着兄弟亚伦在左边,妹妹米利暗在右边。
亨利·契弗·普拉特(Henry Cheever Pratt)的《山上的摩西》(Moses on The Mount, 1828-1829, for- merly归于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体现了现代人对山野风光的热爱。这项工作是不寻常的,因为人的形象是微小的,在宏伟的山以上的先知和祭司侏儒。保罗·塞尚(Paul Cezanne)迷上了附近的圣维克托瓦尔山(Mont saint - victoire),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他多次画这幅画。对山的迷恋在1977年的电影《第三类近距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中或许得到了最生动的现代处理。全国各地的人们似乎都是随机挑选出来的,他们对一座山的形象着迷,并对它的意义进行了无所不包的追求。他们的探索以一个外星种族在山上与地球接触而告终,这也许是一个与主显节类似的世俗现象。
山上的石头,由上帝的手指上刻有十诫,并没有在最早的描述中发现。古人知道在卷轴上写字,只有到了中世纪摩西才带着圆圆的石头出现。犹太学者已经确定,这个形状被称为圆规顶,最初是由基督教艺术家设计的,并被犹太教堂借用,在那里它已经成为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最常见的象征(与以色列使用的六角形马根大卫形成对比)。
塔
人们在世界各地建造了人造山,包括埃及的金字塔坟墓,墨西哥阿兹特克人祭祀和崇拜的金字塔,以及底格里斯河流域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金字型建筑。所有这些都是达到高度的令人敬畏的手段,有些有上升的步骤,有时严格限制使用祭司或皇室谁达到神圣的高度。
在西方艺术中,塔最重要的象征不是与能否到达天堂有关,而是与人类的失败有关。巴比伦塔的故事在圣经中被重新叙述为巴别塔,现在巴别塔象征着语言的混淆。《创世纪》中提到巴比伦人的意图:“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创世纪》11:4)。这个故事来自希伯来人,他们相信他们的真神已经带领亚伯拉罕离开了迦勒底的吾珥,离开这座以塔而闻名的城市是合适的。与真正与上帝的接触相反(就像雅各和他想象的从天上掉下来的梯子一样),试图建造一座通向天堂的塔成为了人类骄傲的象征,随之而来的困惑也成为了无意义的象征。希伯来人的抄写员也拒绝巴比伦的创世故事,这个故事涉及到男女神的交合,以及通过国王和女祭司的神圣婚姻仪式在塔顶的圣殿里模仿创世。
梯子的标准结构可能在宽度上有所不同,在高度和角度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与之相反,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艺术中所表现的塔身有更大的多样性。有时它被描绘成早期的砖结构,就像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马赛克,但更常见的是,它的高度可以达到天上的云。有时它是一个直立的塔,正方形,有窗户来表示内部的楼层,但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建筑,通常有一个螺旋楼梯通向楼上。通常会有工人使用脚手架的迹象,因为塔还没有完工。有时它有许多四舍五入的建筑物,因为圣经上说它是一座“城市和一座塔”。在老简·布鲁盖尔(布鲁盖尔·德)的版本中(丝绒)1625年以前画的,有两条河和一个繁忙的城市,看起来像一个岛屿,后面有山。在古斯塔夫·多尔(Gustave Dore) 19世纪的版本中,重点放在穿透云层的高度,而异教崇拜占据了前景。有时,这个高高在上、永不完工的建筑的总体主题是控制——由表现国王宁录(Nimrod)的某种傲慢姿态所迫。另一种指出骄傲之后是毁灭的寓意(箴言16:18,29:23,等等)的方法是展示一个巨大的建筑倒塌成废墟。
这座塔并不总是糟糕的上升和失败的象征,事实上,它有时恰恰相反。塔通常意味着无懈可击的纯洁。圣巴巴拉,被她的父亲监禁,以保护她的基督教贞操,经常被描绘成一个塔。这也是圣母玛利亚的象征。象征圣人的塔可能有三扇窗户,象征着神圣的三位一体。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使用了塔状山的象征,通常有一条可以用来攀登云层之上高度的外部伸展路径。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塞贝斯石碑经常出现。塞贝斯是苏格拉底的学生,也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者,也是《斐多篇》的演讲者之一柏拉图。他的表格文本来自新柏拉图主义的manu-公元前一世纪的文字。它解释了克罗诺斯神庙墙上的一幅巨幅画。故事讲的是一个人在路上旅行,参观了这座寺庙。根据寓言,生活的意义在于学会分辨真假,善恶,以及处理坏运气的方法,尽管所有的不幸,最终获得幸福。有27个教训要学习,和照明引导通过螺旋上升到寺庙的顶峰。
塔可以作为士兵征服目标的象征,也可以作为学者征服目标的象征。在令人生畏的高地下面的平原上扎营的民兵学者们是各种各样的帐篷(邪恶的帐篷?):无知、懒惰、快乐、恐惧,还有三种。上升的步骤是七种艺术,从语法、逻辑和修辞开始与象限形成对比。将要采取的外墙是学士学位,之后是硕士学位,在“arx Palladis”(智慧城堡)的中心坐着一位统治者,他的旗帜上写着“荣耀”。
树
就像高山和高塔一样,我们赖以生存的树木和我们用来攀爬墙壁的梯子是上升和下降的象征。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他的诗歌《桦树》(Birches)中总结了“树之巅”的概念:
我想去爬桦树,
爬上黑色的树枝,爬上雪白的树干,走向天堂。
比爬上枝头的树的上升更深刻的是用来象征灵魂上升或下降的各种树的形态。一棵树是人类历史上灵魂堕落到原罪的最恶劣的工具,从宗教的角度来说。秋天的文字,据希伯来圣经记载,其中包括“伊甸园东边的一个花园”,就是主耶和华“安置那人”的地方。耶和华神使地长出各样悦人眼目的树,又长出各样可作食物的树。园中有生命树,又有分别善恶的树。“上帝把亚当在伊甸园”穿着它,让它,“每——吃的每棵树只有一个任务,是被禁止的:“每一个你可以随意吃花园里的树木:但是,分辨善恶的知识树,你不可吃,因为你一定会死”(创世纪2:8-17)。阿尔布雷希特·丢勒(Albrecht Durer)在《善恶之树》(the Tree of Good and Evil)中描绘了夏娃受到蛇的诱惑,而亚当则手持生命之树。
这个花园成了艺术家们的最爱。这棵树象征着万物未受破坏的美丽,根据造物主的说法是好的(创世记第1章在大多数日子的创造之后重复了“上帝看见它是好的”)。亚当和夏娃在触摸禁果之前是完美的。上帝命令男人和妻子“成为一体”。他们都赤身裸体(创世纪2:24-25)。夏娃和亚当屈服于蛇的诱惑:“你们不一定会死,你们会和神一样,明辨善恶。”吃了果子,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这才知道是他们裸体。他们羞蒙神的面,就藏起来。他们被指控违抗命令,并提供借口;亚当责怪夏娃,夏娃责怪蛇。上帝诅咒男人耕耘石质的土地,诅咒女人在痛苦中生育孩子。耶和华说,人“与我们成为一体,能分辨善恶”,却注定要死,因为他不能取生命树的果子吃。
有一位天使,手里拿著燃烧的剑,永远阻挡人走“生命树的路”(创世记3:4-24)。
并不是所有的神话都像失乐园的故事,甚至在希伯来圣经中,寻找它的人也能获得智慧:“她是抓住她的人的生命树,凡留住她的人都是幸福的”(箴言3:18)。这是一个opti- mistic版本,人们保留,甚至增加他们的capac-智慧,如果他们选择使用他们的手段是他们的。但受圣保罗影响的正统基督教版本认为,亚当的罪使所有后代在道德上变得软弱和畸形。只有通过第二个亚当基督,才能得到救赎。救主的牺牲之死是在十字架上,这解释是十字架是死树的木头做的,死树的果子是第一对吃的。十字架的地方,各各他,就是亚当的坟墓。堕落的逆转,由第一个女人发起,需要第二个夏娃,耶稣的母亲马利亚,当诱惑通过瑟宾特(撒旦或恶魔的象征)女人的脚,蛇的头(创世纪3:15)。
如果凡人上升到神的层次的途径是通过智慧,那么生命之树也是善与恶的知识之树。有时这两棵树被明确地标识出来(例如萨尔斯堡大主教伯恩哈德·冯·罗尔的弥撒书)。那些坚持波林关于亚当堕落的学说的人自然会把那棵禁果的树当作死亡之树。
东正教的故事,通过十字架上的死亡来救赎,有时把垂死的救世主放在树上,象征着新的生命从牺牲的生命中诞生。
十字架就像树一样,让被救赎的男人和女人得以复活,与神和好。对十字架的沉思是一种承认亚当不服从罪的方式,也是一种向基督徒宽恕敞开大门的方式(席勒)。
耶西的人类家谱是由耶西的中世纪树sym- bolized,最著名的是在法国沙特尔大教堂的彩色玻璃。从耶西到大卫,一直到赞美诗中所称的“大大卫的大儿子”。这是为耶稣作为弥赛亚,或“受膏者”,“基督”称义。
树的象征是中世纪历史反思的核心。最主要的例子是费奥雷的约阿希姆,卡拉布里亚的方丈,他的救赎计划是圣子时代从圣父时代出现,并在一个新的时代,即圣灵时代实现。方丈的愿景被渲染成树木的繁茂。
在对宇宙的系统思考中,没有一个形而上学家比加泰隆骑士、小说家、方济各派***传教士、神学上的极端理性主义者拉蒙·鲁尔更多地使用树的部分。早在Blaise Pascal和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之前,Lull就有了计算机的想法。在一个基本的问题中,他问了根、树干、树枝、树叶和果实。绘画和约阿希姆的预言一样,伴随着他的形而上学。树叶有时被命名为亚里士多德的美食在一个分支上,在它的镜子对面是他自己的系统的现实的主要方面的名称。鲁尔为牧师们写了一本书,在书中他教他们把爵士想象成一棵树,并跟随这棵树从根到果实的生长,以确保每一个方面都得到了覆盖。
然后树成为整体的象征,而存在之树被设计成所有实相的象征。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笛卡尔说“类别之树”或将“整个哲学”比作一棵树在他的哲学原理》(1644),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美索不达米亚的丰富的文化遗产,埃及,和印度教神话,以及工厂——ulous宇宙树的北欧神话。在启蒙运动之前的几个世纪,逻辑文本使用了一种多种多样的图表,一种存在树。这要追溯到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斑岩(Porphyry),他于公元232年左右出生于泰尔(Tyre),编辑了普罗提努斯(Plotinus)。存在的基础是“一”,其他一切都是“一”的散发。宇宙最普遍的范畴是物质,如果物质是肉体,如果生活是生命,如果感觉是动物,如果理性是人,那么物质就是人。人,凭借他的灵魂和智慧,可以逐渐地达到“一”。这是后备箱。这些树枝在左右两边分别代表着心-非物质的或有血有肉的,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有感觉的或无感觉的,理性的或非理性的。其中一种变体显示,homo(人)起源于最初的一对,亚当和夏娃,基督教男子源于再生的一对,耶稣和玛丽。另一幅则展示了人类紧紧抓住存在的根源。
这棵树是否永远扎根于地下而生长,向着光源向上?乔木普遍性由于其对分类的关注,从矿体到植物再到动物再到人,每一种后退水平都是较高的。在东方和西方都有一棵倒挂的树。来自《奥义书》(6:1):“它的根在上,它的枝子在下,这就是永远的无花果树。那根确实是纯洁的。这就是梵天,它确实被称为不朽,所有的世界都在上面休息,没有人超越它。”
其中最有趣的一棵树是由塞比罗斯树发展而来的,塞比罗斯树是神的十个名字,神秘的犹太人在这棵树上聚集起来,想要上升到永恒。这十个名字,三个在根的中心,七个分支,是棕榈树的叶子。
梯子
正如圣经故事中的巴别塔要求我们承认象征的巴比伦遗产一样,雅各在伯特利的梦中梯子的故事也要求我们承认古埃及的象征。希伯来语拒绝建造通向天堂的塔已经成为虚荣和随之而来的困惑的象征,而从天堂下来的梯子才是连接地球和天堂的真正途径。
要理解从杜拉·欧罗巴犹太教堂到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的许多画作,我们需要故事的文本。雅各遵着他父亲以撒的命,不娶迦南人为妻,要在他母亲兄弟的家里娶妻,就往哈兰去。
耶稣偶然到了一个地方,因为日头已经落了,就在那里住了一夜。就从那地方取了石头来,枕在自己的枕头上,躺在那里睡觉。他梦见一个童子,立在地上,地的上头达到海恩,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地上。简体中文和合本(cuv simplified)耶和华站在其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父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所躺卧的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并要在你和你后裔身上,地上的万族都是有福的。我与你同在,必在你所去的各处保护你,又领你回到这地。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这地方多可怕啊!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这就是天的门。(创世纪28:11-17)
雅各就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他把油倒在一个叫伯特利的地方,就是“神的殿”的记号上(创世记28:18-19)。作为上帝存在的象征,另一个垂直的纪念碑被使用,柱子。
希伯来语中梯子从地面爬到天堂的故事被基督徒所接受,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可以建立在埃及和希腊的意义上。埃及人戴着梯子的护身符,俄耳甫斯的崇拜提供了一个梯子,可以把灵魂带到天堂。最重要的发展来自西奈山脚下圣凯瑟琳修道院的院长约翰。方丈用雅各的梯子作为道德完善的象征。修道院院长约翰内斯·克里亚库斯(St. John of the Ladder)将他的哲学写进了一本30章的书《天堂的阶梯》(the Ladder of Paradise),每一章都是阶梯上的一个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