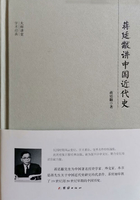中秋节那天半夜,下街南边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枪声,满街的犬吠声登时响成一片。
睡梦中的徐传灯懵懂着直起身子,手扒窗户往外看,满眼都是皎洁的月光。
鬼子又在抓人还是游击队又来袭击宪兵队了?传灯掌上灯,茫然地盯着汉兴挂在衣架上的那件衣裳,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出来……哥哥,你在那世还好吗?跟汉兴在一起的那些历历往事雾一般地旋上了传灯的脑子,传灯恍惚看见年幼的自己跟在汉兴的身后踯躅走在薄雾氤氲的清晨,晨曦透过薄雾将兄弟两个照得五彩斑斓。走着走着,汉兴就不见了,四面八方吹来的风将传灯围在中间,让传灯感觉自己十分孤单。有尖弱的哭声传来,传灯看见薄雾中走出了一袭白色和服的百惠,传灯看不清楚她的模样,传灯只能看见她一闪一闪地走,就像被风吹着的纸条……传灯想过去喊她,让她跟自己一起去找汉兴,可是她忽然就不见了。吉永太郎狞笑着向传灯靠近,他的脸在变幻,开始是人脸,后来逐渐爆裂,逐渐变成了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兽脸,这张脸越靠越近,传灯几乎看见了它血红的喉管……
放在窗台上的油灯呼啦一下灭了,传灯猛然打了一个激灵,这才发觉自己刚才做了一个可怕的梦。
窗帘在忽闪,传灯以为是风把油灯吹灭了,起身再来点,刚刚点上,油灯又灭了。
有人吹灯!传灯冷不丁惊出了一身鸡皮疙瘩,难道是我哥哥显灵了?传灯定住身子,屏声静气,悄悄观察四周……
窗帘一动,一条黑影嗖地闪了进来:“别出声,我是喇嘛。”
传灯有些惊喜有些沮丧,一屁股坐到了床上:“妈的,我还以为……半夜三更的,你来干嘛?”
喇嘛不应声,一步跳到门后,迅速拉开了门,随即,一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了门口,窗外透进的月光让他浑身散发出生铁样的光泽。
“关大哥!”传灯掩嘴一声惊叫,扑过去,一把将关成羽拉了进来。
“你还好吗?”关成羽将手里的匣子抢搁到桌子上,斜眼瞅着传灯,微微一笑。
“还好……”传灯哽咽了两下,“刚才我梦见汉兴了……”
喇嘛连忙插话:“吉永太郎下午来了下街,晚上住在南学堂里。大哥得到这个消息,带着我们几个连夜赶过来,谁知道中了这家伙的奸计,差点儿就被他给‘拾猴儿’(收拾)了……娘的,幸亏李老三反应快,跟几个兄弟把他们引到大马路那边去了,武哥带人在那边接应着,我和大哥过来看看你。”抓起桌子上的一碗水,咕咚咕咚灌了一气,“******,当初我就觉得小炉匠这个混蛋不是个顶事的主儿,果然吃了他的亏!你猜咋了,情报是他提供的,我们赶过来跟他联系的时候他不见了,我们钻了鬼子的口袋……打起来以后我看见,这小子躲在一群鬼子后面,捏着把破王八撸子瞄关大哥,被我一枪撂倒了,估计不死也得落个半身不遂……”把头转向沉默不语的关成羽,忿忿地嘟囔,“大哥,你说你咋就交往了这么个弟兄?还说他跟你是十几年的兄弟呢,操,没死在他的手里。上次我住在他家,他的指头断了几根,我问他是怎么搞的,这小子说是锔锅的时候受伤了,当时我就知道他在撒谎,那分明是被人给掰断的!这家伙鬼心眼子多着呢,有次喝多了,絮絮叨叨地对我说,能活着就比啥都强……”“说够了没有?”关成羽冷冷地打断了他,“他那是被周五常给逼的。”
喇嘛横了一下脖子:“逼他,他就不讲江湖义气了?尤其是……他,王八犊子,他竟然投靠了小日本儿!”
传灯听得有些发懵,问闷闷不乐的关成羽:“你刚来下街的时候是不是住在他家?”
关成羽望着墙角不说话,喇嘛哼了一声:“就是。武哥说,他们以前一起在前海那边混过……”
“不要说了,”关成羽挥了挥手,“传灯,这几天你帮我注意点儿周五常的行踪,我必须尽快处决他。”
“周五常到底去了哪里?”喇嘛盘腿上了炕,“听说他打从不干乡保队以后就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知道,”传灯冷笑一声,“我一直没忘了观察他,他逃不出我的眼皮子。现在他成了丧家犬,去了即墨马山,那边有一帮胡子,领头的外号叫老宫,据说这家伙以前也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前几年看上了本村的一个闺女,拦在路上把人家给糟蹋了,乡公所派人抓住他,打得挺厉害。这家伙恼了,半夜夺了看守的枪上了马山,后来笼络了十好几个人跟着他一起干。我估摸着,周五常看见魏震源回来了,感觉这是走投无路了,想跟从前跟着魏震源一样跟着老宫,先躲躲风头,然后再做打算呢……”
“不要提他了。”闷了好长时间,关成羽瞥一眼徐老爷子那屋,“本来我想过来看看老人家,看来不行了,天亮之前我必须回去,”轻轻将手摸上了传灯的肩膀,“这次过来一是为了刺杀吉永太郎,二是为了扰乱一下他的脑子,因为上次我对你说的关于他们要把舍利铁函运出青岛的事情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让他们适当乱上一乱也好。你没有把上次我交代给你的任务忘了吧?”
传灯说:“没忘,我经常在街上走动,还故意在宪兵队门口晃悠过几次,可是吉永次郎一直没来找我,这几天我正打算过去找他呢。”
关成羽抽回手,捏着下巴道:“也许他是在避嫌。这样,这几天你就去陆军总部找他,装作打听汉兴下落的样子,明白我的意思?”
传灯点点头:“明白,我装作不知道汉兴已经‘走’了的意思。”
“对,”关成羽说,“然后把话往古董那边引,话说得要巧妙,不能让他觉察到你的意图。”
“这个不用嘱咐,”传灯用力握了握关成羽的手,“中国人的宝贝坚决不能落在强盗的手里,放心吧大哥。”
“老人家这边你一定要安顿好,”关成羽又瞥了徐老爷子那屋一眼,“不能再让他担心了。”
“我知道。大哥,山里那边还好吧?”
“很好,”关成羽的眼里放出光来,“跟鬼子干了几仗,很漂亮,鬼子现在轻易不敢进山扫荡了,下一步我准备跟青保大队联合起来跟吉永联队好好地干上一仗,彻底灭了他们的锐气!臧大勇说,共产党毛主席说,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房住的穷朋友,稍有血气和不愿作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应该联合起来,投入到抗日的民族战争中去。我很赞赏这句话,总有一天我要带领弟兄们投身共产党,做共产党的队伍,那样大家才能有一个更好的归宿。臧大勇正在跟上级联系……这话暂时还不能说。反正共产党的主张我是非常赞同的……”
“管那么多干啥?”喇嘛一蹬腿躺倒了,“好兄弟绑在一起跟小鬼子拼命就是好主张,管他谁的主张呢。”
“刘禄也跟着周五常去了马山?”关成羽问传灯道。
“嗯,那是周五常的一条狗,”传灯不屑地嗤了嗤鼻子,“他家的人都死在鬼子的身上,可是他无动于衷,畜生一个。”
“这个人我不太了解,”关成羽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被周五常给逼成那个样子的。”
“别提他了,这个人比他哥哥还土鳖。”
“那也不一定,”喇嘛一骨碌爬了起来,“他现在跟着周五常当胡子去了,也许那帮胡子是打鬼子的,这工夫正跟鬼子接上火了呢。”
“呵呵,有可能……”想起在东北时刘禄对自己的关照,传灯哑了。
喇嘛和传灯全都估计错了,这当口刘禄不在马山,他跟在周五常的身后急匆匆地行走在去崂山的路上。
魏震源暴打蒋千丈的那天,周五常直接带着刘禄赶去了沙子口,没费多少劲就找到了韩仲春。
韩仲春正坐在一个岗楼里给几个汉奸训话,一听来报,兴冲冲地赶了出来。
确定魏震源是抗日分子这个消息之后,韩仲春集合队伍,让周五常和刘禄带路,杀奔下街而来。
五十几个汉奸赶到大庙场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周五常让韩仲春停下,自己找到一个团丁,打听到魏震源现在正在三盛楼跟几个乡绅喝酒,立马赶了回来。
韩仲春激动得就像吃了的猴子,掏出五十块大洋塞到周五常的手里,指挥手下气势汹汹直扑三盛楼。
周五常没有走远,拖着鼻涕一样软的刘禄去了小炉匠家。吩咐小炉匠给他们烫上酒,让小炉匠出门观察三盛楼那边的动静,周五常就跟刘禄你一杯我一盏地喝了起来。不多时候,三盛楼那边响起稀稀拉拉的几声枪响,小炉匠回来了,脸耷拉得比驴还长。周五常当场就明白,魏震源逃脱了……半夜,周五常喊起同样没有睡着的刘禄,惦着韩仲春给他的五十块大洋,咬牙切齿地说,兄弟,没有咱哥们儿的活路了,干脆直接去宪兵队要求当汉奸吧,这就叫逼上梁山啊!他娘的,是死是活就看天命了!刘禄心怀忐忑,半晌没有做声。两个人正在瞪眼,院子里想起一阵悉悉索索的爬墙声。周五常赶出去,一把将骑驴也似跨在墙头的茅草里的小炉匠扯下来,一巴掌抡回了屋子。
当着刘禄的面,周五常一刀一刀地划小炉匠的脸,刘禄害怕了,一声“大哥我全听你的”被他嚷得凄惨如厉鬼。
周五常左手掐着小炉匠的脖子,右手捏着刘禄的手腕,一字一顿地说:“现在咱们三个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死活都在一起了!”
小炉匠看样子是被周五常吓破了胆,浑身哆嗦有如筛糠:“大哥,你说了算……”
周五常将自己的脸越来越近地往小炉匠的眼前靠:“你必须这样,不让你全家都是一个死。”
小炉匠的嘴唇僵硬得合不拢,舌头也发了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刘禄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他知道,就在一天前周五常杀了小炉匠的全家……
在这之前,周五常打听到小炉匠跟关成羽的关系,怕小炉匠将自己的行踪告诉关成羽,绑架了小炉匠的老婆孩子,回来对小炉匠说,你必须听我的,因为我绑了你全家,不听话的话,我一个一个全杀了他们。小炉匠当场就变成了周五常的另一条狗……当周五常得知喇嘛曾经在小炉匠家住过几天后,周五常让小炉匠交代喇嘛都对他说过什么话,小炉匠起初含糊其辞,被周五常掰断了几根指头,全部说了实话……过了几天,周五常当上了乡保队小队长,很少来找小炉匠了。小炉匠担心自己的老婆孩子,来找周五常,周五常说,他们没事儿,等我将来安稳了,一个不剩地给你送回来。小炉匠一走,周五常刚吃过死尸的野狗一般瞪着血红的眼睛对刘禄说,无毒不丈夫,我把他的全家都杀了,不然他是不会死心塌地跟着老子干的。刘禄惊得当场尿了裤子,感觉自己正走在奈何桥上,四周黑漆漆,阴风嗖嗖,自己的哥哥左手牵着自己的娘右手牵着自己的爹正凄凄惨惨地朝自己招手。
周五常见刘禄张着大嘴不言声,将小炉匠往他的身边一推:“关于我的为人你可以告诉他。”
刘禄搂一把小炉匠,闷声道:“咱大哥是个好人。”
周五常冷冷地一笑:“我不是个好人,我踹寡妇门挖绝户坟,杀人****无恶不作,跟了我就等于跟了阎王爷,这一点你必须清楚。”
“大哥,你让我替你做什么?”小炉匠好歹把这口气喘顺溜了,可怜巴巴地说。
“跟我们一起去宪兵队,”周五常沉声道,“你作保,我们从此以后就是皇军的人了,生死都是汉奸。”
“行,”小炉匠狠劲地点头,“只要你不杀我全家,做什么都成。”
“要做就横下一条心,”周五常的声音冷得像刀子,“以后我们就绑成一堆了,先杀几个抗日分子给皇军看看。”
“杀……”小炉匠猛地一抬头,“我知道你跟关大炮是仇人,逮机会我先杀了他!”
“哈,****娘,”周五常阴森森地笑了,“你他娘的有那个能耐吗?可也是,他不防备你,也许你比我干这事儿容易得多。”说着,掂掂手里的钱,一把攥住,“小鬼子也喜欢钱!先用它孝敬孝敬当班的,进去再说,然后……哈哈,好了二位,收拾一下跟我走。”
当下,三个人幽灵一般闪进了下街宪兵队的大门。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放明了,天空似白似黄,就像一张巨大的死人脸。
周五常伸出双臂搂了搂战战兢兢拖不动脚步的小炉匠:“兄弟,就这样吧,你留在下街等我们的消息,我们这就去马山。”
小炉匠不敢抬头看周五常,哈哈腰,嗫嚅道:“我的老婆孩子……”
周五常说声“还活着”,悠然把脸转到了一边。
小炉匠微舒一口气,贴着墙根,歪歪扭扭,病猫似的往家出溜。
周五常摇摇头,冲痴呆一样看着他的刘禄一笑:“这才是一条真正的狗呢。”
刘禄挺了挺胸脯:“对,他是狗,我是狼。”
周五常将手里的一个证件当空一晃,背着手往铁道的方向走:“你不是狼,你也是一条狗,我是老虎。”
两个人进车站等了一会儿,过来几个鬼子宪兵,验看过证件,挥手让他们上了一列刚刚进站的火车。
火车吭哧吭哧地开动了一阵,借着腾腾的白雾,周五常拉着刘禄跳了下来,眼前是一片铁矛般林立的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