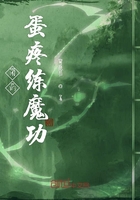这年过得实在只能算是应付,老爷子走了四天,回来的车上除了半袋子白面和两只藏在车底下冻得邦邦硬的野鸡之外,只有小半车药材,大都是货底子,不成个儿的槟榔、折了须子的参尾巴、干裂碎残的阿胶、手指粗细的当归……
年初一的早上,白芷穿上新袄子随着老爷子往各家去拜年。因着过年,崔玉姬头发上的篦梳也缠了几丝红线,算是添了一抹喜气,胡大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大过年的没有炸糕卖,崔玉姬煮了饺子给他,他每吃一口,便看崔玉姬一眼,直看到白老爷子他们离去。
金半仙儿正披着道袍往北郊的道观去,甭管真假,初一的香还是要上的,百姓走亲戚,神仙敬高香,过年的日子里,白老爷子对一切都宽容了许多,竟然破天荒地没有嘲笑金半仙。
舍得典当行家的黄老板着实热情,这典当行开业不过一年多,虽说二丫时常喊着白芷一起去逛集,可与黄老板家却也只算得邻里关系,不想又是果子、又是蜜饯地招待了许久,临走时,黄老板还死活塞了一条链子给白芷,只嚷着白芷乖巧,和他心意,倒把白芷吓了住。
白芷看着柜台上的链子,一双柳叶眉扭在一起,很是苦恼。瞧那羊脂玉籽料的小牌子,平白如光,色润如油,正中一朵半开的莲花,无甚稀奇,反倒是那链子惹眼得很,一环一环地扣在一起,丝毫不见缝隙,显见着是整块的大料雕出来的。
这般舍得用料的物件已是稀有,更甭说这雕工了,链子不过小指一半粗细,环节活络,棱角圆滑,整条链子并不大,放在手里不过一握,戴在身上也不觉扎眼,只是再看时难免夺了人的眼光去,这样的链子,定是出自名匠之手。
“哎!这洪武年间的东西了,哪儿来的?”十一突然探头过来插嘴道。
“你怎么知道?”白芷奇道。
“洪武年间宫中盛行过一阵子这种莲花图样,便是这般的包蕊样式,没多久就改了制式,到了清朝已然是换作了番莲……”十一只看了一眼。
“就不能是这会儿子的人仿的?”白芷一双杏眼闪了闪,十一总是出乎她意料。
“不能,你看那链子衔着牌子的地方,刻着一只燕子,这可是洪武年间最出名的玉雕师傅飞燕子的记号,便是有人仿样式,也仿不出那燕子,这雕工,绝了……”十一一手捻起链子,一手托着牌子,这手法和安四爷给白老爷子看祖传的朝珠时一模一样。
白芷细细瞧去,果然有一只燕子,双翅飞展,轻盈雀跃,不过米粒大小,若不是十一提起,她只怕都不会看到。
“这链子可是好东西,飞燕子的玉雕大都供了皇家……”十一难得竟然话多了起来,可是他越说,这白芷心里就越是忐忑。
十一能文,十一会武,十一知三民主义,十一还懂古董……乞丐是不可能有这样的能耐的,现而今乱成这样,蒋介石年初又被推举为了北伐总司令,可见离打仗不远了,满街地抓人,白芷看着十一,心里竟然存了猜疑,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物?
黄老板又为何送她如此贵重的一条链子,塞给她的时候连个盒子都没有,似乎这不过就是一个苹果、一颗梅子干似的。白芷摇着头收起了链子,许多事情,既然无人明言,旁人自然也还是莫要点破的好。
二月二龙抬头,白老爷子剃头回来,看着十一那头半长不短的乱发努了努嘴道:“去去去,让你何叔领着,把头剃了,晚上见客也好看些”。
“晚上谁要来嘛?”白芷正编着辫子,光亮黑长的头发直垂到腰际。
“知礼早上捎了信儿,说要过来。”白老爷子对这孙女婿可是满意得很,这会儿连胡子都要翘起来了。
彭知礼还没到,知味居的猪头肉却是已经送了来,薄厚适中的肉片高高低低得码在一起,拼出半个猪脸的模样,另一碟猪耳朵切了丝儿,混着姜蒜和香油拌在一起,香气直往鼻子里钻,挡都挡不住;另又并着卤花生、炸蚕豆、炝拌豆干、渍黄瓜四样下酒菜一起装在食盒里。
另一个单层食盒里是一大锅冒着热气的羊汤,羊脊骨在米白色的汤里翻滚着,葱花、香菜厚厚地撒了一层,胡椒粉和干辣椒用白瓷罐子装着摆在一旁,食盒底下还用碳箱子暖着,一路送过来竟还冒着热气……
彭知礼踏着月色走进畅安堂的时候,十一正帮白芷摆着碗筷,十二被通天压在身下,一猫一狗在地上滚打着,金半仙捻着八字胡,笑吟吟地端坐在桌前,两眼直瞪着翻滚的羊汤锅子。
“金道长,给您拜个晚年……”彭知礼看见金半仙,连忙抬手行礼。
“彭老板好,老道我掐指一算,今日东边必有吉事,这就寻了来,巧不巧这一桌子好菜,老道我也就愧着脸皮受了……”金半仙起身回礼。
“你个假道士,竟扯淡,还东边必有吉事,咱两家统共就隔着一堵墙,还分什么东南西北,蹭饭就蹭饭……”白老爷子就差啐金半仙一脸了。
“爷,吉事总是好的嘛,管他东南西北呢,先生不来,你又要着人去叫,快落座吧,彭先生还站着呢。”白芷端着热好的酒放在桌上。
酒也是彭知礼带来的,整整一大坛子莲花白,酒香凌冽,隐隐药香,入喉柔和,酒性清醇。
“哟,好酒啊,早年间老佛爷就好这一口,听说宫里的莲花白是用万寿山昆明湖里的白莲花蕊酿的……”金半仙闻着酒香,半眯着眼睛叹道。
“这个也是。”彭知礼翘着嘴角颔首应了句。
金半仙听得这话,已是再忍不得,不等他人落座,便干了一大碗。
“好酒!好酒!好酒啊!”金半仙连连叹着,又是一满碗。
“就说你个假老道,你还总不认,一肚子酒虫都快成精了!”白老爷子拦住金半仙端起的酒碗笑骂道。
这顿饭吃得实在算得热闹,彭知礼多次往来京津,带回了许多消息,几个男人争论了许久何为“农民活动”,又说起国外的新兴工业,越说越是热闹。老爷子一时兴起起身耍了一套太极拳,金半仙儿更是一人干了半坛子莲花白,喝到入夜时分,已是醉眼迷离地看着门口花瓶里插的梅花,咿咿呀呀地唱起了昆曲。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便赏心乐事谁家院……”八字胡、灰道袍的一个道士竟然把这旦角的唱腔拿捏得如此地道,真真是百转千回,柔情婉转,只听得人心中情丝万千。
大家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饭,谁也没提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事儿,共产党声势浩大,国民政府又和英、日纠缠不清,这仗很快就要打起来了。
白老爷子趁着酒劲儿拉了金半仙去下棋,只剩得知礼、白芷、十一三人围坐一桌。
“早间看见往西大坟去的车了。”白芷泡了一壶茶放在桌上,轻声说道。
“连年战乱,命如草芥。”倒是十一难得接了句话,一双剑眉蹙在一起,今儿一整天,他说的话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又要打仗了。”白芷叹了口气,替二人各添了茶,茶色红亮,蜜香隐隐,和清冽的酒香混在一起,别有一番味道。
彭知礼抿着茶,一字一句道:“只有战争才能结束战争。”这话说得斩钉截铁,却是引来十一侧目。
十一今儿换上了年前新做的褂子,青灰色的棉布,滚着一圈儿暗红的边儿,普通小工常穿的褂子,无甚稀奇。只是刚拿回来试衣服的时候,一个回身被药刀扯住,划开个一寸来长的口子,白芷便绣了个葫芦纹样给遮了住,这衣服只年初一穿了一天,就被十一宝贝似的收了起来。
“只有战争才能结束战争。”十一呢喃重复了一句,竟冲彭知礼举了举杯,一饮而尽,不是茶,是酒。
“是夜,近昼。”彭知礼举杯应道。
十一明白,越是黑暗,便离天明越近,这乱世便是如此,彭知礼相信,他也相信。
“林上月已去,唯有候金乌。”十一仰头便是一杯。孙总理离世,三民主义还未实现。
“金乌虽未至,繁星亦闪闪。”彭知礼亦是一杯。内忧外患非一日之寒,时至今日,冰冻三尺,可三尺寒冰已见裂隙,诸多军阀,必有真心为民者。
“星光如豆,势必艰辛。”十一摇头,又是一杯。中共革命武装和游击战实在比国军的大部队差了太多,早先的几场仗打下来,悬殊之大,可见一斑。
“豆烛亦可燎原。”彭知礼嘴角含笑,举杯畅饮,书生模样的一个人竟然多了一分豪气。
两人你来我往间已是喝光了一整壶酒,那两杯茶反倒凉在一旁,无人问津。
“哎呀!输了,输了……”白老爷子懊恼着走了过来。
“有输自有赢,老爷子何不再来一局?”金半仙也摇头晃脑地撇着嘴跟了过来,好一副自得模样,更是气得白老爷子跳脚。
“不下了,不下了,跟你个臭棋篓子下得多了,我都退步了。”白老爷子坐回桌上,正欲伸手倒酒,却被白芷挡了住。
“爷,新泡的茶,尝尝看?”一碗红茶塞进了白老爷子手里。
“不喝不喝,有酒谁还喝茶啊!”老爷子自是不乐意。
“酒兴起时茶自浓,有酒也得喝茶啊,我陪您喝杯茶吧。”彭知礼端起一旁早就凉了的茶碗道。
“你们两个啊,一唱一和的,就是不让我喝酒。”白老爷子似怒似喜地说着,脸上一抹熟谙世事的笑。
“还不是怕您喝多了吗……”白芷剜了老爷子一眼,没好气地道。
“喝茶一样醉人。”彭知礼跟着道。
“你们这妇唱夫随的,倒是一套一套的,”老爷子笑着捋了捋胡子,又道,“什么时候把婚事办了,老头子我也好早些安心……”白老爷子这句话一出,白芷登时红了脸。
“爷,就说你喝多了吧,前几天还嚷着让我多陪你两年呢,看你明早醒了不后悔今天胡说的!”白芷瞪着白老爷子,话却说得分明。
“白姑娘有孝心,知礼自然成全,何况知礼身上孝期未满,恐怕……”彭知礼起身冲白老爷子抱拳行礼,一句话只说了半句,便不再言语。
屋里一时间静了下来。
白老爷子似是酒劲儿上了来,打着酒嗝伏倒在了桌子上。金半仙更是不知什么时候卧在了塌上,已经睡了过去,通天并着十二一起窝在他脚下,一人一猫一狗俱是起了鼾声。
十一送了彭知礼出门,白芷一人站在院里,西北风吹在脸上,又干又烈,凝脂般的脸上反倒带着笑,这顿饭吃得很舒服。她对嫁给彭知礼这件事还带着迟疑,听得彭知礼推脱,她竟然觉得舒了口气……
彭家送来定亲礼那天,她才刚满十四岁。
那也是个雪天,彭家老爷子一本老正地端坐在那,白老爷子喊了她来见礼。
“都读过些什么书啊?”这是彭家老爷子对她说的第一句话,不像相儿媳妇,倒像是收徒弟似的。
“四书五经早年间在学堂里读过一些,再就是医书了。”白芷倒也不拘谨,她自小流离失所,最不怵的就是见人。
彭老爷子点点头,动作缓慢而略有些夸张,就像一早就摆好了架势似的,白芷觉得,无论她怎么回答,他都会这样点头。
那天之后的一个吉日,六子便带人送来了聘礼,她正裹着围裙,坐在药刀前和一把参须子死磕,白老爷子捋着胡子笑得合不拢嘴,直到这会儿,她都还没和彭知礼面对面地说过话。
“彭家大家大业的,为什么和咱们家定亲?”这是白芷奇怪的地方,她对要嫁给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男人,反倒不觉怎样。婚姻,是两个家族建立关系的最好办法,千百年来都是如此,她不能白吃白家的米饭。
“我畅安堂百年字号,怎么着?还配不上他一个绸缎庄?九流里,我医卜行四,他商贾最末,这是时代不一样了,不然我还舍不得把你嫁过去呢,哼!”白老爷子气哼哼地昂着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白芷想到这,不由噗嗤一笑,这一笑如白雪红梅、黄昏彩霞,登时闪亮了刚迈进院内的十一的眼。
第二天一大早,何得仁便拉着白老爷子小声嘀咕了一番,老爷子宿醉醒来,正口干舌燥地饮着茶,这会儿反倒兴奋了起来。
“行行、行,怎么不行呢?我去给你提亲去!”白老爷子说着就要回屋换衣服。
“何叔,你们说什么呢?给谁提亲啊?你要娶小啊?”白芷听得莫名。
“这孩子……竟胡说八道!我……”何得仁被白芷说得老脸一红,急得话都说不出来了。
白老爷子倒是差点乐背过气去,“给宝子说亲!你个小丫头,没大没小的!”说是呵斥,还不如说是夸奖,老爷子是一丝生气的意思都没有,反倒伸出拇指比划了一下。
“宝子?宝子才多大啊?你这是想给他说谁家姑娘啊?”白芷放下手里正包着的药,从柜台里出了来。
“十四了,不小了,他大姐嫁去了塘沽,一年能回来一趟啊,就他这么一个小子,早点成亲,家里也好多个人照应,”何得仁说得认真,转头又道,“这不,看中了舍得典当行家的二丫头,我看那丫头不错,是个能张罗的人,手脚也利落……”何得仁的话没说完,就被白芷打了断。
“二丫?二丫比宝子大三岁还多呢!”
“女大三,抱金砖嘛!女人大点好管家,你不懂……”何得仁直摆手。
白芷看了一眼十一,还要说些什么,却是又咽了回去,反倒弄得十一一脸莫名,刚要开口问,就看门外进来一人。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白老爷子喜滋滋地迎了上去,来人正是舍得典当行的黄老板。
可黄老板却是一脸的匆忙,抬手冲白老爷子挥了挥,就看老爷子脸色一变,拉着黄老板奔了后院,何得仁咧着嘴招呼十一往楼上露台搬药材去了。白芷一人歪着脑袋,看向后院的方向,满脸狐疑,她瞧见了的,黄老板手里的东西,细细长长,闪着润白光泽,是枚白玉簪,她没见过,却莫名觉得眼熟。